鄉村治理如何實現“善治”
鄭嘉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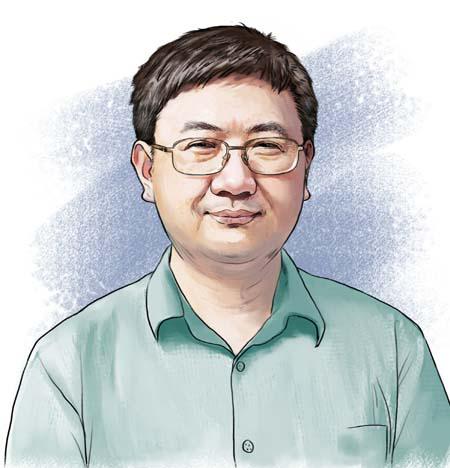
在《鄉土中國》一開篇,費孝通先生寫道:“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70多年過去,中國社會已經發生巨變,中國不再是那個“鄉土中國”了。但是,村莊從未消失,農民依然存在。隨著大量農民進城務工,鄉村正發生著前所未有的大變局,當今中國的農村問題比歷史上的任何時候都更復雜、更棘手。
中國正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計劃到2035年,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的現代化;到2050年,全面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目標。鄉村安定有序是鄉村振興的保障,創新鄉村治理體系、走鄉村善治之路也是實現鄉村振興的路徑之一。那么,什么樣的鄉村治理可以稱作善治?當村莊里的精英不斷流失,鄉村要由誰來治理?在熟人社會解體的背景下,中國農民的主體性又該如何激發?就這些問題,《南風窗》記者專訪了武漢大學社會學系主任、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教授。
講善治,不能抽象地講
南風窗:中國政府提出了鄉村治理的“善治”目標。在你看來,善治的標準應該是什么?
賀雪峰:中國太大了,不同地區的鄉村有截然不同的特點。我們講善治的時候,一定不能抽象,必須具體,不同的地區應該有不同的標準。中國鄉村的區域差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南、中、北方村莊社會結構的差異,二是東、中、西部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
先說南北。我們知道,一般的鄉村治理是以地緣為基礎的,比如鋪設道路、修建水利、保障安全等等。華南的農民聚族而居,往往一個自然村就是一個宗族,血緣與地緣合二為一,在鄉村治理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而華南村莊是比較團結的。華北村莊里則有很多個血緣共同體,我們叫它“小親族”,不同的“小親族”之間競爭很激烈,所以華北村莊里的派系比較嚴重,是分裂的。而在南北中間的四川湖北等地區,由于村莊建成的歷史非常短,不管是地緣還是血緣,都沒能形成強有力的凝聚。從地理上來看,三五家農戶形成一個“灣子”;從血緣上看,人與人比較疏遠,親兄弟間的交往都不很密切,所以是分散的。
這種差別體現在許多現象上,村干部的選舉就是一個例子。在選村干部時,華北村莊自然地分成很多派,競爭也很激烈,會出現各個派系合縱連橫的情況;華南地區不太需要選舉,因為是一家人,大家心里都有桿秤;在較為分散的中部村莊,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意愿不強,想當村干部的人就需要四處作動員。
更重要的是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差異。在部分東部沿海,尤其是長三角、珠三角一帶,許多鄉村已經融入了城市,它們只在體制上是農村,但在基礎設施、市場條件等方面已經和城市沒什么區別了。不同于傳統的村民自治,這些地區的鄉村治理已經和城市治理同構,村莊越來越像社區,村干部也慢慢專職化,開始坐班、領工資。中西部地區就不一樣了,那里大多數的青壯年農民選擇進城打工,人口流失嚴重;村子里剩下大量老人、孩子留守,出現了老人農業,鄉村經濟比較蕭條。
不同區域村莊的條件不一樣,治理的手法、善治的要求顯然不一樣。
南風窗:中國鄉村的主體是以中西部村莊為代表的傳統鄉村,就這部分村莊來說,應該怎樣實現善治?
賀雪峰:我們的鄉村治理不應該實現一個高大上的目標,而是要實現一個基礎的目標,那就是為留鄉農民提供生產生活的需要,維護生產生活的秩序。
從生產上來看,我們應該為小農提供灌溉的便利、機械化的便利、土地連片成塊的便利。從生活服務上來看,不少農村存在彩禮高、人情重,村莊文化薄弱,邪教、低俗文化容易散布的問題,這些都是鄉村治理的目標。
農業政策出臺了很多,但有的是在推動資本、大戶進入農村,而不是在滿足小農戶的需要。中國的農業蛋糕就那么大,動員城里人回農村發展產業,搞規模經營,就把農村本就不多的機會占去了,小農戶怎么辦呢?解決三農問題還是要通過城市化,只有減少農民才能提高農民的收入水平。所以,今天的農民是應該大量進城的。農村產業興旺不是現在,不要著急,現在農村的機會不多,與其在農村發展,不如去城里發展。
當前問題在于,講善治不講條件,把未來的長遠規劃作為今天的目標,把發達地區的做法當作中西部地區的樣板。一些沿海地區的治理方法,一旦成了基層治理現代化的典型代表,中西部就要學習推廣,可中西部地區是學不了的,它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需要。
利用好“中農”
南風窗:在傳統的鄉土社會中,村莊可以通過熟人社會的規則、默契來實現自治;隨著大量農民進城打工,中國鄉村的熟人社會正在解體。在這種背景下,鄉村自治應該如何實現?
當前問題在于,講善治不講條件,把未來的長遠規劃作為今天的目標,把發達地區的做法當作中西部地區的樣板。
賀雪峰:傳統鄉村的人口正在凈流出,而且是鄉村精英的流出、人財物的流出。在這樣的情況下,鄉村實現自治是比較難的。
首先要解決的一個問題是,誰來當村干部。在大多數的傳統農村,村干部是不脫產的。他們沒有工資,只拿誤工補貼,農忙的時候干農活,農閑了再做村里的工作。農村勞動力還沒大規模外出打工的時候,村干部除了農業收入,能多拿一塊誤工補貼,屬于村里收入比較高的群體。但現在村民普遍外出打工,賺的錢要比村干部的收入高多了。村干部只靠誤工補貼和農業收入,幾年以后就成了村里最窮的人:隨不起份子,建不起房子。沒有權威了,那還怎么當干部呢?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湖北省提出把主要村干部專職化。村支書脫產、坐辦公室,年收入提高到四萬塊錢。可是書記專職化了,副書記怎么辦呢?其他村干部怎么辦呢?村干部收入差不多的時候,書記指揮大家干活;現在書記是專職的了,收入高了,其他干部就不愿意干活了。況且中西部農村根本沒那么多事,村干部天天坐在辦公室里,完成一些機械化的任務,反倒失去了和群眾的接觸。
讓中農擔任村干部是個好辦法。在村莊里,總有一些人是不愿進城的,他們在村里找到了自家承包地之外的獲利機會,收入不比外出打工少:比如租種他人的耕地、擴大種植規模,再比如搞農機服務、規模養殖、農資和保險代理。這些留守鄉村的“中農”是村干部最好的人選,也是鄉村治理的骨干力量。由于沒有脫產,他們了解村莊的情況,了解村民的生活,也就能為村民提供基本的生產生活服務;而且他們也愿意成為村干部,除了拿誤工補貼,當村干部能擴大社會關系網,積累政治資源,這是中農特別需要的。
鄉村社會結構天然產生了中農,我們要利用好這種治理力量。這也是為什么不應該支持資本下鄉搞產業一體化,一旦農村的獲利機會都集中到商業資本手中,中堅農民就失去了存在空間,最后的農村精英也要被消滅了。
南風窗:你在湖北荊門等地的村莊里開展了十幾年的老年人協會實驗,這類村民組織對鄉村治理有什么幫助?
賀雪峰:老年人協會成立后,村里60歲以上的老人都成為會員。他們聚在一起聊天、打牌,開展文藝活動,看望生病的老人,把生活過得很精彩。農村的老年人最怕無事可做、在家里憋著,老年人協會給了他們一個生活的“盼頭”。更重要的是,這讓年輕人有了一個穩定預期:自己老了以后,生活也可以很有質量。有了這種預期,他們才愿意參與村里的公共事業,鄉村自治才有基礎。
有一個群體很值得重視,就是老年人協會里的會長、副會長和積極分子,我把他們叫作“負擔不重的人”。這些人60多歲,子女已經成家立業,他們生活上衣食無憂,心理上也沒有負擔,所以很愿意做一些出頭露面的工作,發揮余熱。
基層治理涉及的大都是雞毛蒜皮的小事。家庭矛盾、鄰里糾紛這樣繁瑣的事務說不清、道不明,最讓村干部頭疼。這時,負擔不重的人就發揮作用了:老人們空閑時間多,工作可以做得很細;而且他們天天在一起議論村里的事,主導了村莊的輿論,所以他們調解基層糾紛的效果就特別好。在中西部農村,這樣負擔不重的人并不少,把他們組織起來,就能發揮農民的主體性,化解基層矛盾。
“中堅農民”和“負擔不重的人”都是從農村內部自然產生的,我們應該重視農村內部的結構性力量,通過政策鼓勵和支持這部分力量參與到鄉村自治中來。
培育農民的主體性
南風窗:你剛剛提到了農民的主體性,為什么這種主體性對維持鄉村秩序特別重要?
賀雪峰:進入現代社會以后,農村舊的價值體系和道德觀念正在解體,新的價值體系和道德觀念還沒有建立起來。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農民之間的關系很快暴露在赤裸裸的理性算計之中,村民們只關心自己的利弊,不在乎村集體的得失。在這樣的村莊里,村民之間很難達成合作,村集體沒有凝聚力,不僅村莊的公共工程和公益事業組織不起來,村內的秩序也更加混亂。
這些留守鄉村的“中農”是村干部最好的人選,也是鄉村治理的骨干力量。
我在調研中發現,許多中西部的鄉村都存在主體性缺失的問題。農民對村莊的未來失去了希望,時刻準備著永遠離開村莊。他們不在乎村民對自己的評價,不在乎村內的輿論,所以更敢于不孝順父母,敢于與鄰居產生糾紛,敢于破壞鄉村的公共秩序。
南風窗:在鄉村治理的過程中,應該怎樣培育農民的主體性?
賀雪峰:簡單地理解,培育農民的主體性就是引導農民積極參與自治,讓他們自己決定村莊該怎樣建設、怎樣發展,并且主動為鄉村的建設出力。
我認為,資源下鄉是培育農民主體性的很好的方法。農業稅取消之后,國家對農村的轉移資源越來越多,但是國家政策和資源不能盲目下村,向農村轉移資源的關鍵其實不在于辦成幾件具體的實事,而是調動農民主動性和培育農民主體性。
舉例來說,地方政府決定給一個村子修條道路。很常見的情況是,項目實施過程中會有村民因道路占地變身“釘子戶”,向政府索要高額賠償。這些“釘子戶”往往扯皮打滾,不達目的誓不罷休;而其他村民則事不關己,圍觀而已,一旦釘子戶最終獲利,村民們還會把他視作榜樣,紛紛效仿。本來政府修這條路是為當地農民服務,是惠民工程,但結果卻是政府做的好事越多,“釘子戶”越多,政府與村民的關系也越疏遠。
我們不妨換一種資源下鄉的方式,充分發揮村民自治的作用,引導村民自己決定資源的分配和使用。同樣以修路為例,可以先由村集體討論決定這條路需不需要修、該怎么修,國家財政再根據具體情況發放一定數額的項目補貼。這樣一來,財政資金與每個人的切身利益就緊密聯系起來了,村民自然有動力積極參與公共事務。如果這時再出現“釘子戶”,他損害的就不僅僅是政府的利益,而是壞了全村的好事,他將承受全體村民的輿論壓力。
通過資源輸入激發農民主動性,國家資金的使用效率就變高了。更重要的是,它提高了農民參與村莊建設、維護村莊秩序的能力,在分配和使用資源的過程中,村民被組織起來,村莊內的其他公共事務也有了解決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