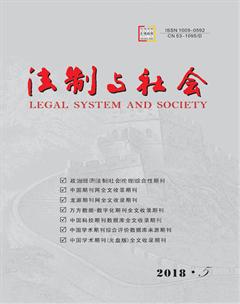論人工智能生成內(nèi)容在著作權(quán)中的定性
摘 要 人工智能所生成的內(nèi)容,如何在著作權(quán)中定性,需要考慮的不僅是有無著作權(quán)法明確要求的“獨創(chuàng)性”,還要考慮人工智能這樣的一種存在,是否符合著作權(quán)法對“作者”的定義。對此,本文以國內(nèi)關(guān)于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諸多法律研究為基礎(chǔ),綜合探討了著作權(quán)中“作者”的認定標準以及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類型、特征,并結(jié)合現(xiàn)時法律對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著作權(quán)定性提出了幾點看法,以資參考。
關(guān)鍵詞 人工智能 著作權(quán) 法律定性
作者簡介:王力,內(nèi)蒙古科技大學文法學院。
中圖分類號:D923.4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5.111
所謂“人工智能”(簡稱“AI”),是指建構(gòu)在人類智能思維、行為、認知等層面上結(jié)合技術(shù)模擬,并以計算機軟硬件作為輸出介質(zhì)的一種新興科學技術(shù)。時至今日,人工智能除了在原有的科學領(lǐng)域大放光芒,在其他行業(yè)領(lǐng)域,如醫(yī)學、藝術(shù)、文學、歷史等領(lǐng)域的參與度也逐漸提升,但隨之所產(chǎn)生的相關(guān)問題也愈來愈多。為此,下文將就人工智能在創(chuàng)作領(lǐng)域所產(chǎn)出的“作品”著作權(quán)定性問題展開探討。
一、國內(nèi)關(guān)于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法律研究
AI技術(shù)的廣泛應用為人類社會帶來了一系列福音,但同時也產(chǎn)生了一連串的問題。對于AI的創(chuàng)作及創(chuàng)作物的法律定性就是擺在人們眼前的現(xiàn)實難題。如果將AI的創(chuàng)作物納入著作權(quán)法律的保護范圍,那么這就需要將著作權(quán)保護規(guī)則進行整體性的變更;如果不將其納入著作權(quán)法律的保護范圍,那么AI生成的作品又確實符合著作權(quán)法意義下的“獨創(chuàng)性”,不予保護顯然又于法有悖。且伴隨AI“獨創(chuàng)性”作品的利益歸屬是否需要法律以強制性規(guī)定加以保護,還是交由市場自行定義和解決等問題,也是其中突出難題。
圍繞這些問題的探討,國內(nèi)學者有著以下看法:有學者認為,AI所作用的領(lǐng)域,多數(shù)都是解決各類知識性的領(lǐng)域,而解決這些問題的技術(shù)主要通過現(xiàn)代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架構(gòu)下的大數(shù)據(jù),通過對這些數(shù)據(jù)的深度挖掘和關(guān)聯(lián)性分析,便可得出解決方案。而AI的存在基礎(chǔ),即在于人類利用自身智慧為其建構(gòu)了一個類似知識庫的系統(tǒng),AI通過極速檢索來進行任務、完成任務,一旦這個“知識庫”中沒有所謂的答案,AI也就無法完成任務。由此可見AI不僅是存在技術(shù)層面的限制,還受限于理解程度、學習能力等方面的限制。例如,在圖像處理、視頻處理、語音處理等方面的學習上仍然有著很多挑戰(zhàn)。因此其創(chuàng)作物并不具備“作品”的法定要件,不符合著作權(quán)法對于獨創(chuàng)性的要求。也有學者認為,之所以對著作權(quán)、專利權(quán)等知識產(chǎn)權(quán)予以法律的形式進行保護,根本目的就在于支持、鼓勵社會生產(chǎn)活動中的創(chuàng)造、創(chuàng)新。AI之所以被稱作“人工智能”,是因為其源于“人工”,是“人工”借助計算機、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等現(xiàn)代化科學技術(shù)的一種延伸,同時,AI在“人工”的驅(qū)動下,還會進行拓展訓練、深度學習,從而學會自我創(chuàng)作,而這些創(chuàng)作物又有著與眾不同的創(chuàng)造性、獨創(chuàng)性,那么賦予其知識產(chǎn)權(quán)意義上的法律保護,屬于應有之義。正如北大法學教授易繼明如是說:“AI的這種深度學習,也就類似于我們創(chuàng)作東西時出的汗,是否具有創(chuàng)造數(shù)據(jù)的權(quán)利性,就看它是否有出汗,這個汗出在誰身上,則權(quán)利就歸屬于誰。”所以,AI在深度學習后,自我創(chuàng)作的作品應當劃為演繹作品,通過鄰接權(quán)便可有效解釋AI創(chuàng)造物的權(quán)利歸屬問題。
二、著作權(quán)中“作者”的認定與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作者”認定
在司法實務中,但凡認定作品的權(quán)利及其歸屬,對其“著作權(quán)人”即作者的認定是基礎(chǔ),也是前提。從整體上看,作品屬于獨創(chuàng)性表達的直接產(chǎn)物,是建立在“人”的思維、情感和認知上的。那么,這一創(chuàng)作作品的權(quán)利歸屬以及“作者”的認定,自然應由其創(chuàng)作者享有。而從法律規(guī)定上看,現(xiàn)行著作權(quán)法中對于“作者”的認定也始終圍繞“人”的主體身份展開,同時兼顧對“人”在其創(chuàng)作作品中的貢獻值的考慮,即是否具備獨創(chuàng)性來進行綜合認定。此外,現(xiàn)行著作權(quán)法對于著作權(quán)權(quán)利的原始取得方式也限定了兩種途徑,即一是通過創(chuàng)作人自身的智力創(chuàng)作取得;二是在職務行為、委托行為等過程中,由特定的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組織基于法律規(guī)定或者合同約定取得。由此,基于這一角度來分析AI的創(chuàng)作物,可以看作是“一種具有高級智能的高級機器所創(chuàng)作的作品”。換言之,AI根據(jù)其內(nèi)部系統(tǒng)數(shù)據(jù)庫、知識庫所儲存的信息來進行創(chuàng)作,整個過程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都是經(jīng)由“人”的設(shè)定、安排,所以AI創(chuàng)作物在著作權(quán)意義上的“作者”,也應當歸屬于其創(chuàng)造者、設(shè)計者。
三、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類型及特征
著作權(quán)法保護的客體是作品,而所謂“作品”,也就是“人”的思維認知、理解表達以及情感融入等形成的、具有獨創(chuàng)性的產(chǎn)物。那么,AI創(chuàng)作物是否具有這些特征,存在哪些類型,學界有著以下共識:
關(guān)于AI創(chuàng)作物的類型,按照“是否存在深度學習產(chǎn)物”為標準劃分為以下幾類:一是源于人類智慧的直接產(chǎn)物,又稱“第一類生成物”。這一類型的AI創(chuàng)作物就是一般意義下的由計算機、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綜合作用下產(chǎn)生的作品,AI在整個作品的創(chuàng)作過程中僅發(fā)揮了輔助性作用,并未有超出程序設(shè)計、代碼指引的任何行為。二是非經(jīng)人類智慧形成的產(chǎn)物,又稱“第二類生成物”。這一類型的AI創(chuàng)作物的產(chǎn)生,并非僅在人類限定的范圍,或是建構(gòu)的知識庫中,而是基于這一前提,融入了AI的自我學習、深度學習等元素,AI是獨立的創(chuàng)作主體。
關(guān)于AI創(chuàng)作物的特點,按照AI的基礎(chǔ)運行原理來看,存在以下兩點突出特征:第一,AI創(chuàng)作物本身與人類自行創(chuàng)作的作品不存在差異性。AI創(chuàng)作作品的過程,主要是基于海量數(shù)據(jù)分析、相鄰數(shù)據(jù)解析和既定算法來完成的,因此創(chuàng)作物的信息內(nèi)涵、欣賞價值等和人類智慧獨創(chuàng)表達并沒有明顯的不同。第二,AI創(chuàng)作過程每一環(huán)節(jié)皆具高效性。在現(xiàn)代科技支撐下,AI借助超級計算機以及網(wǎng)絡(luò)云端數(shù)據(jù)交互、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等技術(shù)的綜合運用,使之創(chuàng)作的速度和效率是人類創(chuàng)作遙不可及的,同時,在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驅(qū)動下深度學習,能夠讓AI在極短的時間內(nèi)完成海量知識的學習,并形成更符合要求的作品,而這也是人類無法與之匹敵之處。
基于前述,目前AI在大多數(shù)領(lǐng)域還只是充當“工具”角色,尚未能全權(quán)取代人類從事全部的生產(chǎn)行為,但其發(fā)展從未停步。因而對其創(chuàng)作物的相關(guān)法律認定也亟待進一步形成共識,建立符合時代發(fā)展、市場需求的完善法律體系。
四、 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的著作權(quán)定性
判定AI創(chuàng)作物是否具有“獨創(chuàng)性”,是對AI創(chuàng)作物著作權(quán)進行定性的關(guān)鍵,同時也是基礎(chǔ)與前提。目前,學界 對于AI創(chuàng)作的作品有著對立的兩種聲音:一種認為AI的創(chuàng)作物只是“機械的匯編”,是任何一臺計算機,通過互聯(lián)網(wǎng)平臺和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以及演算設(shè)計都能夠創(chuàng)作出來的。所謂創(chuàng)作的一系列過程都是在既定模式控制下對現(xiàn)有信息資料的篩選和分析,然后根據(jù)人類口令指引進行組合排列,再按照現(xiàn)有的程序完成對最終結(jié)果的輸出。由此可見,AI的創(chuàng)作物都只是聽從人類的指令,對人類提供的資料信息進行篩選、分析和整理,其中沒有施加AI自身的思維創(chuàng)造,故應將其歸類于輔助工具。根據(jù)《著作權(quán)法實施條例》第三條第2項規(guī)定:“為他人創(chuàng)作進行組織工作,提供咨詢意見、物質(zhì)條件,或者進行其他輔助性工作,均不視為創(chuàng)作。”即,AI的整個“創(chuàng)作”過程并不符合著作權(quán)法意義上的“創(chuàng)作”,所以創(chuàng)作物的著作權(quán)應當屬于對AI設(shè)計和執(zhí)行指令的“人”。而另一種則認為AI能夠在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及多元技術(shù)的綜合運用下實現(xiàn)深度學習,所產(chǎn)生的第二類生成物具有自主性、獨立性,人類在創(chuàng)作過程中的介入程度較小,因此其創(chuàng)作物是具有“創(chuàng)造性”的。所謂神經(jīng)網(wǎng)絡(luò)下的深度學習,主要是通過其中“多層感知器”下的“input layer”、“hiddenlayer”、“output layer”(即:輸入層、隱藏層和輸出層)來完成對信息資料的海選、收集、提取以及分析、理解并輸出等工作。但經(jīng)這一過程的產(chǎn)物屬于“作品”還是AI的思想抑或情感的表達,學界對此又存在較大爭議。有學者認為,著作權(quán)法意義上的“作品”,也可以是通過一系列的情緒感知、情感表達形成的實質(zhì)產(chǎn)物,而這個產(chǎn)物也就是作品。正如前文所述,第二類生成物的外部表現(xiàn),與人類創(chuàng)作的作品并不存在明顯的差異性,而現(xiàn)行著作權(quán)法對于“獨創(chuàng)性”的要求,只在于“作品是獨立完成且具有最低限度的創(chuàng)造性”,但法律并沒有對這種最低限度的創(chuàng)造性作出明確、具體的定量標準和定性標準,僅是要求符合“質(zhì)”即可。由此可證,第二類生成物在深度學習后的產(chǎn)出物,即AI創(chuàng)作的“作品”應當納入著作權(quán)保護范圍。
總而言之,不論學界對于AI創(chuàng)作物著作權(quán)的定性如何爭論,也只是暫時停留在學術(shù)層面的探討研究上,要從立法層面來認定AI創(chuàng)作作品的權(quán)利及其權(quán)利歸屬,仍然存在相當多的阻礙和難題。例如,從著作權(quán)的權(quán)利屬性來看,著作權(quán)屬于人身權(quán)利,圍繞“人”而展開,AI雖然源于人工,能夠以“類人模仿”而植入一定程度的“人性”,但始終是非人類,故而很難賦予其人類專屬的“人權(quán)”。但從經(jīng)濟角度來看,AI發(fā)展至今,逐漸滲透至各行各業(yè),擁有極為廣闊的應用前景,能夠為人類社會帶來的發(fā)展以及經(jīng)濟利益提升產(chǎn)生足量的積極作用,但其研發(fā)和設(shè)計目前仍需相當大的資金投入,所以賦予其研發(fā)者、設(shè)計者應用著作權(quán)利以保障研發(fā)設(shè)計工作的有序進行,也是應有之義。
五、結(jié)語
綜上所述,AI的出現(xiàn)和應用是現(xiàn)代社會進步的直接體現(xiàn),也是各行業(yè)領(lǐng)域轉(zhuǎn)型升級的大好契機,但在這些發(fā)展進程中,不僅要重視科學技術(shù)對生產(chǎn)生活帶來的重大影響,還要關(guān)注如何制定與之相適應的法律法規(guī)。盡管目前對于AI創(chuàng)作物著作權(quán)的定性尚未出臺具體法律予以明確和規(guī)制,但相關(guān)問題的探討和研究已經(jīng)在學界如火如荼地進行。不論如何,法律作為調(diào)控社會、保障秩序的核心手段,應當在立法中兼顧多方利益,反復實踐,積極探索,以我國基本國情為根本,對AI創(chuàng)作物及其相關(guān)權(quán)利制定專門性的法律制度,有效保障AI設(shè)計者、研發(fā)者、使用者以及投資者等各方合法權(quán)益,進而推動社會各行業(yè)產(chǎn)業(yè)的健康有序發(fā)展,同時也為日后AI領(lǐng)域相關(guān)權(quán)利糾紛問題的解決奠定完善的法律基礎(chǔ)。
參考文獻:
[1]陸泉旭.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版權(quán)保護問題研究.法制與社會.2017(13).
[2]葉宗宗.人工智能與著作權(quán).法制與社會.2016(25).
[3]熊琦.人工智能生成內(nèi)容的著作權(quán)認定.知識產(chǎn)權(quán).2017(3).
[4]胡凌.人工智能的法律想象.文化縱橫.2017(2).
[5]劉曉莉.新媒體的人工智能作品對人類文化的影響.大連工業(yè)大學.2015.
[6]易繼明.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是作品嗎?.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7, 35(5).
[7]曹源.比較法和產(chǎn)權(quán)視角中的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中國版權(quán).2017(4).
[8]梁志文.論人工智能創(chuàng)造物的法律保護.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7,35(5).
[9]羅祥、張國安.著作權(quán)法視角下人工智能創(chuàng)作物保護.河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學報.20 17,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