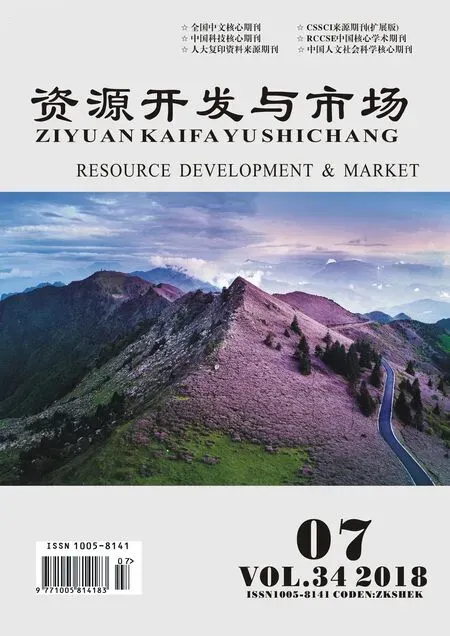區域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耦合協調分析
——以中國沿海城市群為例
,b
(中國海洋大學a.經濟學院;b.海洋發展研究院,山東 青島 266100)
1 引言
開發強度是土地利用程度及其累積承載密度的綜合反映,是區域建設空間占總面積的比例[1]。資源環境承載力是在一定時間和區域內,在保證資源合理開發利用和生態環境良性循環前提下,資源環境系統承載人口增長與經濟發展的能力[2],兩者作為主體功能區劃的重要依據,存在相互制約的動態耦合協調關系。近年來,隨著我國城鎮化與工業化進程的逐漸加快,區域開發建設強度不斷加大,開發建設方式愈發粗放,不可持續性問題日趨嚴峻。學者們運用日漸成熟的方法手段,對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研究開展大量工作。總體看,以全國、省域和省內為空間尺度[3,4],關注開發強度的時空特征[5]、資源環境承載力的時空特征[6]、開發強度與交通運輸的關系[7]、開發強度與碳排放的關系[8]、城鎮化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的關系[9]等內容,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省際地域單元,較少涉及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的耦合協調關系,且針對兩者協調發展影響因素的分析幾乎空白。
城市群作為直接參與全球競爭和國際分工的新型地域單元,是經濟社會發展進程中最具活力與潛力的增長點[10,11]。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和產業的集聚,城市群進入快速成長階段,城市群規劃方興未艾,城市群開發愈演愈烈,城市群成為人口集聚區、經濟集聚區和城鎮集聚區。然而,高速度成長、高密度集聚和高強度運轉的模式同樣產生資源消耗、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等問題,導致資源使用和污染排放比重越來越大,城市群成為生態環境問題頻發的重災區,制約著區域開發的有序進行、資源環境的高效利用與國土空間格局的合理優化。
針對此,本文以我國遼中南、京津冀、山東半島、長三角和珠三角五大沿海城市群為研究區,以1995年、2005年和2015年為時間點,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測算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的時空耦合關系,運用障礙度模型分析影響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協調發展的主要障礙因素,這不但有助于沿海城市群人口資源環境的均衡和經濟社會生態效益的統一,而且對中西部城市群開發質量的提升、開發秩序的規范和健康良性發展態勢的形成等具有重要參考借鑒意義。
2 指標選取與模型構建
2.1 指標選取與數據來源
基于區域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的已有研究[12-14],選取城市建設用地面積占市轄區土地總面積比重表征開發強度。從資源環境壓力和資源環境承壓兩方面綜合測評資源環境承載力,其中選取人口自然增長率、GDP年均增長率、人均水資源消耗量、萬元GDP能耗、萬元GDP工業廢水排放量、萬元GDP工業SO2產生量、萬元GDP工業固體廢物產生量表征資源環境壓力;人均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民人均純收入、人均水資源量、人均耕地面積、建成區綠化覆蓋率、工業固體廢物綜合利用率、污水集中處理率、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表征資源環境承壓。鑒于資源環境壓力包括人口增長壓力和經濟發展壓力,與資源環境承壓共同組成三維狀態空間軸,因此本文運用狀態空間法[15]計算資源環境承載力得分,并比較現實值與理想值。數據主要來源于1996年、2006年和2016年的《中國城市統計年鑒》。
2.2 耦合協調度模型
引入耦合協調度模型分析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彼此影響、相互作用、和諧一致的程度,全面測度兩者的交互耦合協調程度,公式為[16,17]:
(1)
式中,C為耦合度,其中0 引入障礙度模型對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協調發展的障礙因素進行診斷,以此確定各障礙因素對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協調發展的制約程度,公式為[19,20]: (2) 我國沿海城市群開發強度加速上升,1995年、2005年和2015年開發強度平均值分別為2.9976%、3.3553%和5.2944%,超過2030年4.67%的國土開發強度紅線。原因在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人口和產業向東部沿海集聚態勢不斷增強,受此影響,新城新區廣泛設立,城鎮建成區面積快速增長,土地城鎮化進程逐漸加快。其中,珠三角開發強度的增幅最明顯,由1995年的5.9397%增加到2015年的12.9686%。開發強度大小排序依次為: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山東半島>遼中南,其開發強度的平均值分別為8.5892%、4.8049%、2.1125%、1.9836%和1.4595%,可見改革開放先行一步的珠三角開發強度最大,人口密度、經濟密度和城市化水平均處最高一級,長三角作為我國最大城市群,人口規模水平最高,人口聚集能力最強,開發強度僅次于珠三角。在結構性與體制性深層次矛盾制約下,遼中南經濟發展呈現“斷崖式下滑”,人口紅利面臨枯竭,城鎮化增速減緩,開發強度處于最低一級。從53個城市來看,開發強度空間差異明顯,三個年份的標準差分別為5.3528、6.8626和9.4035,高值集中分布于珠三角和長三角沖積平原,深圳(35.6402%)和上海(35.0359%)開發強度始終處于最高一級,超過國際公認的30%的國土開發警戒線,這兩個城市基本沒有可供成片開發的土地資源,許多大型項目無法落地,后備建設空間潛力不足;承德(0.1172%)開發強度最低,這與其山谷地形限制、基礎設施滯后、自主創新能力不強等密切相關(圖1)。 圖1 沿海城市群開發強度的時空特征 我國沿海城市群資源環境承載力穩步上升,1995年、2005年和2015年資源環境承載力平均值分別為0.3636、0.4376、0.4411,低于資源環境承載力的理想值4.0395、4.8622和4.9012,說明沿海城市群資源環境承載狀況得到不斷提升且均處于可載狀態,其中長三角資源環境承載力增幅最明顯,資源環境承載力由1995年的0.3277增加到2015年的0.4240,環境治理力度增強、環境保護投資增加、生態修復工程實施等的成效顯著。沿海城市群資源環境承載力大小排序為珠三角>遼中南>山東半島>京津冀>長三角,平均值分別為0.4352、0.4230、0.4181、0.4102、0.3895。從53個城市來看,資源環境承載力空間差異相對較小且逐年遞減,標準差分別為0.05858、0.0733、0.0645,高于資源環境承載力指數平均值的城市數量分別為22個、30個、16個,占全部城市數量的41.51%、56.60%、30.19%,集中分布于遼中南、山東半島和長三角北部。其中,深圳(0.6806)資源環境承載力最高,通過主動對標全球生態環境標桿城市,執行一流的環保標準,運用一流的環保技術等,加大環保工作力度,使優良的生態環境成為深圳重要競爭力;肇慶(0.2738)資源環境承載力最低,內河涌黑臭現象明顯、湖庫水質有待持續改善、礦山開采導致水土流失加劇、環境監測與監察力度不夠等是制約肇慶資源環境承載力提升的主要問題(圖2)。 我國沿海城市群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的耦合度總體處于拮抗耦合階段,1995年、2005年和2015年的耦合度平均值分別為0.4275、0.3740、0.3924。沿海城市群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的耦合度大小排序為長三角>山東半島>珠三角>京津冀>遼中南,耦合度平均值分別為0.4506、0.4110、0.4079、0.3746、0.3458。從53個城市來看,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耦合度空間差異相對較小但逐年遞增,標準差分別為0.0657、0.0759、0.0766。1995年、2005年和2015年資源環境承載力高于耦合度平均值的城市數量分別為34個、25個、31個,占到全部城市數量的64.15%、47.17%、58.49%,其中北京、濟南、淄博、青島、揚州、鎮江、泰州、南京、鎮江等23個城市的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耦合度始終高于平均水平,相對集中地分布于山東半島、長三角和珠三角,深圳(0.4964)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耦合度最高,承德(0.1940)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耦合度最低,處于最低一級的低水平耦合階段,兩者相差2.56倍。 圖2 沿海城市群資源環境承載力的時空特征 我國沿海城市群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的協調度整體不高,以輕度失調類型為主,1995年、2005年和2015年資源環境承載力協調度平均值分別為0.3294、0.3209、0.3335,呈現較明顯的非同步發展特征。沿海城市群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的協調度大小排序為長三角>珠三角>山東半島>京津冀>遼中南,協調度平均值分別為0.3650、0.3394、0.3325、0.3109、0.2918。從53個城市來看,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協調度空間差異特征與耦合度空間差異特征完全一致,標準差分別為0.0695、0.0705、0.0753。1995年、2005年和2015年高于協調度平均值的城市數量均為24個,占全部城市數量的45.28%。其中,沈陽、北京、濟南、淄博、青島等22個城市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協調度始終高于平均水平,相對集中地分布于長三角和珠三角。深圳(0.6048)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協調度最高,屬于初級協調型;上海(0.5225)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協調度次之,屬于勉強協調型;承德(0.1981)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協調度最低,屬于嚴重失調型(圖3)。 圖3 沿海城市群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的耦合度與協調度 1995—2015年,各評價指標對沿海城市群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協調發展的障礙度差異較為明顯,平均值為∈[14.1680%,20.0023%],前五位障礙指標分別是人口密度(20.0023%)、人均耕地面積(20.0013%)、經濟密度(20.0004%)、城市建設用地占比(20.0003%)和人均公園綠地面積(20.0001%),可見開發強度是影響兩者協調發展的主要障礙子系統。其中:①人口密度是首要障礙因素。發達的經濟水平、便利的公共服務和便捷的交通運輸使大城市的“虹吸效應”突出,中小城市人口流失,沿海城市群人口畸形分布。其中,人口密度對遼中南障礙作用最強,地理位置較偏、經濟實力較弱、社會保障不足等加速了該區人口流失,出現“人才陷阱”與“北雁南飛”問題,加上超低生育率的影響,三個年份中遼中南人口密度分別僅為312人/km2、326人/km2和331人/km2。②人均耕地面積是第二大障礙因素。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使建設用地規模持續增加,大量耕地后備資源被開發利用,加上災毀和生態退耕等因素的影響,人均耕地面積不斷減少,土地壓力巨大。其中,人均耕地面積對珠三角的障礙作用最強,這與其土地面積不足且可墾率低、空間分布零散、耕地質量不高等密切相關,耕地資源緊缺成為其硬約束。③經濟密度、城市建設用地占比和人均公園綠地面積是重要的障礙因素。GDP增速作為政績考核的長期標準,導致忽視經濟發展質量,大城市利用政策支撐條件和配套服務設施等成為高經濟密度區,中小城市多是低經濟密度區,城市建設用地呈現低效、無序、快速擴張,人均城市建設用地水平參差不齊,城市公園綠地存在面積不足、配套設施陳舊、養護管理缺失等問題,不利于居民幸福指數的提升(圖4)。 圖4 沿海城市群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協調發展的障礙因子 本文運用耦合協調度模型和障礙度模型,對中國五大沿海城市群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的時空耦合協調關系特征及其障礙因素進行了量化診斷,得出以下結論:①中國沿海城市群開發強度加速上升,開發強度均值由2.9976%增加到5.2944%,超過2030年4.67%的國土開發強度紅線,珠三角開發強度最高,長三角開發強度次之,遼中南開發強度最低;53個城市開發強度空間差異明顯,深圳和上海開發強度處于最高一級,承德開發強度最低。沿海城市群資源環境承載力穩步上升,資源環境承載力均值由0.3636增至0.4411,低于資源環境承載力理想值,珠三角資源環境承載力最高,長三角資源環境承載力最低;53個城市資源環境承載力空間差異較小且逐年遞增,深圳資源環境承載力最高,肇慶資源環境承載力最低。②中國沿海城市群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的耦合度處于(0.3,0.5]的拮抗耦合階段,三個年份的耦合度均值分別為0.4275、0.3740和0.3914,長三角耦合度最高,遼中南耦合度最低;53個城市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耦合度空間差異相對較小但逐年遞增,深圳(0.4964)耦合度最高,承德(0.1940)耦合度最低。沿海城市群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的協調度整體不高,以(0.3,0.39]的輕度失調類型為主,三個年份的協調度均值分別為0.3294、0.3209和0.3335,長三角協調度最高,遼中南協調度最低;53個城市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協調度空間差異特征與耦合度空間差異特征完全一致,深圳(0.6048)協調度最高,承德(0.1981)協調度最低。③各指標對沿海城市群開發強度和資源環境承載力協調發展的障礙度差異明顯,平均值∈[14.1680%,20.0023%],前5位障礙指標是人口密度>人均耕地面積>經濟密度>城市建設用地占比>人均公園綠地面積,障礙度的平均值依次為20.0023%、20.0013%、20.0004%、20.0003%、20.0001%。其中人口密度是首要障礙指標,以對遼中南(41.5305%)障礙作用最強,人均耕地面積的障礙作用次之,耕地資源緊缺成為兩者協調發展的硬約束,以對珠三角(48.3592%)障礙作用最強,經濟密度、城市建設用地占比和人均公園綠地面積成為制約沿海城市群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協調發展的潛在障礙因子。 綜上所述,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的本質內涵較為深厚,推進兩者的協調發展是一個相對宏大的系統工程,城市群作為一種復雜的綜合集群體,實現其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保護的全面協同更是需要循序漸進。本文針對我國沿海城市群開發強度與資源環境承載力耦合協調及其障礙因素診斷的成果是較為初步的,今后應在區域選擇、指標構建、方法運用以及政策響應等方面應做進一步的探討與研究。2.3 障礙度模型

3 結果與分析
3.1 開發強度時空特征分析

3.2 資源環境承載力時空特征分析
3.3 耦合協調關系分析


3.4 協調發展的障礙因素分析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4.2 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