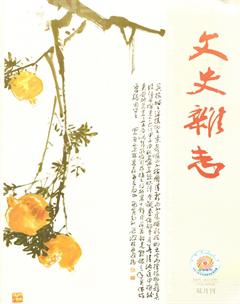都江堰與明朝首富
胡開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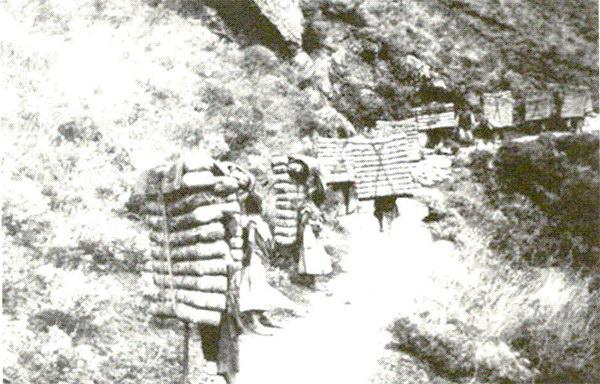


摘要:因?yàn)槊鞒慕騽澐郑冀咛幱谶吘车貐^(qū),其地位也隨之上升到國家安全戰(zhàn)略的層面。明代蜀府通過對(duì)都江堰灌區(qū)的系列管理,成為明朝首富。蜀府利用政策圈占灌區(qū)十分之七的土地,同時(shí)參與掌管茶馬交易,對(duì)都江堰周邊的外族人員和宗教采取優(yōu)撫政策,并不間斷地維修都江堰工程,表現(xiàn)出蜀府有一整套對(duì)都江堰灌區(qū)的經(jīng)營策略。蜀府按照朝廷的意圖,布置宗室人員居住在都江堰附近,這種安定一方的政策有效執(zhí)行了200年左右。隨著萬歷十年的勘界,蜀府經(jīng)濟(jì)實(shí)力下降,無法在明末力挽狂瀾。但古代首富的經(jīng)營策略和責(zé)任擔(dān)當(dāng)仍不失為都江堰的一筆寶貴文化資源。
關(guān)鍵詞:明蜀府;都江堰;王莊;茶馬交易;邊界
李冰開鑿都江堰,導(dǎo)江水以利航運(yùn),并最終確定成都城市的永久選址;同時(shí),使岷江水成為可控資源,“水旱從人,不知饑饉”之說雖稍嫌夸張,但灌溉之利在全國和全世界都是典范。李冰治水,功垂千古,受到灌區(qū)人民世世代代的敬仰,歷朝政府的尊崇,尊為“川主”。筆者初步調(diào)查,“川主廟”的數(shù)量在四川民間應(yīng)該僅次于土地廟。歷代朝廷對(duì)其封王晉爵,為之立祠塑像,以資紀(jì)念。現(xiàn)存最早的石像是東漢建寧元年(公元168年),蜀都水掾尹龍和都水長陳壹在都江堰渠首所立李冰石像。據(jù)《李冰及堰工石像出土紀(jì)實(shí)》,李冰石像立式,高2.9米,重約4.511屯,肩寬0.96米,厚0.46米,造型簡潔樸素,神態(tài)從容,平視而立,眼角和唇邊微露笑容,身著冠服,手置胸前。特別具有考證價(jià)值的是兩袖及衣襟上有淺刻隸書題記三行39字,字跡清晰,字內(nèi)珠砂猶存。中行為“故蜀郡李府君諱冰”;左袖為“東漢建寧元年閏月戊申朔二十五日都水掾”。右袖為“尹龍長陳壹造三神石人珍(鎮(zhèn))水萬世焉”。
都江堰對(duì)后世的影響是巨大的。在政治上,如戰(zhàn)國末年,秦國利用都江堰創(chuàng)建后方蜀地的富饒,取其布帛金銀供給軍用,以蜀中之兵,利用岷江航道順流而下得以滅楚,最后統(tǒng)一中國,建成了第一個(gè)封建集權(quán)制國家;蜀漢時(shí)“諸葛亮北征,以都江堰為農(nóng)本,國之所資”;西晉太康初年,晉將“王溶樓船下益州”滅了孫吳,結(jié)束了三國鼎立的局面;北周先期平定四川,為宋統(tǒng)一全國作了鋪墊;元朝繼續(xù)執(zhí)行這一策略,強(qiáng)攻四川,試圖先行控制長江上游,然后再進(jìn)攻南宋。而在經(jīng)濟(jì)上,都江堰對(duì)四川在全國的地位(從晚唐至南宋)逐漸升高亦居功至偉。
明代都江堰灌區(qū)很特殊。其時(shí)四川經(jīng)濟(jì)雖然始終沒有恢復(fù)到南宋的水平,但卻在明萬歷朝以前造就天下首富——蜀府。明朝王世貞的《弁州史料后集》中記錄了一段談資:嚴(yán)嵩的兒子嚴(yán)世藩經(jīng)常與朋黨談?wù)撎煜履軘?shù)得上的富人,他認(rèn)為“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家……所謂十七家者,己與蜀王、黔公、太監(jiān)高忠、黃錦及成公、魏公、陸都督炳,又京師有張二錦衣者,太監(jiān)永之侄也,山西三姓、徽州二姓與土官貴州安宣慰;積貲滿五十萬以上,方居首等”。在這個(gè)榜單中,宗藩中只有蜀藩,而且名列前茅。在譚綸的奏折中稱“蜀府之富甲于天下”;陸錢在其《病逸漫記》中認(rèn)為,藩王中“蜀府為最富,楚府秦府次之”;張瀚曾經(jīng)親自去過四川成都,在其《松窗夢語》中寫道“城中為蜀王府,其富厚甲于諸王”。這里第一則(嚴(yán)世藩之言)屬于私下的議論,后面三則卻是公開性的表述。嚴(yán)家的私產(chǎn)不敢或不愿意暴露,因?yàn)橛蟹N種限制,但蜀王富有,甚至首富,卻沒有人指責(zé)其有問題,這是一個(gè)很奇怪的現(xiàn)象。這跟都江堰灌區(qū)關(guān)系緊密,下面展開:敘述。
一、都江堰灌區(qū)襁蜀府占據(jù)十分之七
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四川巡按孔貞一上奏說,“蜀昔有沃野之說,然惟成都府屬,自灌抵彭十一州縣,開堰灌田故名焉。近為王府有者什七,軍屯什二,民間僅什一而已。”這份奏書是中性的,描述在萬歷十年(1582年)完成勘界后,蜀府仍然在都江堰灌區(qū)占有全部土地的約70%。但到天啟年間修《成都府志》時(shí),編撰者將這種現(xiàn)象定性為貶義,“腴田膏土盡是王莊,貧民或?yàn)楸说钁簦詢斪鈧颍艘嗵旄兄羁蓱懻摺!边@中間出了什么問題?筆者帶兩位學(xué)生在大邑縣圓通寺找到一塊文字缺失了的《西蜀正字山寺碑銘》(全文見第四部分),通過對(duì)它的解讀,將蜀府圈地變富、成為首富、再逐漸衰落的過程基本弄清。
從地區(qū)看,江浙一帶是明朝的主要賦稅來源地,四川地處邊遠(yuǎn)的西南,上繳賦稅的運(yùn)輸成本很高,主要任務(wù)是監(jiān)管茶馬交易,滿足國家用馬的需求。當(dāng)?shù)氐奶锏兀瑒t分為民田、屯田和王莊。總體而言,明代的王府莊田可分為兩種,“一種是受封以后出京就藩以前的養(yǎng)贍田和香火地;一種是就藩以后的藩國莊田”。宗藩獲得莊田的方式為“欽賜、請(qǐng)乞、納獻(xiàn)、直接侵占等”。由于明代皇帝賜予藩王莊田是從仁宗時(shí)期開始的,蜀府莊田應(yīng)該是直接侵占,以及后來的納獻(xiàn)。
碑文言“各掌印官查得本衛(wèi)各所,原無屯田。臨近州縣田土,委系本府王莊于分封時(shí)自行開墾”云云,其中“分封時(shí)自行開墾”在碑文中出現(xiàn)三次,顯然是特別強(qiáng)調(diào)其王莊土地的合法性。日本學(xué)者研究認(rèn)為,“明初,官方接受了大量的國有土地,其中既包括南宋后期以來就由官方占據(jù)的公田和元代由國家所有、軍隊(duì)開墾耕種的屯田,也包括元朝和群雄勢力遺留的無主土地。”而明朝初年的四川因宋元戰(zhàn)爭造成的損耗,導(dǎo)致地廣人稀,洪武四年(1371年)開始執(zhí)行“湖廣填四川”移民政策,給蜀府大量圈占和開墾土地提供了機(jī)會(huì)。朱椿的兄長秦王曾來信關(guān)心其生活,朱椿回給秦王的書信則說:“聞命之初,遣人親詣貴竹,葺廬舍以安其居止,辟土田以積其糇糧,凡百為備,不煩吾兄之過慮也。”朱椿是第二批被封王的王子。他說的意思是在洪武十一年(1378年)受封后,就仿效其他先期封王的兄長,開始安排身邊的人員到封地“辟土田以積其糇糧”。這個(gè)圈占土地的過程似乎到朱椿正式就國后還在進(jìn)行,如蜀府官員許淳在《蜀府重建秀山碑》中言:“洪武間,獻(xiàn)王分封之初,一聞斯境,遂捐儲(chǔ)蓄,鳩工命匠,始建一觀,名曰上皇。復(fù)建一寺,名日中峰。又構(gòu)一亭,名曰蜀府官山”。這個(gè)“蜀府官山”肯定要管轄周圍很多土地。結(jié)合巡按孔貞一奏書中的“王府有者什七”,可以看出其圈占的土地主要集中在成都平原最肥沃的土地上。
陳寶良先生認(rèn)為王莊有“管莊內(nèi)臣”和“管莊官校”兩個(gè)職務(wù),這個(gè)“管莊內(nèi)臣”在這里就是門正官里面的“蜀府正字”,而“管莊官校”則跟蜀府護(hù)衛(wèi)有關(guān)。嘉靖朝的譚綸任過四川巡撫,曾在奏疏中提到過這件事:“昔臣嘗奉先帝之命巡撫四川,見蜀國之富甲于天下諸王府,且又恪守祖訓(xùn),不敢一毫侵損于民。臣因求其致富之故,則由先年請(qǐng)去二護(hù)衛(wèi),而二護(hù)衛(wèi)之屯田屬焉。其征收子粒亦止如例,每遇水旱蟲蝗,輒又蠲免有差,特自蠲免之外,不復(fù)有升斗逋負(fù),遂因以致富焉。”蜀王自己說出富裕的原因,一是護(hù)衛(wèi)管理了原先三護(hù)衛(wèi)的屯田,也交待出最初圈占土地的人員,就是以那三個(gè)護(hù)衛(wèi)的2萬多人為主力(同理,另外的“軍屯什二”則被岷江上游松藩等處軍民指揮使司所圈占);二是蜀府總體上與佃戶的關(guān)系良好,遇到災(zāi)情,當(dāng)免則免,其他則沒有欠租的。這說明王莊佃戶租金不高,同時(shí)負(fù)擔(dān)的徭役也不重,這樣便調(diào)動(dòng)起佃戶的積極性,從而保證了交租。這也為后來的農(nóng)民主動(dòng)納獻(xiàn)土地、勘界后經(jīng)濟(jì)實(shí)力下降埋下伏筆。
當(dāng)時(shí),蜀府這么大的收入,并不為人忌妒,顯然其對(duì)收入的使用有它的合理性。首先是分配給宗室成員,讓其在基本爵祿外,還有一筆穩(wěn)定收入;作為代價(jià),則要安分守己,同時(shí)駐守都江堰一帶,為穩(wěn)定邊疆出力。其次是提高臣屬待遇,使之安心完成本職工作。最后就是為了保證成都平原的灌溉,蜀府從朱椿開始就非常重視都江堰水利工程,由此還培養(yǎng)了一位水利專家、明清漕運(yùn)制度的確立者陳碹(1365—1433)。最初蜀府派他去修堤防,“灌口都江堰壞,民苦水患。公修其堤防,躬督工作,為堅(jiān)久計(jì)”。結(jié)果陳碹不僅修得很好,還增加了水利經(jīng)驗(yàn)。嘉靖年間,蜀府出資重修灌口二郎神祠,“灌口舊有祠毀于火,蜀王為民軫念焉,出內(nèi)帑重建之。命承奉甯儀、周琦主其事用,殫心發(fā)慮,益宏闕觀。”都江堰建鎮(zhèn)水鐵牛時(shí),“蜀王聞而賢之,命所司助鐵萬斤,銀百兩。”另外每年出資作堰,是蜀府的慣例,“蜀府每年亦助青竹數(shù)萬竿,委官督織竹籠,裝石資筑”。這些都顯示蜀府對(duì)都江堰的關(guān)注是常態(tài),對(duì)灌區(qū)農(nóng)業(yè)發(fā)展幫助很大。同時(shí),蜀王通過巡視都江堰工程,也真切地熟悉農(nóng)民的生活狀態(tài)。懷王朱申鈘(1448—1471)寫過一首《憫農(nóng)》:“父子耕田須及春,扶犁荷種極勞神。鋤禾當(dāng)午衣流汗,誰識(shí)農(nóng)家最苦辛。”蜀府自覺肩負(fù)維護(hù)水利工程的責(zé)任,使普通農(nóng)民只需要安心耕種自家土地,這都是蜀府體恤實(shí)情,尊重農(nóng)人的表現(xiàn)。
二、都江堰是茶馬交易的重要通道
成都有民諺說:“搬不完的灌縣,填不滿的成都。”都江堰地區(qū)一直是成都重要的商品來源地和交易場所。明朝版圖比前代和后代都有所收縮,四川肩負(fù)穩(wěn)定邊疆和茶馬交易的重大責(zé)任。在整個(gè)明朝,蜀府始終重視并投入巨大的經(jīng)費(fèi)和人力于此。第一任蜀王朱椿到成都后就親自去巡邊。陳碹早年在蜀府任右衛(wèi)指揮同知時(shí),“從蜀獻(xiàn)王巡邊,招撫邊夷,兼理茶馬之政,邊人悅戴”。這次巡邊理論上涉及松潘、天全、馬湖等地區(qū),但南面有四川行都司帶領(lǐng)六個(gè)衛(wèi)所,兼管了天全一帶,而馬湖府也是朝廷重點(diǎn)經(jīng)營之地。由此可知蜀王巡邊后,長期經(jīng)營的重點(diǎn)是松潘地區(qū),這里涉及藏傳佛教、藏民羌民回民通道、茶馬交易、都江堰水源等。明成化重臣、有“西蜀小圣人”之稱的宜賓長寧人周洪謨(1420—1491)在《雪山天下高》詩中寫道:“巨靈擘斷昆侖山,移來坤維參井間。內(nèi)作金城障三蜀,外列碉硐居百蠻。”
《明實(shí)錄》記載,洪武三十年(1397年)朝廷改設(shè)秦州茶馬司于西寧,敕右軍都督:“近者私茶出境,互市者少,馬日貴而茶日賤,啟番人玩侮之心。檄秦、蜀二府,發(fā)都司官軍于松潘、碉門、黎、雅、河州、臨洮及入西番關(guān)口外,巡禁私茶之出境者。”為了切實(shí)解決問題,朱元璋專門派駙馬去向朱椿傳達(dá)指示:“秦蜀之茶,自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無此。邇因邊吏譏察不嚴(yán),以致私販出境,為夷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于唐而盛于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制戎狄之道,當(dāng)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我國家榷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紅纓雜物,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夷狄哉。爾其諭布政司都司,嚴(yán)為防禁,無致失利。”為此,朱椿親往實(shí)地調(diào)查并作了制度性的安排。《明史·蜀王椿列傳》載:“前代兩川之亂,皆因內(nèi)地不逞者鉤致為患,有司私市蠻中物,或需索啟爭端。”茶政的關(guān)鍵是要防止“馬貴茶賤”,同時(shí)又要和睦邊疆。《崇慶縣志》載:“蜀府正字禁葬碑,在縣北蓮經(jīng)庵前,正字,官名也,寺為蜀府正字轄,認(rèn)辦貢茶。”這說明蜀府管理王莊的機(jī)構(gòu)名為“蜀府正字”,同時(shí)還兼辦茶政。朱椿不僅要求布政司妥善安排,還創(chuàng)辦“蜀府正字”辦茶,兩家形成良性競爭,從而杜絕了私茶擾亂市場的行為,既達(dá)到國家易馬的目的,又讓“邊人悅戴”,顯示出其眼界開闊,施政策略符合實(shí)際而成效卓著。明朝后期松潘一帶之所以能成為國家最重要的茶馬交易通道,蜀府應(yīng)該做了很多有益工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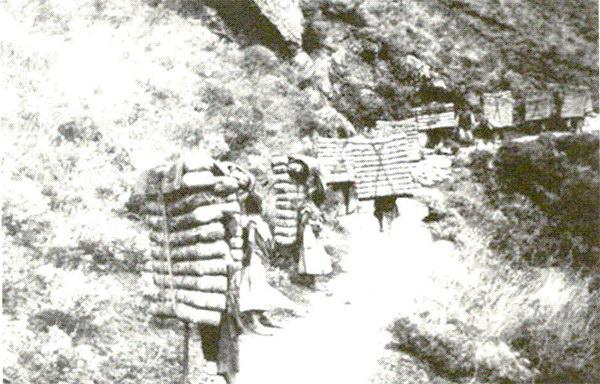
茶馬古道上的背夫(法國方蘇雅攝于1899—1904年)
歸納起來,蜀府成為萬歷朝之前天下首富的經(jīng)濟(jì)來源主要有三點(diǎn):1.因?yàn)槊鞒跞松俚囟啵齑痪蛧氨闩勺约旱膶傧潞妥o(hù)衛(wèi)圈占了都江堰灌區(qū)(成都平原)大量優(yōu)質(zhì)土地;2三護(hù)衛(wèi)最初的屯田,在將中、右兩護(hù)衛(wèi)交還中央后,又成功申請(qǐng)將其屯田全給留下;3.受朝廷指派辦茶,掌管部分茶馬交易,并從中獲利頗豐。這三宗經(jīng)濟(jì)來源都很巨大,遠(yuǎn)遠(yuǎn)超過蜀府掌管的成都少量小稅種收入,而且比得賜《鴻寶之書》而獲“煉金術(shù)”之說更可信。
明蜀王文集(其中朱椿《獻(xiàn)園睿制集》四冊)
三、都江堰周圍是人員和宗教的邊界
朱椿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到成都。成都西部山壩交接處“夷猓雜居”,且常受羌人騷擾。就在朱椿至成都前不久,汶川、茂州羌人聯(lián)合“生番”(指藏族人)叛亂,“約日伏兵臨城”,一度占領(lǐng)灌口。藏羌人“出沒為寇,相沿不絕”“叛復(fù)無常,誅賞互見”。(以上引文俱見于《明史·土司傳》)朱椿帶領(lǐng)四川行都司指揮同知陳碹等巡視灌縣、崇慶等地沿山一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