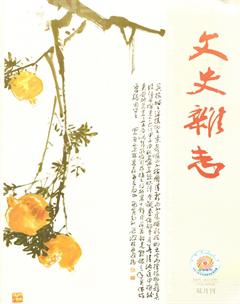四川地區的彌勒造像與明玉珍政權的“只奉彌勒”關系探討
方珂



摘要:彌勒是佛教中一個重要的神祇。四川地區的石窟造像中,自南北朝時期就有了彌勒造像,但多是遵從彌勒上生之信仰。至唐朝武則天執政后,彌勒下生信仰開始流行中國,四川地區也是如此,其后的造像多為彌勒下生之造像。但至南宋以后,彌勒信仰開始脫離佛教體系,四川地區彌勒造像中出現了各種不合經文的組合。明玉珍在元末入蜀后,正是見到彌勒信仰已成為單獨體系,乃“去釋老二教,只奉彌勒”,暗含自身乃彌勒下凡拯救眾生之意,借以在下層百姓中提高其政權的合法性。
關鍵詞:四川;石刻;彌勒;明玉珍
據黃標的《平夏錄》中所載,明玉珍(1331—1366)在重慶建立大夏國(1362—1371年)后,“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在正德《四川志》卷二十七《經略下·割據》中亦有夏政權“去釋老二教,只奉彌勒”之言。那么,為何夏政權只供奉彌勒,本文從四川地區現存的彌勒石窟造像作一探討。
一、巴蜀地區彌勒造像流變
巴蜀地區有彌勒造像比較早,最早可追溯到南北朝時期,現今見到的有明確題記的彌勒造像乃藏于四川博物院。據傳,它在1921年發現于四川茂縣縣城東門外較場壩中村寨西南,時有南齊永明元年(公元483年)造像題記,內容為:“齊永明元年歲次癸亥七月十五日,西涼曹比丘釋玄嵩為帝主臣王、累世師長、父母兄弟、六親眷屬及一切群生,敬造無量壽、當來彌勒成佛二世尊像。愿一切眾生發弘曠心,明信王寶,翟修十善,遭遇慈民,龍華三會,聶豫其昌,永去塵結,法身滿足,廣度一切,共成佛道。比丘釋僧成摻□□□共成此□”。另外,1995年5月,在成都市西安路中段東側的工地中發現一批南朝石刻造像,有8通佛教造像,1通道教造像。編號為H1:1的造像石上有此一段銘文:“齊永明八年庚午歲十二月十九日比丘釋法海與母為亡父造彌勒成佛石像一軀,愿現在眷屬七世父母龍華三會口登初首,一切眾生普同斯愿”,這是公元490年的造像。還有一龕公元541年的彌勒造像,是武陵王蕭紀為其父母所造,據傳1902年出土于成都西外佛寺,題記為:“梁大同七年,太歲辛酉六月乙未朔十三日庚辰,武陵王蕭紀為亡父母敬造彌勒一軀,供養興國寺。上為皇帝[陛)下,國土康寧,兵災永息,為[愿]七世父母乖出六塵,道生[佛]國,早登凈境,現存眷屬常[與]善居一切眾生,咸同斯福”。從這些發愿文中我們可以看到,“龍華三會”“永去塵結”“乖出六塵”“早登凈境”這些詞,明顯是指上升仙宮,可見是依據《彌勒上生經》而來,證明當時四川地區流行的是彌勒上生信仰。
隋代由于時間太短,在四川地區有紀年的造像寥寥無幾,未發現明確題記為彌勒的造像。
到唐朝的時候,彌勒造像更為流行。大足石刻中有紀年的最早的造像——尖山子造像第7號龕即為彌勒造像,題記為:“永徽口年八月十一日”。(按:“永徽”年號為公元650—655年。)造像內容為彌勒佛與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從這些人物身份來看,應該還是屬于《彌勒上生經》范疇。這是唐代初期的情況,但是不久就發生了變化。《資治通鑒》記載,天授元年(公元690年),“東魏國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經》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生,當代唐為閻浮提主,制頒于天下”。此本政權更迭的宣傳之說,但是可以看出彌勒作為佛像之一,在當時的政權與民間是有廣大信仰基礎的。而且,可注意到這時出現“彌勒下生”之說,而其依據《大云經》,又稱《大方等無想經》,是北涼時期的曇無讖在敦煌所譯經,其中并未提到彌勒,當是奔競小人托借此經之名,附會彌勒。《舊唐書·姚璃列傳》載:“證圣初,瑤加秋官尚書、同平章事。是歲,明堂災,則天欲責躬避正殿,璹奏曰:‘此實人火,非日天災。至如成周宣榭,卜代愈隆;漢武建章,盛德彌永。臣又見《彌勒下生經》云,當彌勒成佛之時,七寶臺須臾散壞。睹此無常之相,便成正覺之因。故知圣人之道,隨緣示化,方便之利,博濟良多。可使由之,義存于此。況今明堂,乃是布政之所,非宗廟之地,陛下若避正殿,于禮未為得也”。孟浩然的《臘月八日于剡縣石城寺禮拜》一詩云:“石壁開金像,香山倚鐵圍。下生彌勒見,回向一心歸”,均可印證彌勒下生信仰流傳之廣。在廣元千佛崖的第493號窟(俗稱“神龍窟”)造像內容即為彌勒像,其造像記為:“神龍二年三月八日[還]□□轉運使敬造供養兒田[周]敬造,兒田□敬造,兒田[壽]敬造”,即是公元706年所造,據《廣元千佛崖石窟調查記》言,這是廣元千佛崖中惟一有明確紀年的開窟題記。造像內容為一單獨的倚坐彌勒,是典型地遵《彌勒下生經》之儀軌而開鑿。《彌勒上生經》之造像在唐代四川地區逐漸為《彌勒下生經》造像所取代,但并非沒有例外。在開元三年(公元715年),巴中西龕第10號龕出現有題記:“菩薩圣僧金剛等,郭玄亮昆季奉為亡考造前件尊容,愿亡考乘此微因速登凈土彌勒座前同初會法口開元三年歲次乙卯四月壬子朔”。值得注意的是,此龕出現的彌勒像乃是彌勒凈土造像,仍屬《彌勒上生經》之間閾。在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著名的樂山大佛完工。其自開元年間始鑿,至此已歷90余年,《嘉州凌云寺大佛像記》碑文中記載:“開元初,有沙門海通者,……以此山淙流激湍,峭壁萬仞,謂石可改而下,江可積而平,……有是崇未來因,作古佛像”。這里可看出,樂山彌勒佛的開鑿,一是積石沉江以平湍流,二是“崇未來因”,信仰彌勒,既有現實的功用,也有來世的功德,而且也僅是彌勒單身造像,必是《彌勒下生經》內容。到乾符四年(公元877年),在綿陽魏城鎮的北山的“大佛寺”,其第1區第2號龕與3號龕之間,有造像記云:“敬造彌勒大像一[軀]竊聞大像出現與日月之同明生□……太乾符四年十月二日造佛舍俗□”。這里所言的“一[軀]”,毫無疑問也是屬于《彌勒下生經》,而且,此處已明確提到“大像出現與日月之同明”,應出自《佛說大阿彌陀經》:“第二十四愿。我作佛時,我頂中光明絕妙,勝如日月之明百千億萬倍。不得是愿終不作佛”。作為元末“明教”發端的信仰彌陀凈土的白蓮教,教義正是與此有關。
五代時期的前蜀乾德六年(公元924年),廣元千佛崖第365號龕的一則裝修記為:“女弟子越國夫人路氏幸因巡禮柏堂切睹此彌勒尊佛并諸菩薩悉皆彩色暗昧,遂乃發心,重具裝嚴,已蒙成就神變無窮威光自在,奉為亡過先靈父母一切眷屬承此功德,見佛聞法離苦下脫然后愿國界安寧法輪常轉無諸災障行住吉祥門宅清泰并已(字漶)同(字漶)”。其妝修人對佛像所承載的愿望,包括亡父母、眷屬、國家、自己及家人,幾乎可以說無所不說,從生到死一體包攬。這里面既有亡屬,亦有在世人,似已看不出彌勒上生和彌勒下生的區別。

僧伽法師(泗州大圣)彩繪石雕像(北宋造,在大足北山石窟)
北宋時代,四川地區有題記的造像無多,筆者之寡陋,未見到題記為彌勒的造像。至靖康元年(1126年),在大足北山石窟的第176號龕和177號龕中出現了彌勒和泗州大圣合龕的造像,題記為:“本州匠人伏元俊男世能鐫彌勒泗州大圣時丙午歲題”。“泗州大圣”即僧伽和尚,《宋高僧傳》卷十八有傳。在于君方所著的《觀音——菩薩中國化的演變》中這樣描述僧伽的演變過程——“到了宋代初期,僧伽顯然已從高僧轉化為神僧。他不僅被視為十一面觀音的化身,而且是泗州當地的守護神”。其后又敘“此外,僧伽信仰擴及中國各地,不僅泗州。他不但是淮河之神,航行于中國沿海及境內其他河川的人也對他奉若神明”。在《宋高僧傳》中也敘述為“天下凡造精廬必立伽真相。榜日大圣僧伽和尚。有所乞愿,多遂人心”。這樣看來,至少在宋代初期,僧伽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成了風靡天下的佛教膜拜對像,甚至轉化為觀音。但是泗州大圣與彌勒同鑿一龕(雖是兩龕,并為一龕)之中,說明彌勒信仰在當時仍是等同觀音的重要信仰,可這顯然已經脫離經文了。在南宋紹興二十年(1150年)左右修建的大足北山白塔(也稱“多寶塔”)中,有許多關于佛教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的內容,其中有一龕“參禮彌勒菩薩龕”,乃是一位叫邢信道的道人所造。道人修佛塔并建彌勒菩薩像,表明民間并未重視佛道之別,只是將其作為一位神靈而崇拜。在重慶合川區的淶灘摩崖石刻中,其以禪宗造像為主,除釋迦與禪宗六祖像外,還有彌勒狀的釋迦牟尼像,有達摩、須菩提、彌勒大士組合像,已完全不是經變,創意自由而多變,說明彌勒已并非佛教經典中的佛像,而只是民間一尊重要的神靈,《彌勒下生經》已經被無視。
唐代樂山大佛(彌勒坐像)
二、元末明玉珍政權的宗教政策
迨入元朝,由于漢民族對蒙古貴族政權的不滿,自南宋以來發展迅速的民間秘密結社組織——白蓮教更為蓬勃發展,以致元廷在至大元年(1308年)“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人還隸民籍”,至治二年(1322年)“禁白蓮佛事”。但即使如此,仍無法阻止民間群氓的趨之若鶩。范立舟先生說,由于白蓮教實際上是借天臺宗而歸凈土宗,信仰彌陀凈土,但是彌陀凈土中并無可下凡間拯救眾生之人,于是,在元代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激化的社會背景下,白蓮教開始與有可拯救凡間的彌勒凈土結合,以摩尼教或明教之新形式出現。元朝晚期,彌勒成為最為民間大眾所接受并傳播的神靈崇拜。《元史·泰定帝本紀一》載:“息州民趙丑廝、郭菩薩,妖言彌勒佛當有天下,有司以聞,命宗正府、刑部、樞密院、御史臺及河南行省官雜鞫之”。《元史·順帝本紀五》載:“至(韓)山童,倡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于是紅巾軍起義大爆發,群雄并起,元朝土崩瓦解。據《玄宮之碑》記載,紅巾軍首領明玉珍為隨州隨縣(今屬湖北)人,“不嗜聲色貨利,善騎射”;《平夏錄》又說:“鄉間有訟,皆往質焉……玉珍乃團結里中人,屯于青山,眾推為屯長”,顯然其人不是佛道教徒。筆者認為,明玉珍本人因有“俠氣”,可能接觸佛教和道教極少。在元末戰爭中,他先從徐壽輝,而徐壽輝乃是倚彌勒教而起事,因此,明玉珍受到彌勒下生之影響應是不言而喻的。其入據巴蜀后,擊敗元軍在巴蜀勢力及李喜喜青巾軍余部,上層政權已無憂。為鞏固政權合法性,取得下層人民支持,需要一廣為百姓大眾所接受的宗教偶像來籠絡人心,這正如武則天即位前所倚靠《大云經》一般。這時,作為“轉輪明王”出世下凡的彌勒,既是最熟悉,也是最合適的選擇。如本文前面章節所述,自南北朝時期至南宋,四川地區的彌勒造像綿延不絕,彌勒信仰有極廣的信眾及影響力;最為重要的是,僅就該地區而論,彌勒造像早已脫離佛教經軌,只是作為和觀音(或泗州大圣)一樣的能及時拯救世人的一尊重要的神祗而已。所以,大夏政權才能“去釋老二教,止奉彌勒”(若彌勒仍在佛教經軌中,這樣就行不通)。而夏政權將領鄒興在重慶南岸的彈子石開鑿的一尊彌勒造像,其像除一高近8米的彌勒倚坐像外,另有兩脅侍弟子。這與四川地區其他的《彌勒上生經》與《彌勒下生經》造像皆不符合,反映了彌勒造像已基本演變出佛教范圍。
至于明夏政權為何“去釋老二教”,筆者認為乃是自宋以降的佛、道二教,已多半為民間俗流所利用,脫離其勸善修行之本意。如《明實錄.太祖實錄》卷二百九載:“(洪武二十四年六月)丁巳,命禮部清理釋、道二教。敕曰:‘佛本中國異教也,自漢明帝夜有金人入夢,其法始自西域而至。當是時,民皆崇敬,其后有去須發出家者,有以兒童出家者,其所修行,則去色相,絕嗜欲,潔身以為善。道教始于老子,以至漢張道陵能以異術役召鬼神,御災捍患,其道益彰。故二教歷世久不磨滅者以此。今之學佛者曰禪曰講曰瑜珈,學道者日正一曰全真,皆不循本俗,污教敗行,為害甚大……”《明史·職官志三》載:“(洪武)二十四年,清理釋、道二教,限僧三年一給度牒。凡各府州縣寺觀,但存寬大者一所,并居之。凡僧、道,府不得過四十人,州三十人,縣二十人”。顯而易見佛、道二教在朱元璋制定宗教政策之前,已不符合統治者的期望,從而以行政制約嚴密細致地限制了民間宗教的泛濫。明玉珍又何曾不是如此。至于明夏政權“只奉彌勒”,筆者認為乃明玉珍自視為下凡彌勒,以杜絕民眾更借彌勒信仰的名義集社,從而產生新的不穩定因素。《明實錄》中記載有多處借“彌勒”信仰而為僭偽事:
1.“(洪武十九年五月)戊辰,妖僧彭玉琳與新淦縣民楊文曾、尚敬等謀作亂。事覺,伏誅。玉琳福建將樂縣陽門庵僧初名全無用,行腳至新淦,自號彌勒佛祖師,燒香聚眾,作白蓮會。縣民楊文曾、尚敬等皆被誑惑,遂同謀為亂。玉琳稱晉王,偽置官屬,建元天定。縣官率民兵掩捕之,檻玉琳并其黨七十余人,送京師,皆誅之”。
2.“(洪武二十五年六月),袁州府宜春縣民李某妄稱彌勒佛,發九十九等紙號,因聚眾謀作亂。戍卒楊寅告于袁州衛,衛發兵捕斬之,獲其偽造木印龍鳳、日月袍、黃綠羅、掌扇令旗、劍戟凡百余事”。
以此看來,即使到較為安定的洪武后期,民間仍往往借“彌勒”之名而欲行陳、吳之事,成為統治者之大忌。明玉珍建立政權之初,也曾面臨這樣的問題。他為了防備民眾有異心,而加強政權的政治凝聚力,自稱“彌勒下凡”,以阻平民受其他說誘。而明玉珍在四川地區所行政績,也基本符合其愿望。《明史·明玉珍列傳》稱其“既即位,設國子監,教公卿子弟,設提舉司教授,建社稷宗廟,求雅樂,開進士科,定賦稅,以十分取一。蜀人悉便安之”。
三、結語
總全篇而言之,古代四川地區彌勒造像眾多,且自南北朝至南宋綿延不絕;民眾從最初的彌勒上生信仰,至唐代武周代唐后轉變為彌勒下生信仰,以后更轉化為完全脫離經軌的自由信仰,勾勒出彌勒信仰在民間從盼升天界為神到重凈土,最后輕經文的演變軌跡。而元末起事群雄乃利用彌勒下生信仰而結眾。明玉珍入蜀后,正是看到佛、道二教在民問因流俗變化為害較大,而彌勒信仰已基本脫離佛教,乃“去釋老二教,只奉彌勒”,將自身作為彌勒下凡的化身,以穩定政局,維護政權的合法性,并打擊其他彌勒之說誘引平民作亂的企圖。明玉珍在實際的政策制定和執行中也確實取得了使巴蜀人民生活和平安定的效果,使得明初以前的四川成為欣欣向榮之區。
明玉珍塑像(在重慶江北區睿陵陳列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