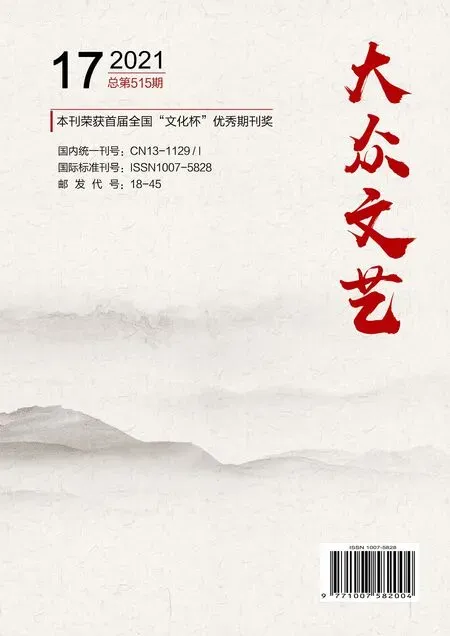“啟蒙”何以可能?
——談王安憶《啟蒙時代》
《啟蒙時代》宏大背景、頗具舞臺感的寫作確實充斥著吸引力,王安憶于焦灼不安的筆觸下裹挾著驚駭,在追求宏大的雄心與現實的自我認知構成的情感間隙中,涌動著一股力量,在啟蒙可能性的探尋中,注入了一抹暖意。既是啟蒙可能性,率先指向的是“啟蒙”概念,進而探討可能性問題,由此導向與現實的關聯。
一、何謂“啟蒙”?
從《思想者》到《啟蒙時代》,回到“啟蒙”本身,可見王安憶對于“啟蒙”的再定義。究竟什么是“啟蒙”?傳統的認知大致是,通過理性擺脫個體的蒙昧狀態。對概念的理解不止于此,應將概念注入多維度的思考,比如王安憶的“啟蒙”,是個人自覺還是集體覺醒?是精英的召喚還是人與人間的相互激發?誰是啟蒙者,誰又被啟蒙?
張旭東在《對話啟蒙時代》中提及,“啟蒙這個概念本身就帶有自我批判的傾向。每個人的人物都是群像式的,每個人都有來歷,都有各自社會事,風俗史上的地位,都帶著自己的問題進入了故事,這種帶有總結性味道又有點實驗的意思,中國革命的第二代如何從概念的領域落實在生活領域。怎樣從國家到社會,從思想到行動,從書本到實際,從自以為社會自我為中心,到理解這個世界有機的復雜的關系,這是一個集體寓言。”1王安憶在不同的個體與人物關系間穿插游走,她所塑造的個人是帶有王安憶性質的個體,她賦予人物以任務,而任務可能超越了個體,直接與時代相勾連。比如“小老大”,他的表達欲與苦悶宣泄,是用病理超脫自身的精神束縛,而被賦予的任務則是把南昌從教條主義中脫離出來。這類任務是一種結果導向,它并非個體的欲望,而是王安憶的個人體察和對時代的體認,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反個人的,也正是在反個人的過程中,王安憶建構了人物的邏輯合理性。
在《啟蒙時代》,“啟蒙”的觀念曲折的走向進化論,即便它看上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織的循環過程。羅崗教授認為,王安憶的“啟蒙”表現為“拜師傅修行”。關鍵問題在于,如此“修行”,能否實現對教條的抽離?在“邊緣”的群體中,個體間的理解與信任是否可能?“小老大”、校長、高醫生等人,他們擔當著個人甚至時代意義上的啟蒙者,這種自覺性是否顯得理所應當?在階級矛盾激化、苦悶感叢生的時代,“人往高處走”無疑是值得質疑的。那些原地踏步,甚至倒退的,或者不能承擔任務的啟蒙失敗,在人物的退場中被遮蔽。
誰啟誰的蒙?不只是個體意義上的啟蒙,如張旭東所言:革命啟蒙社會。在王安憶的作品中,“啟蒙”的表現之一是對于父子關系的再認識,即重新審視和理解父輩,進而理解自身的背景和起源。假設融入感性去分析,如此審視導向的往往不是對父輩的情感體認,而是一種潛在的逃離與回避,這是當代價值觀不大認同的脈絡。另外,在融入歷史感之余,以同情的態度去看待問題,反思上帝視角與現代/傳統倫理觀的規訓,也不失為一種良好的嘗試。
二、時代能否走向“啟蒙”?
《啟蒙時代》指向“文革”初期,王安憶的“向后看”本質上是一種再加工。這種再加工導向一種審視、反思與批判,小說的細節愈完備,調動“意識”的加工意味便愈濃。吳曉東在《記憶的神話》一文中提及,“在所有的美學中,記憶的美學無疑是最具蠱惑性的。”2這里的蠱惑性便在于把真實感當作一種真實。不僅是個人,集體性的回憶也難免與真實有著偏差。洪子誠在《兩憶集》中寫道:“記憶只有借助已被‘雕刻'過的時光,依靠集體記憶形成的標志性事件和闡釋框架才能有效,本想通過‘返回'而發現新意義,在‘大敘述'之外,提供一些‘次要'的參照或者補充,到頭來卻發現已不自覺落入到現成的‘圈套'之中。”3通過情感與時代歷史再塑的回憶,也會落入某種敘事圈套,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回憶與再塑都背負著局限。
梳理側影60-70年代。“文革”時代,革命者之間有著內在的派別,對于集體觀念的強調,成了那個時代貫穿的印記,革命與不革命之間,似乎沒有中間的道路可去。章詒和的《往事并不如煙》,“歷史從來沒有什么東西是突如其來的,其中不為人知的原因恐怕是已醞釀多年的。”4革命的產生,脫離不開舊有的階級矛盾纏繞,它映襯著集體的理想與現實的局限,新中國怎樣能傲于世界之林,傳統的弊端、舊有的階級矛盾如何緩解,資本主義理念如何滲透,又可以通過誰來消除?整體上,無產階級的合法性呈現出一種焦慮。
人物群像書寫的過程,也是王安憶尋找可能性的過程。誰能承擔起社會責任?誰可以擔當啟蒙者?誰又是精英人物?從王安憶分割的文章模塊來看,對人物似乎有一定的拋棄:當下的可能性結束,人物便被安排命運,暫停書寫。對此,王安憶本身也有著無奈,啟蒙未完成的焦灼促使王安憶進行人物之找尋,特性之挖掘。對于筆下人物,她并非完全的旁觀者,發揮想象力的時刻,必然逃脫不開自身的情感體驗。王安憶對此體驗是一種批判性的審視態度,即知曉自身的局限,又不愿拘泥于此,在承認局限的過程中完成一種心安理得。
是否有這樣一種可能,中國的知識分子不可能完全的放棄“主體性”。是否正如《對話啟蒙時代》王安憶之言,留下了一種理性與感性交織的可能空間。費正清的《觀察中國》,提到中國人比其他世界的人民具備更強的文化統一性。這種觀察本身富有啟發性,在這個層面上理解《啟蒙時代》,王安憶的維度更多的是“自下而上”、甚至平行視角,在時代的舞臺中掀起個人主義的波瀾。她的小說充斥著一種革命想象的想當然,小說自身假定的前提是:外在力量、生活力量很強,而自我的規訓,比如說陳卓然的大量閱讀,往往是機械的、效果不大好的,在王安憶筆下,自律從屬于大時代。
由此延伸的問題是,通過外在非個人的力量尋找個人,由此塑造出來的是否是真正意義上的個體,抑或是一種涵蓋共性的個體?那么由此可見的“公”與“私”間的關系該怎么理解?
三、“公”與“私”問題的現實反思
“公”與“私”間的關系處理是值得想象的問題。回到問題本身,王安憶試圖處理“主體性”被壓抑下的可能性問題,同時對于空洞的“理念的世界”,呈批判之意。這樣的形式顯現著內在的緊張感。
對比當下,《啟蒙時代》頗有些“借古諷今”之感。在張新穎的對話錄中,顯現著王安憶對于現代人快節奏、物質化生活的不滿——過于緊張的生活流失了深入思考的維度空間。在這個意義層面,《啟蒙時代》涌動著批判性反思,我們當下是否愿意直面這個時代,能否正視自身思想的不足,以及在節奏不斷加快的今天,那些成為熱衷于時代的思想者、“學習型社會”是否可能?
“學習型社會”的書寫呈現出的快感無疑是種幻覺,人在集體中,跟隨著“集體無意識”行動與言說,人的自覺與能動性將讓位于集體。在南昌學術探討的過程中,私人空間受到擠壓,個人的觀念選擇性的收斂,所幻想的、可隨氣氛改變的集體標準成為主流,主體依照該標準進行思想與言說,這就遮蔽了自身的學術思維空間,因而真正的思考只能在私人空間中完成。
在導向“市民—革命”一體論之時,王安憶的視野的確拓展了探討空間,那些可能性被遮蔽的角落乘著烏托邦色彩浮現。對于南昌,他的革命性與身份/認同是共同推進的,很難把二者剝離。南昌是從集體的人贊揚中,而非從實現個人目標或者其他個人的享受中得到滿足,在這個程度上,南昌的“啟蒙”有可能不在于自覺,而是得益于自身的邊緣身份,以及同為邊緣群體的無形肯定與認同。他的私人空間在小說中很少被呈現,他的“成長”更像是單方面的“公”所給予,在被塑造的、私人空間被擠壓前提下,南昌不可能有真正主體性的思考。
“學習型社會”必須建立在“公”與“私”的協調之上,二者相互擠壓,同時又相輔相成。過分強調“公”與“私”間的二元對立,或單一的敘述“公”、“私”,其本身是帶有偏見的視野,也可能流入一種意識形態。在當下的學術視野中,盡可能的多元,而非單一的思考問題,它能更添概率,去發現被遮蔽的角落、舊有思維模式的局限,這將有利于探尋一種新的學術的、“啟蒙”的可能。
注釋:
1.張旭東.《對話啟蒙時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第65頁.
2.洪子誠.《兩憶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第94頁.
3.洪子誠.《兩憶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第78頁.
4.章詒和.《往事并不如煙》,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第18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