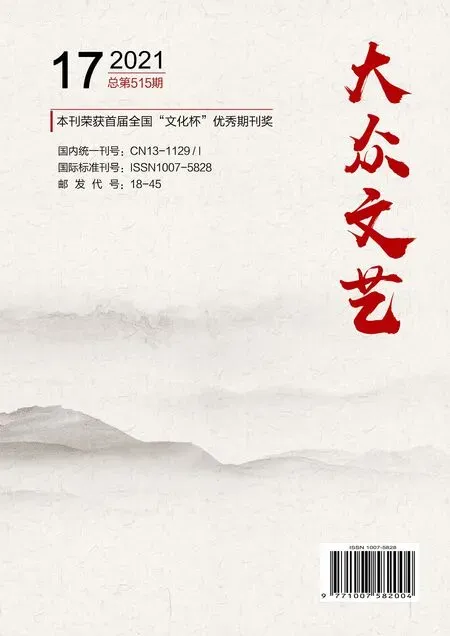時(shí)調(diào)、俗曲內(nèi)涵辨析
明清文獻(xiàn)對(duì)曲子有以下稱謂:時(shí)尚小令、小唱、小曲、小調(diào)、時(shí)調(diào)、俚曲等,徐元勇將上述稱謂以俗曲概之,并對(duì)“俗”字和“俗曲”一詞從詞源上進(jìn)行解釋,認(rèn)為:“明清俗曲中的“俗”字,則只是通俗之意……準(zhǔn)確地說,明清俗曲指的是今天意義上‘民間音樂’中‘民歌’的意思。”1在徐的表述中,突出了俗曲的民間意義,持有相同意見的還有劉曉靜等學(xué)者,那么曲子在歷史上如何存在?
一、廣義的時(shí)調(diào)
廣義的時(shí)調(diào)即各個(gè)時(shí)代的流行曲調(diào)。歷史上唐詩(shī)、宋詞、元曲皆可入樂,今人多對(duì)其從文學(xué)意義解釋,而忽略了音樂內(nèi)涵,唐宋文人選曲制曲子詞,與古代采民歌入樂府、創(chuàng)歌辭的傳統(tǒng)一脈相承。
從項(xiàng)陽(yáng)《山西樂戶研究》2中對(duì)樂籍制的挖掘可知,自北朝樂籍制度確立,在制度規(guī)定下構(gòu)成一個(gè)教習(xí)、用樂的全國(guó)性網(wǎng)絡(luò)體系,樂籍制下的官屬樂人不僅承擔(dān)儀式用樂的禮樂,同時(shí)也承擔(dān)非儀式的俗樂。儀式性用樂更多是從國(guó)家、官方的層面上彰顯,在樂籍制解體以后轉(zhuǎn)化為民間禮俗存在;而非儀式的俗樂作為審美、娛樂功用更為貼近民眾生活,在諸多階層、諸多場(chǎng)合有著大量的需求。這些樂戶在樂籍制度確立開始,就是同色當(dāng)婚的正色樂人,是專門從樂的一群,其官屬賤民的性質(zhì)是一脈貫之的。隋代統(tǒng)一使得樂籍制逐漸成為全國(guó)化建制。唐代確立了官妓制度,并專設(shè)教坊來掌管俗部樂。宋代出現(xiàn)樂籍制度的寬松,出現(xiàn)平民因經(jīng)濟(jì)利益使子女入樂的情況,但畢竟還是較少數(shù)。《元典章》載:“本司看詳,除系籍正色樂人外,其余農(nóng)民、市民、良家子弟,若有不務(wù)正業(yè),習(xí)學(xué)散樂、搬演詞話人等,并行禁約。”3元代凡奏樂演唱者均為正色樂籍的專業(yè)樂人。明代是樂籍制度最為黑暗的朝代,眾多政治高官以罪罰沒入籍,成為統(tǒng)治者鎮(zhèn)壓群臣的工具。清代樂籍制度由盛轉(zhuǎn)衰直至最后解體。樂戶在各朝代都是地位最為低賤的一群,個(gè)別朝代雖有所變化,但從宮廷到民間仍對(duì)加入樂籍諱莫如深。首先可明確的是承載時(shí)調(diào)的樂妓在樂籍制存在的數(shù)朝數(shù)代中,為官屬專業(yè)賤民樂人存在,在婚配、衣冠等諸多方面?zhèn)涫芷缫暎瞧矫裰畬佟?/p>
唐宋的時(shí)調(diào)——曲子是如何創(chuàng)承的?應(yīng)從音樂與文學(xué)兩方面考察,關(guān)注文人的參與。中唐文人元稹的《樂府古題序》曰:“《詩(shī)》訖于周,《離騷》訖于楚。是后《詩(shī)》之流為二十四名:賦、頌、銘、贊、文、誄、箴、詩(shī)、行、詠、吟、題、怨、嘆、章、篇、操、引、謠、謳、歌、曲、詞、調(diào),皆詩(shī)人六義之余。而作者之旨,由“操”而下八名,皆起于郊、祭、軍、賓、吉、兇、苦樂之際在音聲者,因聲以度詞,審調(diào)以節(jié)唱,句度長(zhǎng)、短之?dāng)?shù),聲韻平、上之差,莫不由之準(zhǔn)度。而又別其在琴瑟者為操、引,采民甿者為謳、謠——備曲度者,總得謂之歌、曲、詞、調(diào),斯皆由樂以定詞,非選詞以配樂也。由“詩(shī)”而下九名,皆屬事而作,雖題號(hào)不同,而悉謂之詩(shī)可也。后之審樂者,往往采取其詞,度為歌曲,蓋選詞以配樂,非由樂以定詞也。”4元稹這段話解釋了詩(shī)詞的起源、分類問題。其中“詩(shī)、行、詠、吟、題、怨、嘆、章、篇”是詩(shī)一類,為屬事而作,并非專為入樂,而后世有懂音律者,以詞填曲;而操、引、謠、謳、歌、曲、詞、調(diào),是由樂定詞、專門為入樂而創(chuàng)制的歌辭一類。至于聲律來源有“在琴瑟者”和“采民甿者”二種,后者自古以來就是歌辭聲律的主要來源。正是聲律為依,因聲度詞,致使歌辭長(zhǎng)短句不同形態(tài)彰顯。此外還說明文學(xué)、音樂相互關(guān)系對(duì)辭作的重要影響,聲律是文人作辭的技術(shù)支持,是必須掌握的。而文人從何處習(xí)得聲律?由于承載聲律的女樂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體系化、持續(xù)性、普適性存在,上達(dá)京師下至各地文人都可與之親近,因而習(xí)得音律并非難事。古代樂妓與妓女不同,雖聲色娛人,但詩(shī)詞書畫樣樣精通,因而成為許多入仕前或失意文人的知音。各地文人在茶樓酒肆與樂妓耳鬢廝磨的過程中學(xué)習(xí)音律,其所依音律必有原始形態(tài),初始可能只是地方區(qū)域流行之“民甿”,之后文人依原曲聲律重制歌辭,新詞創(chuàng)制完畢交由樂妓演唱。再者便是樂人推薦的過程,某些曲牌隨之被納入官方樂籍系統(tǒng),由各地樂人體系化承載,再回歸青樓妓館,于社會(huì)繼續(xù)流行。5由此,“小令三千”6在全國(guó)范圍內(nèi)一致性存在。以上便是不同時(shí)代的時(shí)興曲調(diào)被納入官方系統(tǒng)的過程,即民間歌曲——文人選曲制詞——樂人二度創(chuàng)作——納入樂籍體系——樂妓承載、曲牌在民間繼續(xù)流行。文人歌辭乃至后世詞作“文化傳統(tǒng)”的核心是音樂與文學(xué)、樂妓與文人的互動(dòng)關(guān)系。楊蔭瀏稱曲子是“被選擇、推薦、加工”而“不同于一般的民歌”的“藝術(shù)歌曲”。文人選擇曲子的初始階段,可能是地域性、民間態(tài)存在,一旦納入體系,從曲牌到承載者來說都是一種官方行為。曲子詞是一種音樂文學(xué),而廣義的時(shí)調(diào)之于明清以前各朝來說,既可以指散落于民間流行的“民盳”,也可以指納入官方體系后,已成曲牌意義的曲調(diào),是樂府、曲子詞一類音樂文學(xué)所選擇、使用的曲調(diào),更多展現(xiàn)的是其音樂意義。
二、明清時(shí)調(diào)、俗曲辨析
明清時(shí)期,小調(diào)在民間十分繁盛,相關(guān)稱謂有俚曲、小曲、小唱、小令等,它們與時(shí)調(diào)、俗曲稱謂并用,所指均為時(shí)興曲調(diào)。明清時(shí)期由于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展、城鎮(zhèn)俗文化的繁盛,時(shí)調(diào)、俗曲成為一種藝術(shù)化的高級(jí)演唱形式,并為此后多種音聲技藝創(chuàng)造了土壤。隨著清代樂籍制度解體以來樂人在各地的傳唱,不斷與當(dāng)?shù)孛耖g音調(diào)結(jié)合,具備了地方審美特性,在清末以降逐漸發(fā)展為各種曲藝曲種,如天津時(shí)調(diào)等。
近代以來較早使用“俗曲”名稱的是清末羅振玉、鄭振擇二位先生。羅振玉在《敦煌零拾》中將敦煌變文稱之為“俗曲”,鄭振擇《北平俗曲略》一書系統(tǒng)研究了二十世紀(jì)三十年代流行于北平的“俗曲”,分說書、戲劇、雜耍、雜曲、徒歌五個(gè)種屬,將62個(gè)藝術(shù)品種逐一論述,其俗曲所指將明清時(shí)期北平民間流行的音樂藝術(shù)形式基本涵蓋在內(nèi),是一種綜合性的概念。此后文學(xué)界對(duì)俗曲的理解,多沿襲兩位先生的看法。《中國(guó)音樂詞典》:“五四運(yùn)動(dòng)后,我國(guó)研究民間文藝的學(xué)者,對(duì)用一定曲調(diào)演唱的大鼓、彈詞、琴書、牌子曲、時(shí)調(diào)小曲等類的曲藝形式和秧歌、花鼓、落子、灘簧等類的民間歌舞小戲的通稱。”7在現(xiàn)當(dāng)代學(xué)者的研究中,更多賦予了“俗曲”綜合性含義。
總之,明清時(shí)調(diào)、俗曲一類是在樂人與文人、音樂與文學(xué)互動(dòng)下產(chǎn)生的藝術(shù)形式,依聲制詞是我國(guó)自古有之的文化傳統(tǒng),元稹對(duì)詩(shī)、歌的分類很好的展示了音律對(duì)于各朝各代歌辭、曲子詞的影響,文人選曲制詞、并不斷填入新詞,之后納入官方用樂,官屬樂人體系化承載后詞牌、曲牌意義凸顯。明清時(shí)調(diào)、俗曲既有傳承自前朝的曲子、南北曲一類,又有當(dāng)時(shí)新創(chuàng)制的時(shí)興曲調(diào),通過上文對(duì)時(shí)調(diào)、俗曲二詞的辨析可知其并非僅為民間意義,而是一種國(guó)家制度影響下體系化傳承的藝術(shù)品類,只有認(rèn)知?dú)v史上曲子、時(shí)調(diào)、俗曲何以存在、生存、發(fā)展,才能對(duì)當(dāng)下的一些音聲樣態(tài)進(jìn)行更好的把握。
注釋:
1.徐元勇.界說“明清俗曲”[J].交響(西安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0,(3):38-42.
2.5.項(xiàng)陽(yáng).山西樂戶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3.中國(guó)書店編輯部.元典章[M].北京:中國(guó)書店,1990.
4.元稹.元稹集[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
6.唐宋以來,樂籍中有“男記四十大曲,女記小令三千”的規(guī)定。
7.中國(guó)藝術(shù)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中國(guó)音樂詞典[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