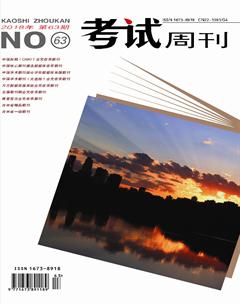《詩經》愛情詩之“禮”的審辨性思考
曾冠霖 徐炫
摘要:長期以來,高中教師和學生對于《衛風·氓》中的女子形象給予了極高的贊揚。他們認為該女子敢于突破世俗傳統的束縛,具有“自主”的意識。那么,對待世俗傳統我們是否應該持有這種決絕的態度?對于《詩經》愛情詩中“禮”的文化我們應該如何評價與對待?筆者認為,這是極其重要的。樹立審辨性的思維去對待我們的傳統文化,秉承審辨性的立場去賞析《詩經》中的愛情詩歌及其中的人物形象是至關重要的。因此,筆者的核心任務,便是結合《詩經》中的愛情詩歌探究“禮”在當時愛情詩歌中的起源、現實意義等,以便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審美觀。
關鍵詞:詩經;愛情詩;禮;審辨性思維
眾所周知,《詩經》在我國史學文壇上的成就地位可謂是無上崇高的,尤其是愛情為主題的詩歌著作。在“男女授受不親”等保守性思想蔓延過后,很多讀者對《詩經》愛情詩中那些敢于追求理想愛情婚姻的女性形象給予了極高的評價。甚而至于批判《詩經》愛情詩歌中的“禮”的思想。這種態度值得我們肯定嗎?
那么,首先我們不得不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禮”的產生只是自上而下的要求嗎?細讀《詩經》中的系列愛情我們不難得出結論。
《邶風·新臺》《鄘風·墻有茨》《鄘風·君子偕老》《鄘風·鶉之奔奔》《齊風·南山》《齊風·敝笱》《齊風·載驅》《陳風·株林》等諷喻詩都是國人對統治階級亂倫愛情的揭露。可見,對“禮”的呼喚不僅僅是統治階級出于統治需要對于下層百姓的要求,也是普通大眾面對亂倫現實,對淫亂無序、極具動物性的社會行為的一種反對。
從《鄘風·蝃蝀》《鄭風·將仲子》《豳風·伐柯》等極具維護“禮”文化色彩的愛情詩歌中,我們可以看出對于封建禮教的維護是極具普適性的。這些詩歌反映了社會大眾對女子的整體性要求:不違“禮”。維護“禮”的思想甚至成了封建女子自我道德修養的一種自我要求。
由此可見,從發生學上來說,“禮”的產生不僅僅是一種自上而下的規定,也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現實呼喚。
既然“禮”的產生有其必要性、現實性,那么它的存在是否也有它積極性的一面呢?
《衛風·氓》中女子的悲劇固然有男子薄情寡義的原因,但是女子本身也有諸多的不是。看上去,女子的不幸是因為“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即她太遵從“相夫教子”等“禮”的教化,是受了“禮”的毒害。同時,我們不難發現該女子是一個敢于沖破封建禮教束縛的形象。“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古代婚姻六禮包括: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衛風·氓》中女子的婚姻只舉行了納吉、親迎兩個步驟。可見,女子敢于追求愛情,敢于沖破“禮”的束縛。那么,這種違“禮”的行為是女子婚姻悲劇的催化劑還是保護傘呢?筆者認為,男子“言既遂矣,至于暴矣”是一部分原因是因為男子違“禮”的結果是“低投入”“高回報”。因而,女子漠視婚禮的“禮俗”規則間接地造成了自己的婚姻悲劇。
同時,閱讀《詩經》中的一些愛情詩歌我們還可以發現由于“禮”的加入這些愛情詩歌為我們展現了一種“樂而不淫”的中和之美,極具審美價值。《召南·野有死麕》是一首優美的愛情詩。本詩前兩章通過具體場景和情節,表現了青年男女對愛情的強烈渴望和執著追求。詩歌第三章則是通過對話間接表現了他們幽會時復雜的內心。“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帨兮,無使尨也吠!”,“你要慢慢地走輕輕地行啊,別弄響我腰間的佩玉啊,更別驚醒看門的長毛狗啊!”他們因為擔心被世人看見,因為擔心世俗“禮”的批判而緊張、害怕。《鄭風·將仲子》表現的也是愛情生活中復雜微妙的情感矛盾。詩中選擇杞、桑、檀三種古代十分珍貴的樹種起興,體現了少年初戀時歡喜狀態。同時,由于擔心“仲子”前來幽會時損壞杞、桑、檀,進而被周圍的父母、諸兄及鄉鄰發現并責備,所以她又懷有有一種莫名的恐懼、擔憂。“樂而不淫”的中和之美在以上詩歌的一喜一憂之間得以體現。
當然,我們并不能因此否定“禮”對于愛情婚姻的破壞作用。《詩經》中的諸多棄婦詩如:《召南·江有汜》《邶風·柏舟》《邶風·日月》《王風·中谷有蓷》《鄭風·遵大陸》等都反映了封建禮教對于愛情婚姻的摧殘。身處社會底層的貧苦婦女,他們不僅要承受自然、兵禍帶來的災難,更備受夫權制的壓迫。《大戴禮記·本命》有云:“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盜竊去。”①可見,封建禮教讓夫家擁有了以任何理由為借口休妻的自由。
周嘯天先生認為:“封建禮教,一如封建制度,也是個歷史的范疇,須要歷史的加以批判。雖然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禮教的作用很壞!但作為古代婚俗從對偶婚向專偶婚過度的文明進程中,禮教的出現最初卻是應運而生和有其積極作用的……它對文明促進的同時,也向人類索取了喪失婚戀自由、人性遭受壓抑的高昂代價……”②周先生的話有其可取的一面。
然而筆者認為,封建禮教不僅僅在漫長的封建社會有其二重性,即便是當下社會也具有二重性。我們應該以審辨性的態度評價它。它的確在喪失人類婚戀自由、壓抑人性方面有其危害性,但是在束縛某些無理、無良行為方面能起到積極作用。因為,“眾人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社會理性的象征,它能在某種程度上把人的原欲引上社會規范的路徑。并且,“禮”也讓人在享受某些自由的同時接受束縛,使得人們在品讀這些帶有張力感的詩歌的時候感受到一種中和之美。
參考文獻:
[1]周嘯天.詩經楚辭鑒賞辭典[M].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版,175.
[2]周嘯天.詩經楚辭鑒賞辭典[M].商務印書館2012年第1版,127.
作者簡介:
曾冠霖,徐炫,廣東省深圳市,深圳市寶安中心區新安中學(集團)高中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