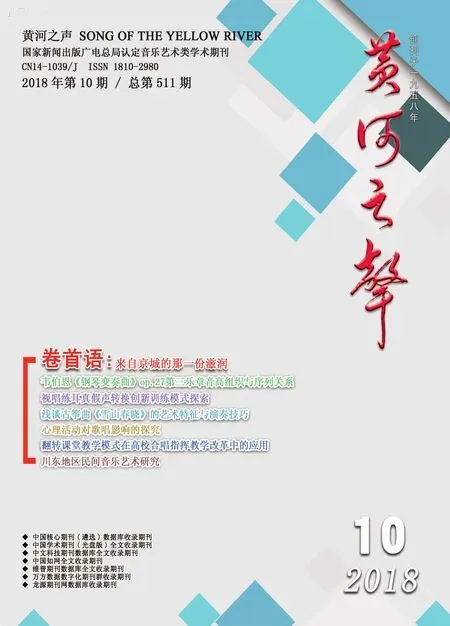韋伯恩《鋼琴變奏曲》op.27第三樂(lè)章音高組織與序列關(guān)系
伍艷婷
(西南大學(xué),重慶 400700)
作為新維也納樂(lè)派重要成員之一,安東·韋伯恩(Anton von Webern,1883-1945)的作品并不多,共31首,以短小、精煉著稱。其中《鋼琴變奏曲》op.27這首樂(lè)曲寫于1935年,是他成熟時(shí)期的作品,采用十二音體系作曲法,共三個(gè)樂(lè)章,其序列之間存在這同宗同源的關(guān)系①。第一樂(lè)章原始音列為P4與I3;第二樂(lè)章原始音列為P8與I10,這兩樂(lè)章采用重疊法的方式展開;第三樂(lè)章原始音列為R8,此樂(lè)章與前兩樂(lè)章不同,其鋼琴織體運(yùn)用縱橫法,點(diǎn)描的特質(zhì)更為明顯。
一、原始序列結(jié)構(gòu)分析
第三樂(lè)章首先采用R8(R8=bE BbB D#C C#F E G F A#G,或3 11 10 2 1 0 6 4 7 5 9 8),從例1中可看出樂(lè)曲一開始十二個(gè)音按時(shí)間順序依次出現(xiàn)(縱橫法),而后再論述此序列在音高組織設(shè)計(jì)方面的特點(diǎn)。
例1:

例2a:

例2b:

(一)序列中的小二度音程(ic1)
此序列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并不是韋伯恩常用的派生音列,其四個(gè)離散三音子集也各不相同(見例2a),但作曲家還是把慣用的小二度音程揉進(jìn)了序列內(nèi)部音高結(jié)構(gòu)中,且特加連音線強(qiáng)調(diào)小二度音程。若把序列拆分成兩個(gè)六音集合,會(huì)發(fā)現(xiàn)兩個(gè)六音集合都是6-1(012345),此集合從原型上看為連續(xù)半音,其音程級(jí)涵量(ICV)為[543210],其中ic1為最大數(shù)量項(xiàng),具有明顯的半音階特征。顯然作曲家在建構(gòu)原始序列時(shí),特地選擇了具有鮮明風(fēng)格特征的半音階為主要音高材料。另外,從音程級(jí)涵量上看,這個(gè)六音集合不存在三全音音程,可見作曲者削弱了三全音強(qiáng)烈的調(diào)性傾向,又巧妙回避明顯的調(diào)性因素。
(二)序列中的對(duì)稱結(jié)構(gòu)
原始序列R8被拆分成兩個(gè)6-1集合,而這個(gè)集合本身具有嚴(yán)格的對(duì)稱性。集合6-1在T0上是移位對(duì)稱的,即可以映射自身;而且這個(gè)集合還是一個(gè)倒影對(duì)稱集合,其相鄰音程序列(AIS=<1,1,1,1,1>)是互逆的,且在T5I中映射自身。
若將此原始序列R8的兩個(gè)6-1集合分別按其標(biāo)準(zhǔn)序重新排序后(見例2b)可發(fā)現(xiàn):其四個(gè)離散三音子集都為3-1(012),整體呈現(xiàn)出對(duì)稱結(jié)構(gòu)。作曲家為避免音樂(lè)連續(xù)重復(fù)半音音響,過(guò)于單調(diào),便調(diào)整三音集合音高位置,使得旋律線條流動(dòng)更有動(dòng)力與張力。
(三)序列中的音高選擇可能性分析
從前面分析可得出在這首樂(lè)曲建構(gòu)原始序列的過(guò)程中,作曲家意圖在建構(gòu)序列的過(guò)程中不采用三全音音程,且強(qiáng)調(diào)半音階風(fēng)格特征及對(duì)稱性結(jié)構(gòu),因此采用了兩個(gè)相同的六音集合6-1,此集合是50個(gè)六音集合中惟一的連續(xù)半音集合,集合6-1毫無(wú)疑問(wèn)成為此樂(lè)曲最為重要的音高結(jié)構(gòu)。而集合6-1共有6個(gè)子集,分別是集合3-1、3-2、3-3、3-4、3-6、3-7,這些集合就都不包含三全音音程。在R8序列中,三音組只用到3-1(012)、3-2(013)、3-3(014)、3-4(015),這四個(gè)集合都包含ic1,使得半音階風(fēng)格特征凸顯,另外,集合3-1本身具有對(duì)稱性,是倒影對(duì)稱集合,在T2I中映射自身。而在R8序列中不用集合3-6(024)與3-7(025),是因?yàn)檫@兩集合分別為全音階與八聲音階的子集合,且不含ic1,與作曲家本意不符合,在風(fēng)格特征上形成沖突。
二、主題三個(gè)序列的比較分析
此樂(lè)曲主題呈示部分為1-11小節(jié),分別用到的序列有R8、RI10與P8。
之所以在原始序列R8后采用RI10,其中一個(gè)原因是樂(lè)曲第二樂(lè)章原始序列便是P8與I10,在第三樂(lè)章中用到其逆行序列,體現(xiàn)兩個(gè)樂(lè)章在序列選擇上的統(tǒng)一性。而采用RI10的另一個(gè)原因是雙集的不變性②,此處的“雙集”是指在兩個(gè)音列形式中擁有相同序列號(hào)的一對(duì)音高級(jí)(見例3)。
例3:
由于R8與RI10為互為倒影關(guān)系的一對(duì)序列,其指數(shù)和為偶數(shù),兩個(gè)對(duì)稱軸雙集都是單一的音高級(jí):bE-bE(序列號(hào)12)和A-A(序列號(hào)2),如例3所示:其余五對(duì)雙集以自身倒影形式出現(xiàn)——B-G首先出現(xiàn)在序列號(hào)11的位置上,其后以其倒影形式G-B出現(xiàn)在序列號(hào)4;bB-#G出現(xiàn)在序列號(hào)10的位置上,隨后再次以倒影形式#G-bB出現(xiàn)在序列號(hào)1上,如此類推,R8與RI10這對(duì)倒影關(guān)系序列實(shí)際上共有七個(gè)不同的雙集,五個(gè)原型雙集出現(xiàn)在這對(duì)序列的第一個(gè)六音集合中,另五個(gè)倒影雙集出現(xiàn)在同一對(duì)序列的第二個(gè)六音集合中。在RI10后便是P8,原始序列R8是P8的逆行形式。此樂(lè)章的主題在傳統(tǒng)的曲式發(fā)展基本結(jié)構(gòu)原則角度上看,為三部性原則,呈現(xiàn)出“呈示-對(duì)比-再現(xiàn)”的結(jié)構(gòu)。
由此看出,作曲家對(duì)于原始序列及其后續(xù)序列的變體在序列選擇上有別出心裁的設(shè)計(jì)。
三、序列之間的統(tǒng)一性
此樂(lè)曲采用變奏曲的題材,且曲式結(jié)構(gòu)為變奏曲式,此處的變奏手法與傳統(tǒng)的稍有不同,采取的是序列形式的變奏。曲式結(jié)構(gòu)如下:主題(1-11小節(jié),R8、RI10、P8)、變奏I(12-23小節(jié),R9、P1、R8、I11、I5、I11、I4)、變奏II(24-33小節(jié),I9、R8、P9、I4、P9)、變奏III(34-44小節(jié),RI7、I7、RI6、I6、R8)、變奏IV(45-55小節(jié),I9、R11、R2、I3、R5、I6)和尾聲(56-66小節(jié),R8)。
把所有序列羅列出來(lái)并對(duì)比分析研究,最終發(fā)現(xiàn)所有的序列都可分為兩個(gè)相同的六音集合6-1,由此再次證明集合6-1為核心音高集合,且所有系列之間具有高度統(tǒng)一性。
例4:

另外把所有第6、7號(hào)音都是C-#F的序列歸為一類——R8、RI10、P8、I4與R2。其中R8、RI10、P8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關(guān)系前面有論述,在此并不贅述。而I4與P8是一對(duì)互為倒影的序列,其中擁有相同序列號(hào)的一對(duì)雙集是在T0I上互為倒影的一對(duì)音高,如擁有相同序列號(hào)1的雙集#G-E在T0I上互為倒影,擁有相同序列號(hào)2的雙集A-bE在T0I上也互為倒影,如此類推,其對(duì)稱軸都是是序列號(hào)6、7雙集#F-C。同理可證,RI10與R2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關(guān)系與I4-P8一樣。此外,與上述分類相同的還有組二:R9-I11-I5-P9,序列號(hào)6、7都是C-G;組三:P1-I9-I3,序列號(hào)6、7都是B-F;組四:RI7-I7-R11-R5,序列號(hào)6、7都是A-bE;組五:RI6-I6,序列號(hào)6、7都是D-#G。
綜上所述,此樂(lè)章所有序列存在著同宗同源的關(guān)系,都源于原型P0,經(jīng)過(guò)移位、逆行、倒影、倒影逆行手法進(jìn)行變奏,保持序列間的高度統(tǒng)一性。
四、結(jié)語(yǔ)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總結(jié)出,韋伯恩設(shè)計(jì)出由兩個(gè)結(jié)構(gòu)相同、極具有鮮明半音風(fēng)格、自身嚴(yán)格對(duì)稱性的六音集合為基礎(chǔ)建構(gòu)的序列,這個(gè)序列亦可分為四個(gè)離散三音集合,由此可看出此六音集合在全曲中起到承上啟下的作用,承上是構(gòu)成序列的基礎(chǔ),啟下可分裂成具有特色的三音集合,使全曲的序列具有高度的整體性。另外,由原始序列R8開始經(jīng)過(guò)移位、逆行、倒影、倒影逆行手法進(jìn)行變奏,且選擇與原始序列在內(nèi)部結(jié)構(gòu)上有著某種相同聯(lián)系的音高組織結(jié)構(gòu)的序列,大大提高了全曲序列的統(tǒng)一性。
韋伯恩在這個(gè)樂(lè)章中所用到的那些經(jīng)過(guò)他精心、嚴(yán)謹(jǐn)處理的序列,恰恰體現(xiàn)了他不僅汲取了勛伯格十二音序列寫作技法的養(yǎng)分,還創(chuàng)造出具有韋伯恩自己特色的序列結(jié)構(gòu)。■
注釋:
① 整首樂(lè)曲三個(gè)樂(lè)章的序列原型是P0(P0=0 1 9 11 8 10 4 5 6 2 3 7),并通過(guò)移位、逆行、倒影、倒影逆行的手法發(fā)展成為一首完整樂(lè)曲。
② 羅伊格·弗朗科利 著,杜曉十,檀革勝 譯.理解后調(diào)性音樂(lè)[M].人民音樂(lè)出版社,201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