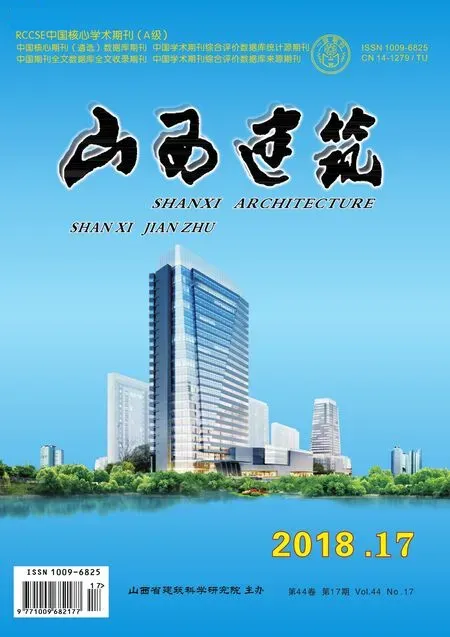深厚淤泥質地層基坑地下連續墻施工機理研究
趙 南 杰
(中國水利水電第八工程局有限公司,湖南 長沙 410004)
0 引言
地下連續墻應用廣泛,該結構具有剛度大、整體性強、防滲性和耐久性好等優點,但是在施工過程中也常常發生槽壁坍塌現象[1-4],特別在不穩定地層中坍塌的情況比較嚴重,造成混凝土繞流,影響連續墻的施工質量[5-7]。本文在平面應變假定的基礎上,采用有限元方法模擬了連續墻的施工效應。本文采用數值模擬的方法,能夠模擬土體的應力與變形形態,合理反映地下連續墻施工引起的地層變位的動態變化。本文采用ABAQUS模擬地下連續墻成槽開挖、混凝土澆筑和硬化全過程,研究地下連續墻施工引起的地層受力與變形特性,并將計算應力結果和現場實測結果進行比較。旨在為地下連續墻設計與施工提供參考。
1 工程概況
深圳地鐵10號線益田停車場位于福田區,廣深高速北部的綠化帶和富榮路地下空間,結構為東西向。益田停車場是一個雙層停車場。標準截面結構為雙層五跨矩形框架結構。該用地的性質是城市綠地。長555.7 m,標準段寬50.75 m,深21.7 m,配套工程安全水平為一級。停車場范圍地質情況從上至下分別為:素填土、淤泥質黏性土、粗砂,礫質黏土、強風化花崗巖、中風化花崗巖。該項目北靠益田村,南臨廣深高速公路。它位于繁華的市區。施工不僅對周邊環境有影響,周邊的城市環境也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施工過程。地塊內有下穿廣深高速的2號人行隧道、3號車行隧道,110 kV變電站一座以及數條東西方向的110 kV高壓地下電力管廊,益田路立交橋橋墩坐落在地塊東側,廣深港盾構隧道在益田立交東西兩側由南向北下穿廣深高速,以上市政設施均對地下停車場的布置有影響。
2 數值模擬
2.1 計算模型及參數
基于大型有限元程序ABAQUS,針對淤泥質地層大型地鐵車站深基坑工程的穩定性,建立了益田停車場深基坑三維有限元模型,確定模型長698 m,寬287 m,高80 m,單元共計96 885,有限元數值計算模型如圖1所示。各材料參數如表1所示。

表1 材料參數表

材料彈性模量MPa泊松比天然重度kN/m3直接快剪粘聚力/kPa摩擦角雜填土100.2519.00.08素填土250.418.64.36.5粉質黏土300.3019.41020.0黏質粉土1 8000.2619.715.617.7中砂3000.419.52.028.0
2.2 計算步驟
計算模型考慮了地下連續施工前后橫向位移、豎向位移隨施工的變化具體計算步驟如下:
第一步:開挖從0 m~-2 m,挖深為2 m,同時施加第一道支撐;第二步:達到設計強度后,第二步開挖從-2 m~-6 m,挖深為4 m,同時施加第二道支撐;第三步:達到設計強度后,第三步開挖從-6 m~-12 m,挖深為6 m,同時施加第三道支撐;第四步:達到設計強度后,第四步開挖從-12 m~-21.7 m,挖深9.7 m,開挖至坑底后,開挖結束。拆除第三道支撐并修建車站底板;第五步:拆除第二道支撐并修建車站中板;第六步:拆除最后一道支撐并修建車站頂板。
3 計算結果分析
3.1 地下連續墻橫向位移時空變化規律分析
選取變形明顯的基坑開挖中部所在的南側與北側兩個斷面進行墻體變形性狀分析,支護墻體采用四節點平面應變單元(CPE4)。
地下連續墻水平位移隨深度的變化如圖2所示。

由圖2可知,首層開挖完畢后,對應的墻體變形微小,從開挖至6 m開始,開挖面以下均為淤泥質土層,墻體變形呈典型的內凸型,最大水平位移隨挖深逐漸增大,最大值隨Z軸逐漸下移,最后穩定在基坑中部。施工完成后,地下連續墻(外墻)的橫向位移變化值較小,由于施工過程可視為多個“卸載—加載”過程,且卸載的影響更明顯,圍護結構(地下連續墻)受這種開挖卸荷效應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向坑內的變形。南側地下連續墻墻頂水平變形規律一致,均是隨著施工的進行,水平位移先增加后減小,最后趨于穩定,至開挖結束時,最大水平位移為3.2 mm,最大水平位移與開挖深度的比值為0.015%,深度位于6 m~10 m之間,可見危險位置出現在墻體中部。此外,在軟土地區中,由于土體自身具有流變性,其變形過程具有明顯的時間效應,對于軟黏土,其固結的時間歷程往往遠大于施工的周期。
3.2 地下連續墻豎向位移時空變化規律分析
對于地下連續墻墻頂的分析依然分別取南側和北側兩個斷面進行研究,支護墻體采用四節點平面應變單元(CPE4)。地下連續墻豎向位移變形曲線圖如圖3所示。

由圖3可知,施工完成后,地下連續墻(外墻)的豎向位移變化值較小,在-8.5 mm~-6.0 mm之間;墻頂各典型點的豎向位移相差不大,相差最大值約為1 mm,南、北側地下連續墻墻頂豎向變形規律一致,均是隨著施工的進行,豎向位移先增加后減小,隨后又增加,之后反彈,地連墻的豎向變形有所回彈,這是由于開挖土體卸荷使得基坑自重減小,總體變形仍表現為沉降,數值相差不大。南側墻頂模擬值與實測值趨勢大致相同,實測值比模擬值大10.3%左右,模擬較為準確。
3.3 現場監測數據對比分析
地下連續墻墻體沉降監測數據統計如圖4所示。
由圖4可知,監測點位移變化通過y坐標變化表示,y為正代表測點處墻頂向基坑內傾斜,為負則向基坑外傾斜,由于偏移為矢量數值,通過時間—偏移曲線難以清晰表示各時間節點處墻體的具體傾向,因此通過將當前測點偏移數值繪制于四個象限的函數圖形內,當前數據點所在位置及距原點距離,分別代表了監測點處墻頂的偏移方向和偏移距離。圖中可以發現大多數測點y向偏移值在10 mm以內,其中SQ3和SQ4測點處的墻頂體位移明顯大于其他測點,SQ3點處的位移隨著開挖在后期變化速率越來越快;SQ6,SQ7和SQ8的變形趨勢較為平緩,SQ8在后期出現了明顯外凸的趨勢;SQ6和SQ7則為內凸趨勢;SQ5在6月15日開始有了明顯的上升浮動,呈明顯的內凸趨勢,但變形量仍在15 mm以內。各測點中SQ3處墻體向外傾斜最大,SQ3位于基坑結構變截面拐角位置,前方基坑施工擾動極其容易使壁后土體對結構產生擠壓,結構設計比較合理。

4 結語
1)南側地下連續墻墻頂水平變形規律一致,均是隨著施工的進行,水平位移先增加后減小,最后趨于穩定,可見危險位置出現在墻體中部。
2)施工完成后,地下連續墻(外墻)的豎向位移變化值較小;墻頂各典型點的豎向位移相差不大,南、北側地下連續墻墻頂豎向變形規律一致,均是隨著施工的進行,豎向位移先增加后減小,隨后又增加,之后反彈,地連墻的豎向變形有所回彈。
3)可以發現大多數測點y向偏移在15 mm以內。基坑結構變截面拐角位置偏移最大,前方基坑施工擾動極其容易使壁后土體對結構產生擠壓,結構設計比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