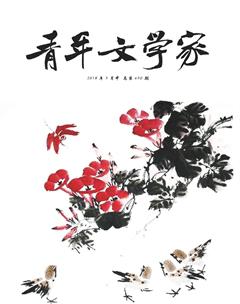論白先勇筆下“城與人”的經典性
摘 要:白先勇塑造了一批“臺北人”和“紐約客”的形象。由于政治、文化的變化和差異,使這些人物顯現“邊緣人”的特質。而且,白先勇對人物所在之城的偏見,更加突顯了人的內心狀態。在人與城的相互影響下,成就了《臺北人》和《紐約客》的經典性。
關鍵詞:臺北人;紐約客;邊緣人;經典性
作者簡介:姜彥竹(1996.6-),女,漢族,吉林省人,武漢大學本科,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14-0-01
且不說白先勇作品是否經典,只提到《臺北人》或者青春版昆曲《牡丹亭》,許多人對此一定不陌生。《臺北人》曾入選20世紀中文小說100強,位居第7位。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世界巡演多場,相當知名。他一生輾轉各地,桂林、臺灣、美國,一路上遇見許多人,也創作出許多人。城與人作為不可或缺的兩部分,相互影響、支撐,成就了白先勇的作品,尤其是《臺北人》和《紐約客》。
一、關于“經典”
在討論具體作品之前,總繞不開對經典本身的看法。“經典”一詞,在漢語意義的源頭指儒家典籍,包含經書和史書,重在真理和教化,正如劉勰所說“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但是劉勰所言的經典已經不限于儒家典籍。[1]直到現在,經典“面目全非”。比起孔孟之書,現在我們更熟悉的經典是《紅樓夢》《狂人日記》等。顯然,經典隨著時代變遷、作品迭出而有所變化。
如何判斷一部作品是經典?哈羅德·布魯姆以純粹的審美視角構建經典,“只有審美的力量才能透入經典,而這力量又主要是一種混合力:嫻熟的形象語言、原創性、認知能力、知識以及豐富的詞匯。”[2]論述了陌生性、普遍性、競爭性和焦慮性等一系列的經典特征。卡爾維諾憑借作家的感性和經驗,用十四條去定義經典,“重讀”“重讀都好像初讀”“初讀也好像是在重溫”[3]等言語表露出讀者的讀書行為決定了一部作品的經典性。
世人圍繞經典的闡述不勝枚舉。經典也正因為處于議論的風口浪尖,而成了經典或至少是接近經典的存在。縱觀許多批評者對經典性的理解,本文對白先勇作品經典性的論述將聚焦于《臺北人》、《紐約客》兩本書中,對 “城與人”獨特而極致的塑造。
二、邊緣之“人”
歐陽子很早便指出《臺北人》的人物共性,身在臺北,背負著過去大陸的記憶。她通過今昔對比將人物分成三類,活在過去、融合過去與現在、斬斷過去。而過去和現在幾乎是對立的,簡言之,過去的一切都好,現在的一切都壞。[4]時空的變化是形成臺北人形象的重要原因。回到人物本身,不管是高官、舞女,還是知識分子、商人、傭人等,不管是屬于哪種類型,他們都呈現出了“邊緣人”的形象。
何謂“邊緣人”?這一詞最初出現在社會學領域,出于種族和文化的差異,邊緣人徘徊在某個社會主導群體之外,被稱為“移民”“外來者”等。當邊緣人出現在“文學”中,狂人、傻子、城市底層的市民、墮落的女性等人物形象幾乎都可以囊括在內。邊緣和中心向來是相對變化的,以“邊緣人”稱呼他們也許并不恰當,但是“邊緣人”因為政治、文化差異產生的矛盾心理,以及漂泊無依的狀態又正好相似。
《臺北人》中的人物來自社會各個階層,歐陽子稱白先勇寫出了社會之“眾生相”[4],我卻以為他只是極致地塑造了“一相”。若用一詞形容這“相”,“悲哀”算是一詞。而這悲哀,一方面源自對大陸政權的喪失,人們被迫流亡;另一方面,在新世界臺北,這些人又不再是政治的中心。而《紐約客》中,“客”一字注定了人物漂泊凄涼的異國人生。他們的“邊緣”源于異國文化的差異。白先勇自身便是赴美留學,如同許多中國留學生感受到過西方文明強烈的沖擊。但在骨子里,中國文化傳統似在隱隱抵抗。當紐約客面臨著兩種文化博弈,沒有絕對的勝負,游離在中西文化的邊緣,承受著文化碰撞帶來的焦慮和掙扎。
三、黑夜之“城”
奧爾罕·帕慕克曾說:“小說里的景觀是小說主人公內心狀態的延伸和組成部分。”[5]前面已提到邊緣人悲哀的、焦慮的內心,而他們所在的城被白先勇刻畫得是那么充滿偏見,又那么極致地展現了屬于邊緣人的一面。
《臺北人》里,尹雪艷的公館,麗兒住的洋房都在仁愛路,金大班跳舞在西門町,長春路上住著朱青、賴大哥、盧先生,還有臺北近郊坐落著高官和貴婦的府邸。
臺北市的明暗之間仿佛劃開了分明的界限,每一種光亮閃耀著屬于他們自己的社會階層。但不要忘了,光亮的底色是無盡的黑夜。整個城的氛圍籠罩黑暗、壓抑之中,正如臺北人內心的失落。而且,這樣的一幅臺北地圖在大陸地圖的對比下,才更顯絕望。路名上縱有大陸的長春、南京、溫州,這些地方卻只能遙相望。花橋榮記應該在桂林,舞場應該在上海百樂門,輝煌的府邸應該在六朝南京。臺北的一切就像仿制品,假的真不了,難掩內心落寞。紐約的夜,更加細致。不知不覺,人們迷失、墮落、異化,人情淡漠。紐約的黑夜令人恐怖、窒息,同時引發人們對西方現代文明的重新思考。
事實上來講,臺北和紐約并非如此,但白先勇寫下的偏見極有魅力。就像倫敦不止有骯臟、犯罪率極高的街道,但僅這一點就讓倫敦成為狄更斯的倫敦,僅是黑夜的燈光,就足以讓臺北成為白先勇的臺北。
參考文獻:
[1]劉象愚.經典、經典性與關于“經典”的論爭[J].中國比較文學,2006,(第2期).
[2](美)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著;江寧康譯. 西方正典 偉大作家和不朽作品. 南京:譯林出版社, 2005.04.
[3](意大利)伊塔洛·卡爾維諾著;黃燦然,李桂蜜譯. 閱讀指南叢書 為什么讀經典. 南京:譯林出版社, 2015.11.
[4]歐陽子著. 王謝堂前的燕子. 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 2014.09.
[5](土耳其)奧爾罕·帕慕克著. 天真的和感傷的小說家.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