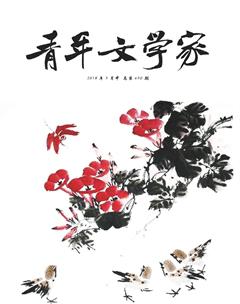從明清小說批評看古人的思想“交流渠道”
韓京洋
摘 要:本文對古代小說批評的內在進行探源,得出其實質為文人的一種“交流渠道”的結論。通過對個別明清小說批評進行分析,表現了此種“交流渠道”的所具有的特質。把明清小說批評與戰國時代辯論和現代的電腦交流軟件進行對比分析,表明“交流渠道”的發展進程。
關鍵詞:交流渠道;明清小說批評;辯論;電腦交流軟件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14-0-03
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辯論方式盛行,人們通過集眾辯論的方式,表達自己在學術、政治上的不同的見解和主張。通過與生長在不同環境中的不同的人進行激烈的思想碰撞,辯論者能夠最大程度的打破自身思維局限性,從而對自己所研究的問題有更深刻的認識。而旁觀者也可以在辯者你來我往、互不相讓的辯駁詰難中以最快的速度對辯題有一個深入的了解,悟性極高者,甚至可以萌生出自己的想法。
集眾辯論固然是很好的交流渠道,但卻存在著一定的制約性。首先它要求辯者和觀眾必須在固定的時間到達固定的場地,路途遙遠者或者因故有事者無法參加,因此存在著時效性。其次,所參加辯論會的人群只能局限在舉辦地的附近,其風俗、文化等較為接近,這使得辯者無法和價值取向差異更大的人群進行思想碰撞。最后,辯者多為飽學之士,下層平民百姓和一般學士或文人無法參與其中,因此受眾范圍十分狹小。
隨著時代的發展,人們漸漸找到了適合于自己的思想交流渠道。隋唐時期,傳奇小說進入“變態領域”,主體意識充盈于作品之中,敘述視角由第三人稱轉換為第一人稱,“我”作為線索人物、事件人物以及記錄者出現于作品之中。所謂“詩言志”、“詞言情”、“文以載道”,文學作品作為一種載體,在作者和讀者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作者把自己的觀點賦之予作品,而讀者通過對作品的研讀,來體會作者的思想和情感,這種方式形成了早期的交流形式,即“一次交流”。此“交流渠道”始于原作者,即“一次作者”,終于讀者,即“一次讀者”,為“單向一次交流”。這種交流形式,使讀者能夠更深入全面的理解作者的心境,從而對作品進行更完美的解讀。然而,這種交流形式雖然受眾面廣,不受時間和場地的制約,卻存在著一定的弊端。單方面的信息的輸出和接受,使讀者在對作品進行解讀后,所形成的贊同或反對的觀點并不能及時反饋給作者或者他人,更無法通過深入探討的方式,加深自己對于作品的把握。
宋元時期,小說理論得到發展。劉辰翁對《世說新語》進行較全面的評點,范圍涉及訓釋疏通、指出歸類不當、指漏糾謬、提出不同見解、評騭人物故事以及品評藝術特色等多個方面,開創了小說評點的先河,這也是已知的最早的文言文小說評點。劉的評點雖然不能反饋給《世說新語》原作者或編撰者南宋劉義慶以及其門下食客,但其思想卻與他們進行了一番深入“交流”。作者接收原作品所傳達出來的信息,進行深入思考后把分析結果再次傳播于眾,其對原作的解讀正確與否以及程度深淺引發讀者進行再次思考,把這種交流形式稱為“二次交流”。這里的作者既是“一次讀者”,又為“二次作者”,稱為“中間作者”。這里的讀者為“二次讀者”,稱為“最終讀者”,值得注意的是,“二次讀者”中的一些人同時又是“一次讀者”。“二次交流”始于原作者,途經“中間作者”,終于“最終讀者”,為“單向二次交流”。通過“二次交流”,“最終讀者”可以把自己對于原作的解讀和“中間作者”對于原作的解讀進行比較與分析,從而使自己對原作有更深入的理解。同時,也可以指出“中間作者”的解讀不當之處,并把自己對于“中間作者”解讀的分析傳播于眾,從而形成“三次交流”。以此類推,層層遞進,直至“多次交流”,通過不斷的分析與總結,加強對文本的把握。這種“交流渠道”雖然沒有及時反饋的功能,但由于對于文本的分析較為深刻、細致與全面,從而能達到極佳的效果,甚至有些時候,比“雙向一次交流”更為有效。
明清時期,不僅金圣嘆、毛宗崗、張竹坡、王國維等文人用“小說批評”這種交流方式來表達自己的主張,余象斗、馮夢龍等書商和李卓吾、梁啟超等思想家也積極參與其中,一時間盛況空前。
嘉慶時期,《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在民間受到熱捧,引起轟動。楊涌泉、熊大木、余象斗、熊龍峰、余邵魚、余成章、劉剡、劉龍田、熊宗立、俞良甫、鄒學圣等出版商開始投入到小說批評與再創作中去。其中,熊大木模仿《三國志演義》和《水滸傳》進行了大量的創作,如《楊家將演義》、《北宋至傳》、《唐書志傳通俗演義》等作品皆在民間引起了極大的反響。熊大木的作品中,小說創作與小說點評同時進行,評點的格式為雙行夾批和文后附史論。但其文學素養不高,缺少運用虛構、挪移、捏合等手法的藝術功力,因此著作中隨處可見大量堆積的史料,且其無力信手引用和隨口吟詠,所以只能頻繁采用“后人有詩嘆曰”這一寫作手法。雖然熊大木的創作和評點水平不高,但仍然受到市場的熱捧,形成了“熊大木模式”,一時間,大量的出版商爭先效仿。這種熱潮雖然帶來了很多消極影響,形成了拼湊成書和胡編亂造的惡劣風氣,并且導致了淫穢色情小說和續書的泛濫成災,但也有其積極意義。“熊大木模式”從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小說創作和小說評點的發展,從側面反映了古代交流渠道的匱乏,不管是“一次交流”還是“多次交流”,民眾渴望看到或讀到他人的觀點,并把他人的觀點和自己心中的想法相比較,從而引發更深入的思考。對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民眾來說,小說批評更是解答了他們對作品的疑惑,并從一定程度上增強了他們的理解能力。
萬歷時期,思想家、文學家李贄反對禮教、抨擊道學,公開以“異端”自居。“四大奇書”除了《金瓶梅》之外,均有署名李卓吾的評本。其中,《水滸傳》就有六個版本,萬歷三十八年杭州容與堂刊刻的《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和萬歷四十年郁郁堂袁無涯刊刻的《出像評點忠義水滸全傳》奠基了小說評點形態,對后世影響較大。李卓吾把小說評點和社會批判緊密結合在一起,運用小說批評來宣傳反道學、反傳統的叛逆思想。此時,小說批評作為一種獨特的“交流渠道”,隱晦地傳達出作者的價值觀,并使這種價值觀,被大眾所知道、了解,甚至于啟發了志同道合之士。李贄創立的“情教”有廣大的教徒,其“童心說”也影響了很多文人。湯顯祖發展了李贄的“童心說”,提出了“至情說”的觀點,從一定程度上講,是完成了“三次交流”。
學術巨匠胡應麟在文獻學、史學、詩學、小說和戲劇學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其對于小說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一時一書,而是有相當宏觀的認識和整體把握,他不僅對小說的源頭和發展歷史進行探索,對其本質和功能亦有研究,從宏觀和微觀的角度,對小說創作主體進行對比研究。此時,“一次作者”不再限于某個作者,而可以跨越不同時間和空間。“二次作者”憑借自己的“交流”意愿,可以對不同朝代和不同地點的“一次作者”進行篩選,并把自己對其認同或者否定的觀點傳達給讀者。既屬于“一次讀者”又為“二次讀者”的讀者,可以把“一次作者”和“二次作者”的觀點進行比較,以認證自己的觀點。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采用胡應麟的材料極多,基本觀點也與胡氏相同,這證明了魯迅對胡的觀點的認同,這種認同感在他和讀者的“三次交流”中體現。
明末小說評點進入繁盛時期的準備階段,這一時期,評點作品數量多,評點的質量和水平也有顯著提升,馮夢龍、湯顯祖等人對話本小說和戲劇的評點取得較高成就。馮夢龍,吳縣長洲人,著有小說類話本《喻世明言》、《醒世恒言》和《警世通言》。出身于士大夫家庭,科舉不順,五十七歲才補為貢生,清兵南下之時,曾親自奔走反清大業,后憂憤而死。從馮夢龍的經歷來看,其一生經歷頗多,且命途多舛。他的思想復雜矛盾,受王陽明和李卓吾的影響,一方面嘲笑孔夫子,貶斥六經,另一方面,卻一直兢兢業業治經,著有《麟經指月》、《春秋衡庫》等經學著作,稱贊孔圣人“刪除六經、表章五教,上接文武周公之派,下開百千萬世之緒,此乃帝王以后第一代講學之祖。”他一方面肯定卓文君的自擇私奔,對女性勇敢追尋自我的意愿表示欣賞與贊揚。一方面在《壽寧待志》中為節婦立傳,認為其清白胡可沒也。馮夢龍的這種矛盾的性格特征,固然和自我之本源思想有關,也和“一次作者”與“二次作者”的作品對其影響有著莫大的關聯。王陽明作為“一次作者”,間接的影響著馮夢龍。馮夢龍接受李卓吾和王陽明的思想也是分階段性的,根據自己的經歷不同,其傾向的選擇也不盡相同。馮夢龍青年和中年時期,受李卓吾影響較大,思想進步。晚年則受王陽明影響較大,思想趨于保守。結合馮夢龍自身經歷來看,其選擇的價值觀念傾向和自身的經歷有關,這也從側面證明了讀者會根據當下自己所處的環境和狀態的不同,選擇“作者”輸出的最符合自我之心境的價值觀念。一部分讀者把這種觀念和自己的價值觀念相暗合,并衍生出新的觀念,繼而輸出給后續讀者,從而完成循環的“交流”模式。馮夢龍論述了說話藝術和話本的興盛,以及話本小說語言通俗的必要性等小說理論。強調了小說中藝術虛構的合理性,以及論述話本小說的社會作用問題,從形式和內容上說,是具有理論價值的小說論文,已經初具現代論文的一些基本因素。馮夢龍在文學上主張“真情”,并且在《敘山歌》中,提出要“借男女之真情發名教之偽藥。”并且編撰了《情史》,設立“情教”,構建情教體系,創立了“情教”理論。和湯顯祖一樣,發展了李贄的“童心說”,他們二人同為李贄的“讀者”,又同時為“作者”,由李贄的思想觀念衍生出新的屬于自己的思想觀念,并把這種觀念輸出給其他讀者。由此可見,除了“作者”并不是統一確定的,處于同一范疇的“讀者”也可以各不相同,信息的輸出并不是單一渠道的,是發散性的。
湯顯祖在思想上受“兩大教主”李贄、達觀道人影響較大。湯顯祖文學造詣較高,在戲劇、詩文、小說和評點等方面皆有成就其代表作品《牡丹亭》對后世影響較大。《牡丹亭記題記》中寫道:“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生,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與死,死而不可復生者,皆非情之至也。”[1]他強調立意,崇尚至情,提出了“至情說”。以湯顯祖為代表的“臨川派”在戲劇理論方面更注重內容,崇文采,尚趣巧。而以沈璟為代表的“吳江派”更注重本色,道德和聲律。由此可見,處于同一“范疇”的讀者的思想觀念既可以相同、相似、相互暗合,又可以截然相反、背道而馳。這些讀者作為作者的同時,把自我的觀念輸出給更多讀者,從而進行發揚,這使得整個發散“交流”中,呈現出異彩紛呈的局面。針對“沈湯之爭”,王驥德做出了科學性的論斷,摒棄門戶之見,客觀公允地指出了二人戲曲的長處。王驥德既為二者的“讀者”,又為“作者”,在把二人思想融合的同時,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使同一方面的背道而馳的觀點呈現出相互交匯,甚至融合的狀態,體現出“交流”進程具有海納百川的特征。
清初小說評點走向繁盛,創作繁榮、題材廣泛、門類齊全,為小說評點提供了對象。這一時期,小說評點在理論上有了大幅提高,理論內涵豐富而深刻。《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和《金瓶梅》被稱為“四大奇書”,被許多文人一評再評。“一次作者”的佳作增多時,給“一次讀者”的思想以更好的啟蒙,從而使“二次作者”增多。“二次作者”的佳作增多時,大量“三次作者”也應運而生,形成良性循環,促進文化繁榮。金圣嘆刪改《水滸傳》,將120回腰斬為70回,第一回改成楔子,刪去梁山聚義后的故事,以盧俊義一夢為結束,題名《第五才子書施耐庵水滸傳》,成為流傳至今的定本和通行本。有的學者認為,《水滸傳》作者名字應加上金圣嘆一名,可見其影響之大。金圣嘆的綜合型評點形態,對毛氏父子、張竹坡等人影響較大,他在原著的基礎上,重構小說結構,整理敘事框架,使作品趨于完美。通過對“一次作者”的作品的賞讀與分析,在“讀者”的作用下,作品被賦予新的生命,成為具有極高文化價值的文本,并且對于后世產生了深遠的意義。文化作品在不斷的“交流中”進行衍變,并且得到改善,這種“交流”是無窮盡的、沒有終點的,從而使作品也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聊齋志異》是中國清代著名小說家蒲松齡終其一生寫成的一部志怪小說,體裁廣泛,內容豐富,人物形象鮮明生動,故事情節曲折離奇,結構布局嚴謹巧妙,文筆簡練,描寫細膩,具有極高的藝術成就,堪稱中國古典文言短篇小說之巔峰。王士禎兩次對《聊齋志異》進行點評,但限于其經歷心境與蒲松齡比較而言,差異過大,其評點未能得其精髓。后但明倫對《聊齋志異》進行點評,在思想方面揭示了作者的創作目的,歸納塑造形象的特點,總結章法結構,見解深刻。由此可以看出,在“交流”的過程中,雖然一些“中間作者”的觀點不夠全面,認識有所偏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屬于不同層級的“讀者”對其不斷地進行改進,最終趨于完善。
從遠古到近古,又至現代,能夠在思想上進行深刻交流一直是人類發展的一個永恒的趨向。為了這一想法成為現實,并且使交流更方便、快捷、富有成效,大量的硬件產品應運而生,從竹簡到紙張,從飛鴿到電話,無不透漏出人類對于交流的渴望。印刷術的進步,文本體裁的多樣化,戲曲、說話等表演藝術的繁盛,也使交流更簡便快捷,賦予內涵,并且具有感染力。現代科學技術急速發展,電腦的興起終于使“多向交流”變為可能,“第一作者”可以在第一時間發表作品,并且被更多的“一次讀者”所看到。“一次作者”可以對作品發表自己的看法,簡單明了亦或深刻透徹,其觀點被更多的“二次讀者”所賞讀。在貼吧、豆瓣、天涯、知乎等帶有評論功能的軟件的幫助下,人們可以進行即時“交流”,也可以進行延時“交流”,而“@”功能的出現,使“交流”更有針對性,從而提高交流效率。不但文本這種表達人們思想的方式可以進行“雙向交流”,電影、音樂等文化形式也可以被即時評論。這些在交流方式上的進步,使得“交流”真正擺脫了古代交流方式的弊端,從而邁向了新的開端。
注釋:
[1]湯顯祖.牡丹亭[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