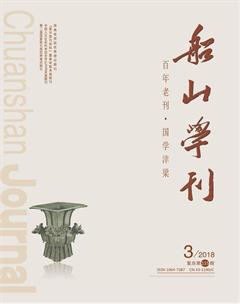自我實現
孫長虹
摘要:
杜維明認為天人合一是自我實現的本體論上的依據,它為自我實現提供了宗教性及神圣性。他認為自我實現是在與他人的關系中進行,應該尊重人的生存脈絡,即尊重家庭的特殊性,不過應該反對特殊主義;他也否定毫無差別的普遍主義,認為兼愛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必要的。他主張個人應該通過理性認識他人、社會的意義和價值,克服自我中心主義和裙帶關系兩種錯誤傾向,實現由特殊性向普遍性的超越、自我轉化與群體轉化的統一。他的這些思想與集體主義存在著共通之處,應該能夠為今天的社會主義道德建設提供有益的借鑒。
關鍵詞:自我實現;群己關系;特殊性;普遍性;理性
群己關系是道德文化的核心問題,在傳統道德文化中,這個問題是以個人、家庭與社會的面貌出現,家庭是非常重要的一環。杜維明是現代新儒家第三代的代表人物,他在對儒學的現代詮釋中,形成了對這個問題的獨特觀點。他從人的本體出發,把群己關系置于自我實現的邏輯脈絡中,使其具有既不同于自由主義、又不同于社群主義的認知和實現路徑。
一、自我實現的涵義及本體依據
杜維明認為,自我實現,即自我轉化,是指實現自己的本性,達到自我超越。在對人性的認識上,杜維明繼承了傳統儒家的觀點,認為人性本善,仁者愛人,善是在與他人、家庭、社會以及外部世界中體現出來的。因而,自我轉化和超越并不僅僅是個人的私事,而是具有社會性。“我們知天的渴望以及與天合一的企盼植根于我們對人類伙伴的義務之中。除非涉及到家庭、社會以及整個世界,否則,個人的救贖與解脫,就像是遁世的隱士一樣,便只具有單方面和有限的意義。”[1]197杜維明深刻地看到了人的社會性本質,認為自我轉化不是個人的行為,而是群體性行為;自我轉化是在群體關系中的轉化,是實現個人作為社會人的義務和價值。簡言之,是對人類義務和責任的實現。這與當代我國提倡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精神的實質是相通的,都是主張個人與集體、社會的本質上的密不可分的關系。
自我實現的實質是內在超越。內在超越是現代新儒家學說的一個重要內容,他們認為傳統儒學雖然沒有形成像西方那樣的宗教,但是儒學也具有超越性,其典型特征是內在超越。與西方宗教注重超越人世的天堂觀不同,內在超越注重現實和現世,是在此時此地的一種自我超越。杜維明認為:“在儒家自我的結構中固有一種對超越的強烈渴望。但是,這種渴望不是對一個外部最高的存在者的渴望,而是對賦予我們人以其本性的天的渴望。從更深刻的意義上說,這種對超越的渴望也是對自我超越的強烈要求,即超越自我的現存狀態,使自我成為應該的自我。”[2]147在他看來,自我實現是對人的狹隘的私我的超越,實現作為人的本性,它具有本體論上的深刻依據。
在本體論上,杜維明認為天人合一,即天與人都具有同樣的仁心仁性。“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3]15即人具有與天地萬物一體的“仁”之本心本性。在本體論上杜維明與傳統儒學、宋明儒學以及現代新儒家熊十力、唐君毅等人是一脈相承的。正是因為人性本善,我們才有進行自我實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杜維明看來,自我不是一個孤立的原子,即不是單一的分離的個體,而是人類關系中的實體,“自我,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是它的所有關系的總和。同時,它又被看作是各種關系的一個中心,不能被歸納于這些關系本身。”[4]7
杜維明認為本體論上的天人同性為道德的宗教性及神圣性奠定了基礎,在此基礎上,他提出了倫理宗教的觀點,注重道德的宗教性。杜維明認為仁之本性與“天”聯系在一起,“天”在中國思想中不僅是自然之天,還有本體之天、倫理之天等多重含義,是個兼具神圣性和神秘性的概念。他認為傳統儒家中有對超越的強烈渴望,自我實現本身就具有宗教性。在整個儒家傳統中,雖然,儒家沒有現代意義上宗教的組織、外在超越等特征,但是,其是具有宗教性的,這種宗教性來自于本體上的天地萬物一體。正是因為如此,儒家傳統中并不缺乏神圣性。作為個人,應該把這種神圣性實現出來,而不是對其加以褻瀆,泯滅了作為人的本性。
對于現實的人而言,自我實現離不開家庭、社會,他充分肯定家庭、社會在自我實現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和價值,強調必須要認清并且處理好個人與家庭、他人及社會的關系。
二、家庭、社會在自我實現中的價值和作用
杜維明認為自我實現絕不僅僅是個人的事情,而是向他人的奉獻精神,是獻身于比自我更大的事業之中,因而,自我實現離不開家庭、社會,是在家庭、社會中進行的。家庭、社會對于個人而言,不僅具有工具性價值,也是其目的性意義所在。
杜維明認為家庭是自我實現發生的場所,“齊家”的能力意味著把封閉的私我轉化為開放的自我。借用現代社會學的說法,就是家庭是個人社會化的重要場所。“儒家把‘家視為終極自我轉化發生的場所。這樣一種洞見,從精神性上來說是深刻的,從社會政治學上來說是富有意義的。”[5]138杜氏把家庭看作自我轉化的場所,承認并尊重人的具體的生存脈絡,體現了對傳統儒家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杜維明肯定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在自我轉化中的作用,認為對家庭其他成員的真實感情是自我轉化的手段。在情感的作用方面,他與梁漱溟的觀點是類似的:都肯定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在道德中的重要作用,體現了對傳統儒家的仁愛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杜氏認為應該尊重家庭成員之間的血緣親情,而不能把天倫之情與其他情感完全混同、等量齊觀。他曾經多次對墨子的“兼愛”觀點進行分析,認為與儒家思想相比,墨子沒有考慮到人的現實的生存脈絡。他認為:“父子之間真摯的感情是一個我們經常遇到的事實。不顧及具體的人類處境而建立‘兼愛這樣抽象的原則就是忽視人的生存脈絡,而正是在這樣的生存脈絡中他的理想才能得以實現。因此,儒者堅信博愛的實現必須以一個具體漸進的含攝過程作為起點。”[6]36杜氏認為兼愛的目的是沒有問題的,問題在于墨家忽視了人的生存脈絡,把人看作是抽象的人。人在生存層面的實現當中具有特殊性、具體性,對人的血緣關系和具體生存環境都應該尊重,不能忽視人的具體生存環境,抽象地要求自我的實現,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杜氏看到了家庭作為人的生存脈絡的重要性,主張應該對其加以尊重而不是簡單地否定,體現了對特殊性認識的深化。
但是,杜氏并不因此否定理性的作用,他認為,自我轉化依靠的是特殊情感與普遍理性的結合,即既要尊重個人生存脈絡的特殊性,又不能忽視人在本體上的普遍性。在我國傳統文化中,特殊性與普遍性的關系問題歷來是個理論與實踐中的難題。對家庭的重視往往導致了狹隘的宗法集體主義、裙帶關系;對家庭的超越產生的是墨家的“兼愛”思想,這種思想又難以被人們所認同和遵循。杜維明在這個問題上既看到了特殊性的不可或缺,又不止于特殊性,主張在終極的高度上對特殊性的超越,實現特殊性與普遍性的結合。也就是說,既要尊重家庭,又要超越裙帶關系等狹隘的小團體觀。
杜維明認為人類社會是自我實現的必要場所,個人的自我實現離不開他人、家庭、社會。他認為:“對于我們的自我實現,他者的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因為我們很少會在孤立絕緣的狀態下進行修身。正是通過不斷的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我們才逐漸學會欣賞作為一種轉化過程的自我觀念。”[1]122在杜維明看來,個人與社會、他人的關系是結構性的關系,而不是暫時性的、僅僅工具性的關系,個人根本不可能存在完全脫離他人、社會的個人修身,正是在人與人之間構成性的相互關系當中,我們才能實現對自己、對他人、對社會的正確認知和行動,個人轉化與社會轉化是統一的過程。自我轉化的最高境界和理想目標是實現群體的終極轉化。正是在此意義上,自我實現不僅僅具有個人的意義,也具有社會的意義和價值。
三、自我實現的方法
杜維明沿襲了傳統儒學依靠自力的傳統,認為自我實現首要的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雖然自我實現具有本體論上的根據,不過,他明確指出,本體論上的潛在性與生存狀態上的實現過程存在著區別,潛在性并不必然意味著現實性。修身是自我轉化最重要的途徑。
杜氏認為修身也就是學做人的過程。整個儒家都有一個信念,那就是對人性的相信,相信它能夠臻于完美;不過人性不是自足的,它需要不斷學習修煉。學的內容應該包括傳統儒家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這些都可以被理解為修身的形式。當然,在現代社會,修身的內容和形式需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有所不同。他認為自我實現是從行為到思想的各方面的自我超越,即使是作為訓練身體的禮,體現的是社會的要求,而不是空洞的形式主義。
在杜氏看來,修身必須理解他人的意義和價值,把自己放在廣闊的社會關系中進行。“自我的實現,要求我們超越自身的局限。我們通過助人自立而立己。與他人的關系,作為一個完整的自我修身的進程,必須遠遠超越最起碼的對他人的寬容。理解別人的存在的能力,對于立己是至關重要的。……我們只有通過幫助別人去樹立自己,才能夠樹立自己。”[4]11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杜氏認為修身是在與他人的關系中進行的,它絕不僅僅意味著個人技能層面上的發展,而更多的是個人對自我與他人之間的關系的正確認知及行為。
修身的必然結果是個人的道德性體現在人際關系之中,也就是傳統儒學的道德發展的四個階段: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在杜氏看來,在這四個階段中前者是后者的必要條件,后者也對前者起到促進作用。更進一步說,前者是在后者中不斷完善的,即修身需要在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實踐中不斷進行。他認為,這四個階段“不能被認為是直線式的運動。若要齊家,人們首先要修身;若要平天下,人們首先要治國等等,當然這些都是正確的。但是,我們或許也可以這樣說:修身必然地要導致齊家,因為在儒家學說的脈絡內,認為修身離開人際關系而獨立進行是不可思議的。因為家庭關系為人際關系的基本層面,是修身的一個必要部分;并且,從最終發展的觀點來看,修身也必然地要導致平天下。事實上,除非最終導致平天下,那么它就不算是充分地表現了。因此,從實際的觀點來看,修身是一個延續的漸進含攝(inclusion)過程。”[6]35在杜氏看來,修身與齊家、治國、平天下是一個邏輯上共同進行的過程,意義上也是同等重要。它不是單向的一個維度,而是多維互動的過程,圖示如下:
邏輯脈絡不是: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邏輯脈絡應該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杜維明的思想與他之前的儒學思想相比,一個非常明顯的變化是他注重群體在自我實現中的作用。如前所述,杜氏繼承了傳統儒家的思想,認為自我實現主要依靠人的自力,不過他深刻地看到了本體上的性善與生存脈絡存在的差別甚至對立,他認為雖然儒家學說中沒有原罪的觀念,但是人在現實中有“惡”的表現,即脆弱性、易墮落性、甚至自我毀滅的傾向,因而自我轉化不僅需要自力,也需要他力。盡管缺少關于‘墮落的神話,但人的脆弱性、易墮落性、邪惡性等,在儒家的符號體系中都得到了充分認識。儒家敏銳地意識到了人類的自我毀滅傾向,更不用說懶惰、邪惡、傲慢等類似的傾向了。正是這種對人在自我修養中碰到的巨大困難的深刻意識,促使儒家把人的精神發展界定為一種群體行為。一個孤獨的人在完全孤立的狀態中試圖尋求自我拯救,而又沒有來自群體的切身支持,這種觀念在儒家社會中是不可思議的。儒家更珍惜的途徑,是通過與日益擴展的人際關系圈的交流和參與去進行自我的修養。[2]149-150杜氏認為必須在人際關系中才能實現自我轉化,脫離人際關系的自我實現是不可能的、不存在的。這種觀點實質上與當今我國社會的集體主義精神存在著內在的相通,甚至可以說,在絕大部分內容上是一致的。
四、克服兩種錯誤傾向
雖然在本體論上,杜氏認為人都有自我實現的潛在性,但是,他深刻地看到了人在生存層面與本體層面的差異,對自我實現中出現的偏差、誤解和錯誤進行了明確的分析和解讀。他主張在自我實現過程中,要克服自我中心主義和裙帶關系兩種錯誤傾向。
杜氏毫不諱言傳統社會人際關系中存在的自我中心主義和裙帶關系問題,他認為這些都是對自我實現的背離。在他看來,自我轉化不是單純個人自己離群索居的轉化,而是在人際關系之中的轉化。杜維明深刻地看到了人的社會本質,堅決反對自私自利的自我中心主義。他指出,自我是處在社會關系之中的,“作為關系的一個中心,自我在不斷地發展。它不是一個封閉的體系。相反,它總是向著人類經驗和人類關系的其他層次開放。在這個意義上,自我,作為關系的中心,涉及到一個在不斷發展中的人類關系網絡里不斷進行擴充的過程。因此,我們必須把實現自我的真正進程同自我中心或者自私自利區別開來。要真正實現我們自己,我們就必須超越我們的自私自利和自我中心。”[4]7
在杜維明看來,應該充分重視群體的價值和意義,但是絕不意味著一種狹隘的群體觀。在自我實現中,還應該克服裙帶關系,即狹隘的群體觀或集體觀。在傳統中國社會,裙帶關系是難以克服的頑疾。就如貝淡寧所認為的:“儒家的觀點是親情紐帶應該從親密的人延伸到其他人,強度逐漸減弱。如果親人和陌生人的紐帶發生沖突,親情常常要被優先考慮。”[7]33費孝通曾指出,我國傳統社會是差序格局。針對這種情況,杜維明指出:“如果我們不能同那些與我們沒有血緣婚姻關系的人們建立有意義的關系,我們的家庭主義就蛻化成了裙帶關系。這也是另一種形式的結構上的局限性。同自我中心主義一樣,裙帶關系也使自我局限于一個小的圈子里。從短期來看,外加于自己的孤立主義或保護主義,可能會給我們一種虛假的安全感,但是最終它將使我們麻木不仁,減弱我們的創造力,并且腐蝕上天賦予我們的人性。[5]139-140在他看來,裙帶關系不僅不能給個人和家庭帶來利益,反而在根本的意義上損害了個人的自我完善以及家庭利益。從人與人之間相關性出發,杜維明認為,裙帶關系局限在非常狹隘的家庭或家族的圈子中,沒有認識到個人與他人、社會甚至自然的相關性,雖然在一定時間和空間里可能會得到一定的利益滿足,但是從更長遠和更廣闊的時空背景中,對人性本身、家庭和社會都是嚴重的腐蝕。
在杜氏看來,裙帶關系是由家庭主義錯誤發展而來的一種狹隘的集體觀。他認為,我們應該尊重個人的生存脈絡,即尊重家庭在個人成長中的重要性。但是,對特殊性的尊重并不等于特殊主義,我們應該超越特殊主義,實現普遍主義。這樣,事實上,他就對傳統社會存在的各種狹隘的團體觀進行了批評,認為它們都是出于對特殊的重視而滑向了特殊主義。
杜維明認為,自我中心主義和裙帶關系等現象的存在既有認識上的根源,又有實踐上的原因。認識上的根源在于主體沒有真正認識人的本性,沒有認識到他人、社會的意義,從而使自己局限在個人或家庭的小圈子里;實踐上的原因則在于社會、群體在個人的自我轉化中的作用沒有很好地得到發揮。要克服這兩種錯誤傾向,首要的是關于人的意義的真正建立。自我作為人際關系的中心,必須要真正理解人性、理解個人與他人的關系,認識他人、社會群體對我們的意義。杜氏認為,只有真正理解人之意義,才能超越家庭、小團體等狹隘的集體觀,才能超越自我、家庭、國家,乃至超越人類中心主義。
五、對自由主義和社群主義的超越
杜維明的群己觀非常獨特,其邏輯起點是個人的實現,而其最終的落腳點卻是在群體中實現自己,所以這究竟算是社群主義的還是自由主義的,就產生了困難。在通常意義上,儒家包括現代新儒家都被視為社群主義的代表,雖然,儒家很少談人權,但并不能說明他們就否定了個人的自由和權利,就如狄百瑞指出的“沒有任何證據可以斷言,在儒學和大多數國家都贊同的人權之間,存在什么內在的不兼容。”[8]142而只是說明包括現代新儒家的儒家思想對人與人類社會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的深刻理解和認知。儒家反對原子式的個人主義,而是主張個人與社會的構成性作用,就如社群主義所主張的“對于個人的認同來說,個人作為其中一員的社群是構成性的,而不僅僅是暫時性的或偶然性的。”[9]242
杜維明認為群己之間絕對不是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而是即此即彼、亦此亦彼的關系,二者在本質上具有統一性。個人、他人與社會都具有目的性價值和意義。如果個人是有意義的,個人相加所組成的群體無疑也是有意義的。如果只是個人的自我實現具有目的性價值,而他人、他人組成的家庭或社會沒有目的性價值,那么,就會形成悖論。同理,如果只有社會有目的性價值,而組成社會的個人卻沒有,這是不可想象的,存在著邏輯上的自相矛盾。杜維明指出:“自我必須擴充到超越了它的肉體的存在,以取得自己的真實性,因為社會性是組成真實自我的一個側面。然而社會不能被認為是某種強加在個人身上的外在東西。在本質上,這一社會就是擴充了的自我。”[6]31在杜維明看來,個人必須在社會中實現,個人與社會存在著本質上的一致性。這與馬克思主義人的本質觀相類,即在其現實性上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
正因為對個人與社會關系的深刻洞察,杜維明的思想既不同于自由主義,又不同于社群主義。在群己觀上,他提倡以一種高度自覺的、主動的態度把個人和社會聯系在一起,而不是視其為對立關系。他的關注點并不在于個人權利,而在于個人實現。這當然并不意味著他反對尊重個人權利,而是意味著他認為個人價值是在社會中得以實現的,個人權利與社會利益之間并不是決然對立,而是相輔相成。就如安樂哲所指出:“儒家思想既不像自由主義民主模式那樣,把‘手段與目的做嚴格區分,將社會作為實現個人目的一種手段,也不像團體主義模式那樣,將個人作為社會的一種手段。”[10]219-220杜維明的個人思想跨越了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的分水嶺,將個人與社會同作為目的。這體現出在現代社會背景下,其對傳統思想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結語
家庭的道德與對社會的道德孰輕孰重,發生沖突時如何選擇,這是傳統社會乃至現代我國社會所面臨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和現實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家庭的特殊性與社會的普遍性之間的關系,幾乎所有的儒家學者都對這個問題有所論述。杜維明的貢獻在于把握了傳統儒家的精華,以一種綜合統一的思維和方法看待群己關系中的理性與情感、特殊性與普遍性。他既看到了情感在家庭中的重要性,又看到了理性在超越家庭道德、實現社會道德中的作用,強調二者的結合。特殊性與普遍性之間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應該對人的血緣、情感等天然情感充分尊重,強調通過意義的賦予,認識他人、社會的意義和價值。杜維明延續了傳統儒家的差序理論,認為無差別的兼愛忽視了人的生存脈絡,在現實中不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同時,他主張由特殊性向普遍性的超越,體現了對人性的尊重,具有本體論上的深刻依據和意義。
杜維明的理論與前代新儒家學者相比,一個顯著區別在于:他看到了個人與家庭、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克服了單向度思維模式的束縛。以往的儒家都對人性過分樂觀,忽視了人性的缺點、弱點,在實現家庭道德與社會道德之貫通方面過度依賴個人自覺。杜維明則認識到人的不可避免的限定性和缺陷性,強調集體、社會在自我實現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群己關系上,杜維明的研究很少牽涉到對利益、權利等的分析,使得其研究成果缺乏經濟層面和制度層面的深刻洞察;他雖然看到了社會與人的互動作用,認為應該在社會中自我實現,但是對于在群體中如何進行自我實現,他則幾乎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方法措施,這是后來者無法回避、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
杜維明在群己關系問題上的觀點,既不同于西方以個人為本位的自由主義,也不同于以社群為本位的社群主義,而毋寧是二者的結合。他不像西方文化那樣在二元對立的思維中看待問題,而是在多元統一的思維中看待問題,既尊重特殊性,又反對特殊主義,主張個人與集體的統一關系。他的這些觀點與當代我國社會所提倡的集體主義精神存在著內在的相通之處。我們在構建和提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集體主義思想的過程中,對傳統的文化精華應該加以繼承和發展,現代新儒家的學術成果具有很好的參考借鑒作用。
【 參 考 文 獻 】
[1] 〔美〕杜維明.東亞價值和多元現代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2] 〔美〕杜維明.儒家思想:以創造轉化為自我認同.曹幼華,單丁,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3] 程顥,程頤.二程集:上.北京:中華書局,1981.
[4] 〔美〕杜維明.新加坡的挑戰:新儒家倫理與企業精神.高專誠,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5] 〔美〕杜維明.中庸:論儒學的宗教性.段德智,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6] 〔美〕杜維明.仁與修身:儒家思想論集.胡軍,于民雄,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
[7] 〔加〕貝淡寧.中國新儒家.吳萬偉,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0.
[8] 〔美〕狄百瑞.亞洲價值與人權——儒家社群主義的視角.尹鈦,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
[9] 應奇,劉訓練.共和的黃昏:自由主義、社群主義和共和主義.長春:吉林出版集團有限責任公司,2007.
[10] 〔美〕安樂哲.和而不同:比較哲學與中西會通.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編校:龍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