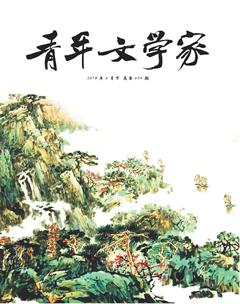由《重訂文選集評》看明清學人對嵇康及其文學作品的接受
摘 要:《重訂文選集評》為明清《文選》評點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對嵇康作品的評點反映了部分學人對嵇康其文其人的評價。《集評》對嵇康詩文風格的評價多與《詩品》《文心雕龍》一致,但明清時人更能欣賞其直抒胸臆、文質自然之美。《集評》對嵇康養生論的評價未能結合嵇康其人,失之淺薄;對嵇康兇終原因的探討較為全面,但仍未觸及根本。
關鍵詞:《重訂文選集評》;嵇康;詩文風格;明清《文選》評點
作者簡介:張嘉慧(1993-),女,漢族,河北滄州人,揚州大學文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為魏晉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18-0-02
嵇康作為竹林七賢的核心人物和魏晉風度的名士典范,歷來為士人學者所關注,風流恣肆的兩晉涌動著嵇康情結,詩意盎然的唐代亦吟唱著叔夜遺韻,時逾千年,明清學人對嵇康的接受又是如何?明代文學評點蔚為大觀,《文選》評點亦成為明代選學研究的主流,及至清初,余風尚存。乾隆三十七年(1722),于光華編纂的《文選集評》由友于堂首次刻印刊行,集評以何焯評點為藍本,集取孫鑛、張鳳翼、李光地等人之說;后又增補邵子湘、方廷珪、葉樹藩等人的評點,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由啟秀堂重刻,是為《重訂文選集評》(以下簡稱《集評》),該本搜羅總結明清選學評點之精粹,為明清《文選》評點的集大成之作。其時,乾嘉考據學風已漸趨盛,選學領域亦然,而評點則走向沒落。因而《集評》在研究明代、清初學人對六朝前作家作品的接受與品評方面有著重要價值,茲考察《集評》對嵇康作品的評點,并以此為依據,探究明清學人對嵇康及其作品的接受。
一、《集評》對嵇康作品之評價
魏晉六朝以來,文學理論與品評蓬勃發展,嵇康作為正始文壇之風標,對于其詩風文風的品評不勝枚舉,其中尤以鐘嶸《詩品》和劉勰《文心雕龍》的評價為人所熟知,幾成定論。《重訂文選集評》中針對嵇康詩風文風作何評價?與鐘、劉二人之見又有何異同?
嵇康的四言歷來為人所推崇,《文心雕龍》謂其“清峻”,失“雅”而含“潤”。《文選》選錄嵇詩皆為四言,《集評》中《贈秀才入軍五首》文末總評云“清思峻骨,另開生面,劉舍人目為清峻,信矣”[1],認同劉勰對嵇康四言“清峻”的評價。但對于未得四言正體之“雅”的評價則似有異議,《幽憤詩》文末總評有孫鑛評點:“筆氣洞達,說意甚透,麗藻中不失古雅,堪諷堪誦,自是四言之俊”,認為嵇康四言堪稱“古雅”。二者之抵牾或許源自評點者對“雅”的不同評判標準。劉勰言“平子得其雅”,則觀張衡四言,如“猗猗秋蘭,植被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美彌嘉。之子之遠,我勞云何。”(《怨篇》)頗具《詩經》風雅之致,劉勰或以此為雅。而孫鑛生于明代,距《詩經》的年代久矣,其所謂“古雅”,或是與唐以來的近體詩相較而言。對嵇康四言是否為“雅”的評判是《集評》評點與齊梁文論的異處之一。
此外,《集評》中多有將嵇康四言與《詩經》相比較的評點,認為其“脫去風雅陳言,自有一種新生之致”,而其“不為風雅所羈”之處在于“直寫胸中語”,且“此叔夜所以高于潘陸也”。由此看來,鐘嶸批評嵇康五言之“過為峻切,訐直露才”在明清評點者看來則成為嵇康四言之勝。不僅如此,在《與山巨源絕交書》的文末總評中亦有云“絕交字立意甚奇,彼時亦只是直吐胸臆,乃遂成一段偉跡”,盛贊其立意新奇、直抒胸臆。不可否認,嵇康五言創作確不及其四言、賦作與論說。但鐘嶸所激賞的文學風格實為子建之“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他從五言詩的“滋味”出發,提倡對賦、比、興的手法要“酌而用之,干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使詩歌呈現出“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的美感,因而不喜峻切之風。而明清學人則單純從嵇康某篇詩文出發來評點其風格,更能夠發覺其獨特魅力,品味出“文質自然”之美。
除上述分歧以外,《集評》中對嵇康詩文風格的評點多與鐘、劉之見相契合。劉勰言《與山巨源絕交書》“志高而文偉”,《集評》中孫鑛評其“文格宏潤,亦是古今一篇大文字”,皆認為此文風格宏偉;劉勰云嵇康性格爽直故為文“興高而采烈”,《集評》評點《養生論》有言“質率而不失其華,筆力自暢”,皆是就其興會充沛、辭采率麗而言;劉勰稱嵇康有詩文“境玄思淡,而獨得乎優閑”,《集評》中亦有評點道其“洗盡宿垢”“淡而率”,皆賞其清逸閑澹之趣;憾然,《聲無哀樂論》因其玄學色彩與蕭統以儒為主的思想不合,未被《文選》選錄,但劉勰所贊賞的嵇康論說之“師心以遣論”,亦可由《養生論》中獲悉,《集評》中有批道“旁引曲證,剖析殆盡,卻并無一迂語”,可見嵇康論說之別出心裁。
《集評》中所錄明清《文選》評點對嵇康詩文風格的評價多與《詩品》《文心雕龍》一致,但與劉勰所謂“平子得其雅,叔夜含其潤”不同,認為嵇康四言亦屬古雅,并更能欣賞其直抒胸臆、文質自然之美。
二、《集評》對嵇康養生之評判
在文學創作以外,“肅肅如松下風”的風姿,“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張,竹林七賢的名士風流,曹室之婿的尷尬身份,剛腸嫉惡的性格,臨刑撫琴的絕響,皆是圍繞在嵇康周圍的話題,明清學人如何看待嵇康其人,茲可由《集評》對嵇康的評點窺視一二。
嵇康著《養生論》,提倡“清虛靜泰,少私寡欲”,但所受爭議頗多。北齊顏之推曾言“嵇康著《養生》之論,而以傲物受刑”,認為“養生先須慮禍,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養之”(《顏氏家訓》),是謂嵇康不知避禍,終喪性命,論養生也無益。元人郝經亦對嵇康養生而不保身不以為然,并言辭激烈:“著論養生,而卒殺身,豈知養生之道哉!太上養心,其次養生,喪心病狂,身死久矣,又奚養生為?”(《續后漢書》)此外,白居易《和〈酬鄭侍御東陽春悶放懷追越游見寄〉》云“生何足養嵇著論,途何足泣楊漣而。胡不花下伴春醉?滿酌綠酒聽黃鸝。”以詩酒人生之快意反對嵇康清心寡欲的養生自持。同時,亦有人贊同嵇康養生之論,杜甫《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云“何必走馬未為問,君獨不見嵇康養生被殺戮”,結合詩意,此處是謂事有出于意外者,嵇康被殺正是其養生中的意外,因而子美并不認為嵇康養生之論有何咎過。蘇軾更是推崇嵇康養生,曾“以嵇叔夜《養生論》頗中余病,故手寫數本”(《跋嵇叔夜養生論后》)。
《集評》中針對嵇康養生的評點與以上所述皆不相類,其中錄孫執升評點:“其所謂生,不過卻病延年,其所謂養,不過清心寡欲,不涉虛幻,正是不墮斫削也,透快明確,可以惑愚蒙,可以砭金石。”此評認為嵇康《養生論》中所言,不同于道教服食丹藥以求長生之虛幻不實,其卻病延年之目的與清心寡欲之方式皆可達到,是可取的。而陸敏樹之評則將嵇康之絕塵脫俗拉回凡俗世界,“聲色利欲,世所謂養生,皆其伐生者也,誰其知之,誰其知而能之”,即便人們知道聲色利欲有損于身體,但又有誰能將之摒棄呢?與前人多結合嵇康生平命運來論其養生不同,《集評》中評點其養生專就文章而談,因而集中于對養生之道的評判,立意較淺,此當為《文選》評點中普遍存在的缺失,因評點者并非專研于某一位作家的作品,因而難以對各位作家的各篇作品皆做到知人論世,故詳于作品結構、主旨、技巧、辭藻的評點,而在總評中則不夠深入。嵇康養生實際上并非僅其《養生論》中所言之清心寡欲,亦有服食之舉,其所希冀的不僅是卻病延年,更在于求仙問道以得超脫。究其所由,魏晉之際,社會動蕩,名教虛浮,司馬氏殘害異己,現實之殘酷無序使得嵇康等耿介之士只能將目光由外界返歸于自身,由現實回避至自然,因而注重養生之道,傾慕竹林山水。但也正因其本性之剛腸嫉惡,故而對于自己不齒之事,可以選擇回避卻不甘于屈服,終遭殺身之禍。嵇康被殺與其注重養生并不矛盾,只是其豐富人格的不同側面,都可歸于其傲岸率真之性情。
三、《集評》對嵇康兇終之探討
對于嵇康何以兇終的討論,自晉以來,莫衷一是。《集評》乃針對詩文的評點,其中雖無評點專就兇終一事發表看法,但亦可從中歸納評點者的見解。
《幽憤詩》題下批道:“天下不平之事,至嵇呂一案無以加矣,司馬家兒不及阿瞞父子,萬萬何言英雄也,安能不生阮公廣武仙之嘆。”嵇呂一案致使嵇康入獄,其冤情已為眾人之共識,評點者在此處將過責歸于司馬氏,認為時無英雄而小人得道,以致顛倒黑白。此篇還有評點云“歸到自警以結全篇,然龍性難馴,莫可追也”,認為嵇康雖在《幽憤詩》中自我警醒,但其性格傲慢所引發的災禍已難以挽回。此災禍當指嵇康對鐘會之拜訪不予理睬,使得鐘會懷恨在心,是以嵇康性傲為兇終之由。此外,尚有與阮籍作對比者,“嗣宗至慎,卒得保身,非薄湯武,徒騰口說,亦何為哉”,阮籍在恐怖的政治局勢中得以保全,是因為能夠謹言慎行,口不臧否人物;而嵇康“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非湯武而薄周孔”,此為二人結局迥然的原因。《與山巨源絕交書》的評點中有云:“非湯武薄周孔不過莊生之舊論耳,而鐘會輩遂以為指斥當世,赤口青蠅,何所不至,然適成叔夜之名矣。”同樣認為嵇康非湯武薄周孔的言論是導致其殺身之禍的重要原因,“非湯武”是不認同權臣以下犯上,“薄周孔”是反對名教之虛偽,皆直指司馬氏政權;而鐘會以此誣陷嵇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于今,有敗于俗”[2]則是其獲罪的直接原因。
由此可見,嵇康性格之傲岸使其得罪鐘會,言辭之峻切則刺痛了司馬氏,嵇康兇終絕非一種因素導致,《集評》中關涉兇終之因的評點對嵇康性格、司馬氏、鐘會皆有所論及,集眾人之力,可較為全面地梳理嵇康兇終的原因。但以上諸論僅就此事而談,歸因雖全,深刻不足,金人趙秉文以為“嵇康之死乃生不逢時,即使沒有鐘會挑唆,像他這般蓋世才華,又加以堅決與統治者不合作之態度,亦是難逃死劫。”[3]此論不局限于嵇康一事,而是站在古今世事規律的角度,掘其根本,頗有見地,卻未得《集評》評點者所采納。
自乾嘉考據學風興起,評點逐漸沒落,在乾隆年間刻印刊行的《重訂文選集評》作為《文選》評點史上唯一一部具有集評性質的著作,實際上具有總結明清《文選》評點的意義,通過其中有關嵇康的評點能夠了解明清部分學人對嵇康其文其人的評價。總體而言,《集評》對嵇康詩文風格的評價與《詩品》《文心雕龍》無太大分歧,但明清學人較之南朝時人更欣賞嵇康作品的直抒胸臆、文質自然;《集評》對嵇康養生論的評價未能結合嵇康其人,失之淺薄;對嵇康兇終原因的探討較為全面,但仍未觸及根本。《集評》對嵇康評點的缺失,一方面反映了評點者對嵇康的考察不足,一方面則受文學評點乃為初學者而設的性質所限;但作為明清《文選》評點的集大成之作,《集評》對于研究明清學人對《文選》作家作品的接受及《文選》作品本身都有著重要價值。
注釋:
[1]本文引用《重訂文選集評》詩文及評點皆據[清]于光華輯《重訂文選集評》,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2年版,后文不再逐一標注。
[2]劉孝標注引《文士傳》,參看余嘉錫撰《世說新語箋疏》,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44頁。
[3]袁濟喜,高丹《嵇康傳箋證》,《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2期,第1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