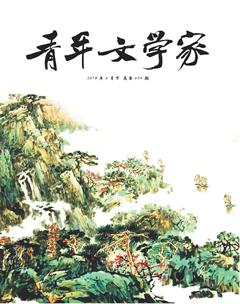《模仿者》的權力與規訓主題探究
摘 要:從權力與規訓理論對《模仿者》進行深入細致的解讀,圍繞權力是如何對受殖者的身份和心理進行規訓和壓迫,以及主人公在困境中對規訓做出的頑強反抗和最終走向流離失所的過程,揭示出西方霸權對反抗力量的收編是受殖者無法改變的宿命和創傷,從而表明局部斗爭不能推翻殖民權力。
關鍵詞:《模仿者》;福柯;權力與規訓
作者簡介:張春林,河南商丘人,現云南師范大學英語語言專業在讀研究生。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18--02
對于2001年諾貝爾文學獎的獲得者──印度裔英籍作家維·蘇·奈保爾而言,第三世界國家的歷史與現狀始終是他關注的重點。《模仿者》作為后殖民文學代表作之一,描述了以特立尼達為原型的后殖民國家伊莎貝拉島在英國殖民權力下所遭遇的困境——歷史殘缺、文化錯位、身份模糊以及社會混亂無序,以及受殖者在權力規訓下對獨立身份的尋求和權威的挑戰。因此,作為一部描寫后殖民狀況的紀實作品,受到國內外研究者的重視。多數研究者從后殖民背景,身份認同和飛散視角等方面加以分析。然而針對小說中一系列殖民壓迫與反抗等問題,還沒有研究者從權力與規訓理論來進行探。因此,本文從福柯的權力關系視角入手探析權力對受殖者的規訓和壓迫,從而揭示出被殖民者無法根除的殖民創傷和無奈的臣服,進而表明“局部斗爭”并不能推翻殖民的權力統治。
一、規訓壓迫下的身份喪失
福柯認為,學校兵營,工廠,機關等社會的各個角落,規訓權力就像擺脫不了的魔鬼如影隨形。任何生活在規訓權利制度下的人都受到權力行使者全面的監視與觀察[4]95。在《模仿者》中,代表英國殖民權力的學校對受殖者的規訓和壓迫無處不在。辛格作為小說的敘述者,以回憶錄的形式描寫了一段童年時期在伊莎貝拉島上學時的經歷,作為在權力掌控下的“小白鼠”,時刻學習和接受英式文化和教育。“學校建筑也成為一個訓練機構”[4]96。在回憶中,教師對學生的壓迫亦是隨處可見。“格蘭特少校起了這個名字并發揚光大。他是個非常會取名字的人。”[1]128。格蘭特少校作為英帝國權威的代表擁有命名權,命名是對一個人乃至一個國家屬性的決定和掌握,是對附屬者的規訓和教化。作為權力的象征,教師則認為“身為黑人男孩,伊頓的真實角色是花園或者院子里幫忙的男孩”[2]135。這樣的殖民教育,使受殖者精神麻痹,否定自己,因此“我們是天生的模仿演員”[2](133)。除此之外,福柯還指出學院的建筑就這樣成為一個監視機構,[4]96監視者一雙看不見的眼睛隨時都在監視著每一個囚犯。[4]105在小說中,主人公辛格多次提到“我被標記了,我被注意著”[2]93,一種內心的恐慌和無助使其更加屈服在強大權力面前,監視作為一種無形的力量,觀察著所有人的一舉一動。“使被規訓的人經常看見和能夠被隨時看見。這樣在檢查者與被檢查者之間就形成了一種權利關系,規訓權力通過整理編排對象來顯示自己的權勢。”[4]101。受殖者成了強大宗主國謙卑恭順的仆人。對他們而言,這個世界早已規劃有致。
此外,作為受殖者之一,辛格在身份認同失敗和人格獨立喪失的情形下,內心雖然掙扎無助,但實際上卻接受了權威所帶來的規訓和身份。首先,他還把自己原來帶有明顯印度色彩的名字拉吉特·克力帕辛格改為英國化的拉爾夫·辛格。“人的名字雖然只是一個符號,卻是界定自我身份認同的重要標志。辛格對自己名字的否定,實際上也就否定了自己身份和國家的文化傳統。”[5]40同時,這也是一種對英殖民權力的認可和屈服。接著在其前往倫敦追尋自己身份認同的過程中,與桑德拉結為夫婦,“也許是和桑德拉結婚后的影響,我開始隨波逐流,不僅僅聽從她的,也聽從事情的安排”[2]48。桑德拉作為地道的英國人是“貪婪,充滿社會野心的。”[2]42盡管如此,她純正的血統和語言天賦深深吸引著辛格,所謂的吸引無非是模仿的范本,桑德拉對辛格而言只是一個追尋英國身份的來源,渴望從她身上汲取更多的英國傳統和身份認可。這無疑是一場注定失敗的結合,桑德拉作為英殖民帝國的象征對受殖者而言永遠是無盡的勒索和壓迫,就像富人永遠不可能與窮人為伍一樣。而“幸福的首要前提是出生在一個著名的城市。”[2]117辛格是天生的模仿者,模仿首先是一種奴隸狀態的標記,這種標記是無形的規訓和壓迫,并且無法改變。辛格的英國身份認同失敗迫使他徹底成為一個漂泊之人。
二、無力反抗下的宿命
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在小說中,身為傳統印度人,辛格父親的反抗是在長期沉默中爆發的。“他一瓶接著一瓶打,一直用鋸齒的可口可樂瓶做武器。”[2]102。作為西方殖民的代言物,可口可樂在辛格父親眼里等同于帝國權利的壓迫與欺凌,怒不可遏的民族情緒使他喪失了理智,他排斥自己的妻子,西塞爾,以及所有代表西方霸權的事物。但被殖民國家始終處于一種進退兩難的困境,它既不會被殖民國家完全同化,徹底失去本土文化和傳統,也不會毫無雜質地保留原有的本色,一塵不染。它處于一種不接受也不拒絕的邊緣地帶,渴望成為宗主國一份子永遠是不切實際的事。辛格父親在面臨認同失敗后默默接受了在當地的教育局工作,得不到西方帝國的身份認同卻依舊處于被其壓迫欺凌的狀況,辛格父親從剛開始“忠誠的奴隸”轉變成了反抗殖民者的奴隸領袖。父親的背離首先體現在騎車載人的“知法犯法”,“我父親,一位政府公務員,選了一條主路公然違法,這讓我非常吃驚。”[2]122接著,父親領導的碼頭工人罷工和遷徙是反抗的極端體現,起義運動往往是受壓迫者最無效最脆弱的歇斯底里,在強大的權威面前只不過是一陣熱血來潮的無聲吶喊和歸順前的無力掙扎。當然,在小說中,父親運動的失敗也早已注定,“像父親這樣的運動無法持久”[2]132父親的反抗最終淹沒在強大權力的漩渦之中。“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民反抗往往都是以悲劇告終,而反抗者最終成為權力系統運轉下的潤滑劑。
相比于父親極端盲目的反抗,辛格的抵抗或許顯得更加明智與冷靜。辛格的反抗之路是在遇到布朗之后開始的,這個對自己種族有屈辱感的黑人男孩迫切為受苦受難的受壓者發聲說話。《社會主義者》的發行是標志著成功的開始,政治覺醒掀起了浪潮,呼吁著擁有自己的國家屬性和政治獨立,但長期處于被殖民狀態的伊莎貝拉早已喪失本國經濟產業和教育制度,甚至政治自由也無力使受殖者的心靈從停滯狀態中擺脫出來。但在布朗和辛格建立的新黨派和慷慨激昂的演講組織下,人們渴望擺脫壓制和追求自由平等的情緒被成功調動起來,而“我們也被成功弄得頭暈目眩”[2]203當他們真正開始實行政策的時候卻是舉步維艱,辛格鼓勵一位當地人生產當地罐頭失敗了,然而轉向制作罐裝進口黃油卻成功了。當地人不接受當地水果卻熱衷于進口黃油,這不單單指食物問題,而是象征著兩個國家的抉擇與趨同,崇洋媚外是解釋不了這個問題的,曾經被英國殖民過的伊莎貝拉依舊隱存著對英帝國的趨附與認可。在他們的潛意識里,已經接受了經濟落后,地位低下,傳統落后這種被灌輸的思想,哪怕國家自由和解放了,心被壓制久了容易變得呆滯與毫無主見。因此,在一群幾乎喪失自主性的群眾中找出一條自主富強的發展道路是困難的,“我們很快發現自己依靠的不過是一群暴徒,我們對暴徒的掌握只不過來自不牢靠的言語。”[2]210我們用虛無縹緲的言語激勵著群眾結果無非是帶來了一群激進分子,這一場由兩個人掀起來的運動無疑是不牢固的不科學的。到最后,辛格迫于政治形勢的壓力,逃避到倫敦重新追尋他的身份認同,直至成為流離失所之人。
正如福柯認為,“局部斗爭一開始就是沒有希望的,而現代生存美學夸大了個體的精神力量,它們最終都不能改變資本主義社會和被權力奴役的處境。”[3]172。辛格的父親,布朗和辛格都為擺脫英帝國霸權和規訓做了一定的努力和貢獻。弱肉強食是次要,根本問題在于他們三者自身的身份矛盾性和模糊性,辛格的英國身份認同的失敗,辛格父親身為象征西方的傳教士的失敗,布朗去英國追求政治自由的過程等都表明在反殖民斗爭中,個人力量和反抗往往是形單影只,在堅不可摧的殖民機制面前猶如飛蛾撲火。福柯指出,“局部斗爭就是直接斗爭,以個體擺脫規訓為目的。”[3]173從結局來看,發起局部斗爭的三者始終沒有擺脫規訓,整個國家又談何擺脫帝國壓制?從某種意義上說,局部斗爭更可能是規訓權力的一種策略,只有讓被殖民者進行斗爭,權力和規訓才能更好地發揮其效力。針對局部斗爭,殖民者權力中心隨時調整自己的方位,把斗爭力量收編到自己的系統中去。這樣,反抗便徹底失去了意義,成功更無處談起,反殖民斗爭陷入了一種進退兩難的境地,而沉默和死亡成了被壓迫者刻板式的宿命。
三、結語
對于被殖民國家來說,在強大西方霸權的掌控之下,身份的“流離失所”是一個種民族乃至一個國家永遠抹不掉的悲痛和創傷,小說中,辛格對外來文化向往又抵抗,對源文化排斥又無能為力,并經歷了一段目的性的傀儡婚姻,展開過一場外實內虛的種族斗爭,其都陷入西方霸權系統的收割中。然而,時代日新月異,歷史卻不會隨著前人的逝去而消失。一個民族的復興與獨立是一個漫長而艱難的過程,肉體上的壓迫和束縛可以即時解放,但思想上的遺痕卻是一道隱形的墻。不難想象,民族解放既不是盲目激進的敲鼓吶喊,也不是新一輪的規訓壓迫。民族應該擁有科學理性的方針,民族團結和富有創新主見的意識,才能使人們在精神解放的路上越走越遠。
參考文獻:
[1]V. S Naipaul. The Mimic Man [M]. London: Picador, 1969.
[2]蔡安潔. 模仿者[M]. 佛山: 南海出版社,2016.
[3]劉永謀. 福柯的主體解構之旅[M]. 江蘇: 人民出版社,2009.
[4]胡穎峰. 規訓權利與規訓社會[M]. 北京: 中央編譯出版社,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