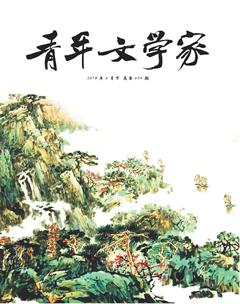《最危險的游戲》中的女性缺席
摘 要:在對《最危險的游戲》的研究中,有學者分析其敘述視角,有學者探討其句法,還有學者分析人物心理,文章側重分析小說中的女性缺席。
關鍵詞:《最危險的游戲》;女性缺席;荒島文學;時代精神;脫衣求真
作者簡介:劉莉(1994.2-),女,漢族,現就讀于西安外國語大學英文學院2016級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英國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18--01
《最危險的游戲》是美國短篇小說家理查德·康奈爾的代表作,小說發表于1924年,獲得當年歐·亨利短篇小說紀念獎。小說講述了來自紐約的獵手雷恩斯福德失去平衡跌落游艇后游至陷船島,在島上他遇到同樣熱衷狩獵的扎洛夫將軍,此人厭倦了對動物的狩獵,發明了新型狩獵對象:人。雷恩斯福德被迫與扎洛夫將軍進行了三天的生死較量,最終戰勝了后者。文章試圖從女性缺席的角度,從對荒島文學的繼承、時代精神和“脫衣求真”藝術手法對《最危險的游戲》中女性缺席進行探討。
一
在《藝術哲學》中,法國批評家丹納指出“要了解一件藝術品,一個藝術家,一群藝術家,必須正確地設想他們所處的時代精神和風俗概況”(丹納 9)。在維多利亞女王統治期間,女性社會地位低,社會對女性要求嚴格。女性的權利受到控制,活動范圍僅局限于家里。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美國也深受其影響。女性的從屬地位是美國家庭和社會生活的重要主題。深受維多利亞時期社會條例影響的美國,女性鮮有機會接受教育,社會只允許男性做重要決定。但這一時期出現了女作家如凱特·肖邦、夏洛蒂·佩金斯·吉爾曼和伊迪絲·華頓,開始關注社會上的“女性問題”,批評維多利亞時期對女性的壓制。吉爾曼的《黃色墻紙》控訴了父權制對女性的壓迫;肖邦的《覺醒》描寫了女性為擺脫父權制對女性束縛的掙扎,但作品受到大眾指責,凱特也險被當地藝術沙龍驅逐。這兩部作品體現了女作家們對女性社會地位的不滿和提高女性關注度的嘗試,在當時產生了一定影響。《最危險的游戲》發生在一戰后的20世紀20年代,當時的女性地位相比維多利亞時期的女性提升了不少,而這部作品全是男性角色,完全將女性排除在外,這一方面反映了作為時代的產物,小說仍受當時的特定風俗和社會氛圍的影響,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女性作家的影響力及社會對女性問題的關注度有待提高,社會對其認可仍需一個過程。
二
《最危險的游戲》中女性形象的缺失是對荒島文學男性傳統的極端化表現。荒島文學是指以荒島作為特定空間的文學。作者有目的的將主人公置于封閉的環境,把人物活動限制在小環境里,觀察人物在原始狀態下的變化,而荒島作為背景用于反映人與自然的矛盾及作者對社會的思考(丁銳 8)。荒島文學在英國小說中有著不可忽視的地位。18世紀的《魯濱孫漂流記》、《格列夫游記》,19世紀的《珊瑚島》都是荒島文學的杰出代表。這些荒島小說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對女性描寫都微乎其微,女性形象或粗俗平庸或是男性附屬品,女性角色處于邊緣狀態。《珊瑚島》中被解救的女孩是為了襯托男主人公的“英雄救美”,《魯濱孫漂流記》中魯濱孫的媽媽是位順從丈夫的女性,《格列夫游記》中小人國的女性粗俗、目光短淺。這些小說中的女性所占比重都很少,女性形象黯然無神。與上述小說相似,《最危險的游戲》的故事也發生在島上,在雷恩斯福德到達陷船島后,島上只有男性和動物們,女性完全處于缺席狀態。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最危險的游戲》繼承了荒島小說的男性傳統并將其極端化,使女性角色完全處于脫離狀態。
三
“脫衣求真”是指通過將主人公隔離于一個封閉的空間,飄然于社會規定、道德之外,展現出其本來面目,從而服務于主題表達的敘事藝術手法。文章認為,《最危險的游戲》通過采用這種藝術手法更好的表明主題。
在女性缺席的環境下,男性可以更直接的展現自我,不必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擾。從《珊瑚島》、《魯濱孫漂流記》以及1954年戈爾丁的《蠅王》,脫衣求真都得到了完美詮釋。在《蠅王》中,正是女性的缺失,杰克才毫無避諱的展現自己屠殺和野蠻的一面。行遠指出“當外在環境被還原到原始狀態時,這群來自文明世界的小天使便很快被還原成了原始的野蠻人”(行遠 5)。《最危險的游戲》也是如此。正是因為陷船島上都是男性,扎洛夫將軍和雷恩斯福德無所顧忌,對社會上弱者生來即為強者服務的觀點侃侃而談,并瘋狂的進行獵殺游戲,展現了他們人性中獸性的一面。假如島上有女性角色,兩位人物會出于給女性留下紳士、彬彬有禮的形象的顧忌,無法真實展現他們的本性。此外,女性的出現會為荒島的背景增添幾分浪漫色彩,島上人物也不會急于離開島,這就無法達到作者通過荒島揭露人性惡和諷刺的目的。
結論:
本文通過從荒島文學男性傳統、時代環境下女性地位低微和脫衣求真的藝術手法三個方面分析了《最危險的游戲》中的女性缺席。文章認為,《最危險的游戲》繼承了荒島文學如《珊瑚島》、《格列夫游記》、《魯濱孫漂流記》等男性形象占主要地位的傳統,并將其極端化,完全將女性角色隔離。另外,小說中女性的缺席也深受維多利亞時期女性社會低下的影響,盡管前有肖邦后有格爾曼在作品中呼吁關注女性社會地位,大眾對此的認知仍有一個過程。最后,作品中女性缺席是“脫衣求真”藝術手法的重要體現,在女性不在場的環境下,男性角色可以毫無顧忌地展示自我,從而達到作者揭露人性惡和諷刺的目的。
參考文獻:
[1]丹納. 《藝術哲學》[M].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
[2]丁銳.“英國荒島文學中女性缺失現象分析”[J]. 河南科技大學, 2009.
[3]行遠. “《蠅王》的人物、主題和結構特征”[J].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