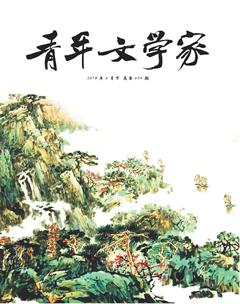《南極之戀》:中國當代“作者電影”的新聲突圍
劉冰 高晶 姜野
摘 要:以電影《南極之戀》為范例,旨在探討“作者電影”在中國當代影視“進行時”中,自編、自導的電影作者們,如何突破“類型化”電影的創作窠臼,在敘事、審美和意識形態架構中實現自身突圍。這種努力正在拓展中國觀眾的觀影角度,在國語大片曾經以“名導演”掛帥為最大賣點之一的格局中,重新建立以“作者”為原點的觀影維度,無疑是中國電影市場與文化空間拓展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南極之戀;作者電影;類型化;時代轉向
[中圖分類號]:J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8)-18--04
引言:
電影《南極之戀》于2018年2月2日在全國上映。上映首日就以2274萬的好成績奪得當天的票房冠軍,上映三天,累積票房7778多萬。
電影取名《南極之戀》,聽來既無詩意,也毫無新意。觀影之前,有兩個淺顯的關鍵詞符號:南極和愛情。而大眾是否走進影院有四種現時可能,這也代表著當下中國電影四種典型觀影群體:聽到大俗名,直接放棄(電影作為藝術享受);有南極,可以去科普或獵奇(電影用來拓展眼界);有愛情,可以去做個假日消費(電影作為消費工具);演員還不錯,趙又廷和楊子姍,即便電影不好看,也可以去養個眼(電影作為追星的精神寄托)。
還有第五種可能:導演沒聽過,但有近期新人導演李芳芳《無問西東》成功之例,也許有驚喜。
在商業電影帶來的審美疲勞期,“驚喜”成了穩定電影市場的一劑“良藥”。
在導演吳有音的簡歷上,算上《南極之戀》,只有兩部電影的導演經歷(另一部為2013年名不見經傳的電影《白相》),但他的編劇和小說履歷滿滿當當,外加數百條影視廣告的創作經歷,顯然是影視圈里寫的多的,作家圈里拍的多的。這兩部電影均為自己原著,編劇和導演,《南極之戀》即取材于他的長篇小說《南極絕戀》。在中國電影界,這樣的人設為數不少,尤其是在“第六代”導演開創“個體化抒情”的創作格局以來,這種“作者電影”并不鮮見。近年來,編導一體的大制作電影依托中國“高概念電影”的發展態勢,滋生出一批具有當代性的“作者電影”。2018年開篇的《無問西東》、《南極之戀》等這些依托史據或科普編導的影片,不單升級了影視文化消費的文本深度,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著大眾的觀影指向。也許,中國電影的概念消費將在新一代的“作者電影”中呈現出新的時代轉向。
一、“作者電影”的歷史與當代語境
在中外電影理論史的脈絡和創作實踐中,法國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曾提倡“導演監管文字、聲音、視覺等所有這些電影的基本元素,都要以電影‘作者,而不是編劇或文本作者等來衡量”[1]的理念,確認了“作者電影”的主張。1943年,他更提出“電影的價值來自作者,信賴導演比信賴主演可靠的多”。1964年,法國電影新浪潮主將弗朗索瓦·特呂弗提出了“電影作者論”,他成為這一概念的命名者、倡導者與實踐者。彼時,這一概念的提出是為了對抗好萊塢電影工業體系中明星(產品符號)重于導演(產品的設計者)的現象。之后,法國電影新浪潮運動、德國的新電影運動、新好萊塢和意大利的新現實主義運動,一同掀起了電影創作上由傳統電影向現代電影轉變的序幕。
“作者電影”這一概念的提出本是堅持導演在電影創作中的核心地位:“一個優秀的導演應該、也必須撰寫自己的電影劇本。否則,他非但無法成為影片的‘作者,相反,只能淪為編劇的視覺詮釋者或故事的插圖作者。”[2]這一概念也成為歐洲藝術電影與好萊塢主流商業電影分庭抗禮的旗幟,但歷史的趣像在于,特呂弗“作者電影”成就的第一個電影作者是好萊塢導演希區柯克以及他之后的一系列好萊塢導演。“在文化書寫的實踐中成了好萊塢電影將自身經典化的有效契機,好萊塢電影由此進入了學院機構化的進程。”[3]
好萊塢是類型電影的始發地。“類型電影”的商業性與“作者電影”的藝術性個人表達是否兼容,在歷經市場的檢驗后早已不容置疑。“作者電影”的倡導者《電影手冊》中這樣寫道:“一個秉賦著最起碼的美學才能的人,如果他的個性在作品‘照射了出來,那么他就會比最聰明的專家更為成功。我們發現,規則并不存在,直覺和感受性戰勝了一切理論”。伍迪·艾倫、馬丁·斯科塞斯、大衛·林奇、昆汀·塔倫蒂諾既是類型片的創作者,也是當然的“電影作者”。
在中國,“作者電影”在由傳統向現代轉變的社會語境中,有著自己獨特的人文構架和表現形式。20世紀上半葉,費穆的《小城之春》最早有了“作者電影的痕跡”,他和同時代作者們的歷史性價值在于“既有現代特征又有民族風格,以大膽超前的實驗和成就卓著的探索,先行性的開啟了現代電影創作思維的歷史意義。”[4]之后的第三代和第四代導演由于特定的社會背景和歷史語境,將自己“作者”的創作印記與歷史現實、國家命運緊密結合。社會責任感與反思心態是當時“作者電影”的主要思路。有人稱第五代導演是中國真正的“作者電影”群體,他們不斷利用現代電影技術和鏡頭語言,用強烈的電影視覺符號打造了一代民族、民俗形象與國際形象。第六代的“作者電影”具有了充分的獨立意識,體制外成長的經歷讓他們更關注邊緣群體,對社會現象的鑒別和捕捉意識敏銳,與法國的新浪潮電影興起有著驚人的一致性。在商業電影大潮的夾縫中,這些“作者”默默堅守著自己的人文品格和審美內涵。
商業化、市場化、娛樂化是中國電影在面臨好萊塢商業沖擊,不得已進行市場化轉型的過程中被動面臨的三個特征。無論從社會學需求還是傳播學互動的角度,“作者電影”的藝術性與個性堅守顯然已不合時宜,在內容和形式上均需要與時俱進的開拓創新。創作者的人文情懷已面臨和時代脫軌的險境,在新時代,新一代的精神探索勢在必行。
二、中國當代“作者電影”的“類型化”遵循與“超類型”創作突圍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陳旭光教授曾在“類型電影”的基礎上,提出中國電影大片中的“非類型電影”和“反類型電影”的概念。“中國‘大片類型是在類型的建構、類型性與非類型性、反類型性的復雜糾葛沖突的態勢中完成的。反類型電影是對于類型電影的某些程式進行有意對抗、顛覆和戲擬化,可能是多種類型的雜糅拼貼,也可能屬于某種類型電影,還可能超越于類型電影,成為很難歸納定位的超類型電影。”[5]
1、后工業社會的“類型化”電影敘事空間
《南極之戀》部分秉承了近年來隨著電影科技手段大踏步更新之后,由好萊塢倡導建立的類型電影模式。電影在原有災難片、愛情片等類型化的電影語言的審美經驗基礎上,以人類探索生存語境的本真意識,豐富了“類型化”電影的敘事場域。一個空間,四壁茫茫;兩個角色,生死相依。面臨死亡威脅的被囚禁的個體,如何活下去?這是一個人類早已不新鮮的話題,但當對抗的背景換成了太空(《地心引力》)、海洋(《少年派奇幻漂流》)、南極等不具備人類日常生活條件的敘事環境,人與自身的對話就超越了過往認知經驗,塑造了新的電影敘事空間。無邊的大海上,浩瀚的太空中,天色一片的雪域,有時安靜得只有自己的心跳聲。人類有意或無意的遭遇了無辜的自然,為自己搭建了近乎無解的困境。視覺的簡化與噪音的消失,消解了人作為生物的集體經驗。它帶來了孤獨,但也創造了詩意的對話空間。由此看“南極之戀”,即是人與人之戀,也是人與自然之戀,這種情感中更包含一種敬畏與博弈,以及在極度困苦中體味到的極致快樂,在極度絕望中演繹出的極致浪漫。“活下去”是一種與自然對抗的生存的本能,“走下去”是一種與孤獨相持的意志的抗爭。在共有精神磨難的主題召喚下,此類型化電影成就了人類歷經前工業社會與自然對話,工業社會與機器對話,走向后工業社會如何與自身對話的自解之殤。
互聯網經濟高速發展的十年,造就了一代“孤獨的焦慮”。在中國,前有《魔獸世界》、《開心農場》,后有《王者榮耀》、《旅行青蛙》風靡火爆。無論是魔獸或王者的“獨孤求敗”,還是從偷菜到養蛙的“佛系修煉”,孤獨感被打造成了一門大生意。人們被鼓勵在封閉的空間中用鍵盤和手指與世界交流對話,最好不費神,不費力。但如果沒有了這個工具,孤獨的人類如何自處?如何相處?生存的欲望來自本能還是“被需”?此類型電影敘事空間在近乎“幼稚般的貧瘠空間”中提出了思考。
2、“超類型”電影美學敘事結構
素有“好萊塢編劇教父”之稱的羅伯特·麥基曾將商業形式的故事概括為:“一個事件打破一個人物生活的平衡。使之變好或變壞,在他內心深處激發起一個自覺,或者不自覺的欲望,意欲恢復平衡,于是這一事件就把他送上了一條追尋欲望對象的求索之路,一路上他必須與各種(內心的、個人的、世界)對抗力量相抗衡。他也許能,也許不能實現愿望。這便是故事的意義。”[6]
在“超類型”的電影敘事中,既沒有明確清晰的人物設置,也沒有陰晴難測的性格對比。工業時代對人的異化,已很難用二元化的臉譜來實現人物一目了然的劃分與定位。在人物與觀眾之間建立當代群譜化的形象認同,讓觀眾自覺進行自我投射,才能在商業化電影氛圍中做到價值判斷的“個性處理”。《南極之戀》的序幕完成于短短的幾分鐘內:機艙逼仄的空間內,物質“土豪”吳富春(趙又廷飾)和精神“貴族”荊如意(楊子姍飾)因各自追隨的夢想同赴“美好的無人之境”,在單刀直入的空難中交待了同赴生死場的敘事緣起。在突破既定愛情電影的先聲模式中,既設定了人物最終結局的走向,又回避了跌宕起伏的戲劇沖突,棄用了矛盾交織的群體博弈。吳有音“廣告導演”的職業經歷,做到用最少的鏡頭控制敘事的節奏,同時又事出有因。
從人物設置來看,一男一女是“愛情電影”的基本設置。但本片的電影結構跳出了“愛情電影”的模式,力圖構建“超類型”電影的綜合配置。女主角因空難失去了行動能力,她的劇情空間被鎖定在幾平米的屋內,男主角承擔了真人實景困境生存的敘事任務,影片用高技術含量的災難片的敘事和科普元素來消解愛情片的煙火氣。盡管這些元素無疑具有很大的冒險性,比如奧斯卡獲獎影片《地心引力》的前車之鑒:導演阿方索面對挑刺劇本里的“科學硬傷”,無奈的照單全收。“這些問題對電影要講的事沒影響。”“哈勃望遠鏡和國際空間站是否在同一軌道上,桑德拉·布洛克能不能在太空艙穿運動背心和短褲,失重狀態下眼淚怎么可能在臉上流淌”等科學常識成為了觀影者詬病該片的話語劍戟。顯然吳有音有充分的自信將這些劍戟阻擋在外:2011年極晝,作為中國第27次南極科考隊員,遠赴東南極中山站。2012年極晝,作為中國第28次南極科考隊員,遠赴西南極長城站。2013年極夜,獨自進入北極圈,到達中國北極黃河站,創作《南極之戀》電影劇本。2014年極晝,赴中國南極長城站,為電影實地勘景。2015年10月,帶領劇組赴南極實景拍攝。導演甚至在“知乎”上開通了個人賬號來回答網友關于南極相關的科普問題。用親身經歷和體驗編劇,不是工業化電影生產的常態,但在敘事的真實性考量方面無疑會提醒那些“瞎編亂造”的國產“高概念”大片,為“作者電影”的藝術品質提出更高的標準和要求。此次登陸南極,使得該片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在南極極地地區實景拍攝的故事長片。正如導演吳有音所說:“對于南極的展現,純粹的自然之美與電影工業之美都不可或缺,兩者的結合,才能把《南極絕戀》中真實的情感與不受限的想象力表現出來。”
在時空處理上,《南極之戀》電影作者暗合了《地心引力》、《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影片的線性時間發展邏輯,沒有采用閃回,倒敘等拼盤式的前言和后語。被遺棄的科考驛站與茫然無邊的南極雪地,逼仄的空間與極端環境中,求生的欲望與“相濡以沫”的精神動力,形成了一種詩意的殘酷與美麗,這就使幾乎只有兩個角色的115分鐘顯得并不枯燥,相反還很有樂趣,甚至不乏溫馨和詼諧的橋段,影院里不時響起的會心之笑大概可以證明,觀眾也融入了這樣的時空。全片在生還是死的博弈中,將當下的時間和情境作為思考的全部語義,回避當下流行的時空拼接和轉換,用鏡頭語言表達豐富的寓意,結尾處極光鯨魚幻象暗合了楊子姍所說的“極光是死去少女的靈魂變化”,“希望生命像鯨魚一樣強大。”作者保留了“生”與“死”的開放性結局,甚至引發了某些觀眾對荊如意之死的“薛定諤”式的猜想,這樣的結尾無疑是“作者”忠于內心,情滿而事不滿的自信之舉,也給觀眾的大腦留下了“個性思考”的空間。
3、當代中國“作者電影”的意識形態堅守
美國電影學者托馬斯·沙茲曾說:“不論它的商業動機和美學要求是什么,電影的主要魅力和社會文化功能基本上是屬于意識形態的,電影實際上在協助公眾去界定那迅速演變的社會現實并找到它的意義。”[7]從新時期電影開始,中國第四代、第五代導演在特定的意識形態時空中完成了自己的觀念敘事,無論是沉重的歷史責任感還是張揚的主體意識都縫合在中國歷史的變遷沉浮中。張藝謀盡管被冠以“影像華麗而意義空洞”的導演之號,但他無疑也為東方主義的中國古典形象做出了自己的努力。陳凱歌電影厚重的人文傳統,也蘊含著精英知識分子對國家意識形態的思考與文化擔當。“第六代盡管是‘歷史的缺席者,甚至是自覺的缺席者和被放逐者”,[8]但他們感性的個體焦慮仍然是中國意識形態不可或缺的縫中觀照。
近觀當代中國電影,作者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將個體遭遇放到了國家主體形象上升的現實語境中。或是現實考量,或是有感而發,不同的是,《戰狼》用從頭至尾的嘶吼和群體情緒試圖達到愛國主義宣講的目的,而在《南極之戀》的愛情故事中,導演自覺的隱藏在攝影機后,不動聲色地完成了個體與家國捆綁的現實政治書寫。小說《南極絕戀》第十四章中是這樣描述的:“富春在兩分鐘的時間里凝固了大約一萬年,然后癱倒在地。他靠在那塊巨巖上,微微顫抖著,靜靜望著遠處風中那面飄舞的國旗。經歷了兩個多月的極地探險后,吳富春同志終于找到了極光站。”在影片中,國旗的出現也是這樣低調而驚喜,一扇生死之門就此打開,一種歸屬與自豪不言而喻。“南極婚禮”、“高空物理”、“空間站獲救”等符號,在隱喻中成功宣介了國家經濟、政治和科技形象,但又打消了觀眾被動接受意識形態的戒心。“中國電影進入一個趨好時代,一個可以高歌猛進的時代;中國電影又進入一個危機四伏的時代,一個需要警醒的時代。面對內外的壓力和挑戰,中國電影必須認清自己的核心競爭力:電影業不僅是娛樂業、技術工業,更是文化產業、內容產業,中國電影的核心競爭力就是講好中國故事。”[9]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需要一批立意高遠,富有人文價值與情懷的好作品。《南極之戀》將“中國故事”融入探索自然之力、探討人性光輝的世界性語境之下,實現商業性效益與藝術性美學的平衡,作為中國當代“作者電影”的一種新聲突圍,具有一定的開拓意義。
正如作者《南極絕戀》小說后記中所說;“這一千四百萬平方公里的寂靜,是寒極,也是風極。它呈現一種與世隔絕的氣質。它如同一尊石像,看淡生死,無畏別離,內心強大,四大皆空。”生死面前,信仰也許微不足道,也許是心靈唯一可托付的歸宿。影片中觀音菩薩和圣母瑪利亞的平行敘事符號,在作者試圖激起的東西方文化碰撞或對話中,隱喻出哲學的思考,也為電影的意識形態打開了多義的解讀空間,思考在當下社會亂象和精神迷失中,情感與信仰如何支撐起人類的精神家園。
結語:
以電影《南極之戀》為代表之一的當代“作者電影”的興起,是中國影視創作“進行時”中,自編、自導的電影作者們,努力突破“類型化”電影的創作窠臼,在敘事、審美和意識形態架構中完成自身突圍的嘗試。這種努力正在拓展中國觀眾的觀影角度,在國語大片曾經以“名導演”掛帥的格局中,重新建立以“作者”為原點的觀影維度,無疑是中國電影市場與文化空間拓展的有效途徑。
注釋:
[1]【法】雷米·富尼耶·朗佐尼:《法國電影—從誕生到現在》,王之光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180頁。
[2]戴錦華:《電影理論與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2頁。
[3]戴錦華:《電影理論與批評》,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頁。
[4]《中國現代電影的前驅(下)》論費穆和<小城之春>的歷史意義》,《電影藝術》1996年第6期
[5]陳旭光:《影像當代中國—藝術批評與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98頁。
[6]《故事—材質、結構、風格和銀幕制作原理》,周鐵東譯,中國電影出版社,2001年,第230頁。
[7]《舊好萊塢/新好萊塢:儀式、藝術與工業》,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2年,第353頁
[8]陳旭光:《影像當代中國—藝術批評與文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84頁。
[9]趙葆華:《電影的核心競爭力從何而來》,《人民日報》,2016年06月03日“文藝新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