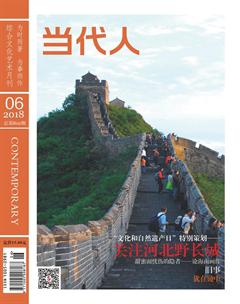關山片斷
李新立
坐在上關鎮
上關,應該在華亭縣東北方吧。我方位感差,也不知道辨得對不對。覺著這名字很有趣,有戰略的味道。說好了去看核桃林,真的去了,林看到了,極目之處,占滿了山坡溝洼,據說有千畝之廣。可惜季節不對,寬大稠密的葉子都脫落了,更別說看到核桃。并不失望,果實能給人更多的饋贈,這不,我們吃上了核桃餡餃子。核桃含油,搗碎了,油乎乎的,再不調其他食用油,擱一點兒調料便可。一盤一盤的,蒸騰著熱氣,眼前擺了蘸吃的小碟,里面分別裝了蒜泥料和辣椒料,可以按個人口味任意選擇,也可以將兩種蘸料和在一起。圍上一圈吃時,好多人發出“嗯”“嗯”的贊許聲,我想那不是裝出來的。
上關鎮有個新建的廣場,比一般的小縣城的還要美麗。廣場的南邊,跨過一條馬路,是糧田。不是常見的普通認知的糧田,那可以算是糧、菜、果、畜的集大成者,可以叫做農家生活體驗地。體驗地由東向西而去,目測過百畝,多個片區構成。先是十余座塑料溫室,里面種了草莓,可惜過了季節,沒有見到草莓開花——我一直沒有見過草莓開花,果子見過,公路抑或社區的小道旁,有人推架子車叫賣,價格不菲。想必花和果子一樣鮮艷。如果是夏天,溫室里的現代化設施都會運轉,比如降溫的風扇排氣、給水的噴頭灑水,聲音喧鬧,卻不覺得煩躁,倒是清涼宜人。
另一個片區是果,果林中間夾雜了蔬菜,可視為空間和肥料利用的典范。都是什么果呢?一塊是葡萄園,矮化了的品種,個兒不會太高,枝蔓會順著搭好的架子奔跑。眼下,巴掌大的葉子脫落得只剩下幾片,還有枯黃。若是夏天,一串串細小的花開時,恰好葉子舒展,綠白映襯,那些枝蔓上的綠色細腳,曲曲扭扭地像是回頭,頗招人喜愛。葡萄花脫落后,脫落處留下一小白點,那就是葡萄了,過上幾天,就長得跟麻籽一樣大了。另一塊是桃園,新技術栽培,枝條被壓得很低。如果春夏進園,這里的色彩更加斑斕,人們一定會第一眼看到,并且歡快地高喊著狂奔而來。
園子不缺水。南邊有河,是汭水還是黑河,沒有搞清,反正都是涇水的支流。水被引了過來,攔成了壩,一個大泵置在水中,為田園供水所用。從標示牌和壩的狀況看,壩還用于養魚。天氣轉冷,沒有見到釣者,也沒有看到魚躍水面。倒是看到了一處半封閉的沙地上,八九只鵝在散步,伸著脖子警惕地看著走動的幾個人,一副不懼怕的模樣。
從上關的整個環境看,東、北邊關山巍巍,北邊河水西流,這地方雖然僻遠,卻倒安靜,適宜游樂養生。我就想,在園子里喝茶散步,或者小住些日子,一定會十分安逸。問題是,我有閑情,也有逸興,卻沒有這樣的時間。一個人奔波,牽扯幾口人的生活呢!不過,我仍有個愿望,夏天的時候,到上關再走走看看。
去看一棵樹
我一直期盼,能與意外的美好和神秘相撞。
上次沒有,這次呢?
我們從崇信縣城出來,朝西而去。過了銅城工業區,左拐,進了坷佬社。坷佬社,我前年因事來過。南邊的山腰上,散著三四戶人家,秋后的麥子已然盡悉裝進了糧倉,兩個草垛旁邊,一棵榆樹盤根錯節,冠蔭如傘,讓我有可供稍息之處。這些院落背靠著的大山,黃土地貌,青黃相間,那青的,是雜草樹木,黃的,是一坨坨的黃土。這種景象,司空見慣,不覺得有什么新奇。當時,有人指著朝南的溝口說:“里面有風景。”我朝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幾棵榆樹擠在一起,遮擋住了視線。想必也沒有什么。加之時間緊,只好離開。
但我記著這句話:里面有風景。
現在,是真要進去看看。進山的路全硬化了,蜿蜒盤旋,通向不可預知的地方。漸漸,黃土甩在了身后,兩邊的山陡峭了起來,我認識的和不認識的樹木也濃密稠郁。人的興奮隨情景也發生變化。兩旁撒了不多的院落,倚山勢而建,院前的杏樹,果實紅綠相間,斑斑可見。可這山里,有不可預知的災害,加上耕地不多,交通不便,許多人家搬到了山外的新農村,只有個別人家,尚未搬走。肯定遲早會搬走的。這就有三個女子,站在院前的一棵杏樹下,討論著新繡的鞋墊。鞋墊不管給誰,這情景都讓人親切溫暖。
左右兩邊的山夾著一條河,自西向東流去。天氣晴好,水清且淺,若是雨天,想必河水會泛濫,水邊東倒西歪的矮小樹木和雜草,可作這個判斷的證明。河有名字,叫“關河”,也有人說是叫“官河”。不管叫什么,都簡單好記,如百姓人家的稱呼。叫“官河”,也不無道理。據記載,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秦王李世民西征西秦霸王薛舉時,就屯兵據守在銅城峽中。“率土之濱,莫非王土”。雖說唐王當時江山未定,但天下大統之后,取得百姓認同未嘗不可。
路越來越陡,山越來越高,樹越來越密。現在明白了,山是橫貫陜甘的關山支脈,在它的腹地,蘊藏著樺樹、青岡、椴樹等樹種,又有麝獐、黃腹角雉、金雕等野生動物出沒其中,不時有厲鳥鳴叫聲傳來,在樹梢間回蕩。關山,以雄奇險峻著稱,駐足,看見三山手足相連,緊密環抱,崖壁如削,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這里水源充足,如果屯兵打仗,那是絕好的關隘。由此說來,李世民與眾將選擇此處,以據其險取勝,的確顯示出了他們用兵上的運籌帷幄。也因此,又叫“關河”,盡在情理之中。
低頭沿北邊的石級而上,兩側的石縫里,野草與野花扎根,分明感覺得到它們得到恩惠般地開啟香唇,說著自然界的贊美詞。果然,數十步之后,不經意間抬頭,有樹撞入眼簾。是槐樹,傳說中的古槐!我原本以為它生長在懸崖峭壁之上,根如磐石,虬枝飛舞,祥光瑞照,或者,至少在人跡罕至的密林之處,挺拔參天,傲然聳立。但不是。
這,多么意外,多么美好!
古槐生長的環境與眾不同。這里的地勢平坦了許多,占地約五六畝見方,只有槐樹獨自屹立,周圍空曠,并無雜樹。這棵樹很有些年頭和來歷,據《崇信縣志》記載,隨李世民西征的大將尉遲敬德,曾在這棵槐樹下歇息、習武、練兵。想想,那時距今約摸1500年之久了,如今的槐樹,十幾個人是合抱不過來的,而樹冠差不多也過了1000平方米,那么,唐高祖武德元年的敬德就可倚樹歇息、率眾練兵,想必當時的樹冠更加濃郁,四周也更加空闊,也就是說,在唐高祖武德元年,槐樹也已經獨立千年之久了——經專家實測,樹齡竟然過了3000年!
所有來自人間的聲音停頓,仿佛有仙樂奏起,縹緲,曠遠。
我感嘆,一棵樹的傳奇,就這樣與歷史風云聯系了起來。而更稱得上傳奇的,應當在于它本身的神性光芒。
第一次面對這樣的大樹,內心竟然有些慌亂,身邊友人的解說是有條理的,進入我視線的卻是散亂的。景象與解說如此不能同步,源于我要一下子把所有景象裝入眼睛的迫切。“樹上附生有五種植物”,我卻看到的是樹枝間有序搭建的鳥巢,有這樣一個屹立不倒的家園,與一棵幾千年的古樹生活在一起,應當是幸運的;“主樹干上分生出八個枝干,又稱八卦樹”,我卻在尋找隱藏在槐樹上的動物,比如松鼠,肯定有,還很多。一棵經歷了風雨的大樹,應當是弱小者的避難所。
“樹身上有幾道鋸痕”,是的,這次,我的確看到了。它的軀干上,布有幾條高低不同的橫直線,它們凸起,宛如疤痕。一定不是有人畫上去的,也不是有人刻上去的。據說,百年之前,有人把槐樹賣給了一位富戶,富戶便帶著人用大鋸去放樹。一般,鋸縫處會溢出潮濕的鋸末,流出乳白色的樹汁,可這棵樹流出的卻是紅色的汁液。于是,驚恐之下,富戶停止了行動。第二天,他們去察看情況時,發現鋸縫已經彌合,于是他們心生敬畏,堅定地認為,樹是不可褻瀆的“神樹”。
遠我們而去的真相,只有古槐知道,大山把它寫在了古槐的血液里。我們看不透,只有用膜拜去努力參解。
我喜歡“彌合”二字。好多人與事物一樣,在某種不得已的環境下,去選擇疼痛地沉默,并以沉默的方式,接受外來的挑戰甚至傷害。“彌合”,并不是本能,它由強大的內在精神構成,以萬般柔韌的毅力作支撐,當受到傷害時,默默地去自我療傷,自我安慰,自我愈合,最后達到自我保護的目的。它所呈現的,只是外在,但這種外在所形成的力量,足以擊退比自己還要強大的敵人。向一棵樹學習,就是接受自然界賜予人類養心修性的教程。
由此延展,一棵屹立幾千年而不倒的古樹,人們堅信它具有了“神”的品質,實在可以理解和接受。它能不倒,就有一種活著的信念,它能“彌合”自己,就能護佑蒼生。槐樹下有不大的神龕,似乎用三塊土坯壘成,顯然,里面留有不久前來自民間的香火供奉。外圍仿樹根的護欄,不高,約80公分左右,上面綁了不少來自民間信男善女的紅絲綢。他們是來祈愿的,祈求出行平安、財源廣進,祈求祛病除災、健康長壽,也祈求學業有成、事業順利,還祈求門戶興旺、五谷豐登。或許,古槐真不能給人們什么,但對古槐的敬重,其實是人認清自己弱小的某一面后,對自然生靈的敬畏。這也是古樹講述給人類的生動一課。
竟然沒有風,一切安靜了下來,我浮躁的心也安靜了下來。
在這里,我肯定在心底說了什么,記不大清楚了。好吧,只愿天下太平,人間倉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