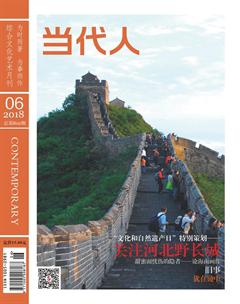開封的亮度
李曉妮
從貴州一路向北,到武漢換車,凌晨才趕到了開封。
夜晚的開封,空氣有點涼而干燥,隱秘地能嗅到古城的味道,什么味道?說不清。古城古在哪里呢?記得在中學歷史課時,老師就說過:“如果沒有金國的騷擾和蒙古人的侵入,宋朝會發展得更好,中國的古老文明,很多是在宋朝閃光的。”
開封有我的老同學,她帶著我在開封老城區游走。既然來了,一定要看看大相國府,這個寺院據說是地底下老的相國寺位置上重新建成的。門楣上有趙樸初題寫的“大相國府”匾額,我看到的開封民國年間老照片里,匾額還是“相國府”,不知道怎么越活越大,成了“大相國寺”?毫無疑問,趙樸初先生寫的大字非常古樸渾厚,且很有佛性。同學故意考我,讓我說說這四個字有什么特點?對于書法,我可從外表欣賞,卻說不出內在的東西。同學看我一臉惶惑,莞爾一笑,揭開了謎底,說:“這四個字,從右到左,字越來越大。”我定睛望去,果然如此。朋友解釋說,“大”字是由“一”“人”組成的,在宋代,宰相一人之下,萬人之上,而宰相必須以國家利益為重,才能千古流芳。國家再大,也大不過神靈。宋朝是有宗教信仰的朝代,相國府里沒有住宰相,而是住著佛教諸位神靈。寺院是神靈住的地方,所以“大相國寺”這四個字,“寺”字最大。
我是一個寫詩的人,怎樣看眼前的開封?不知是一種意象,還是一種精神?眼前的開封已經不是一千年多年前的北宋開封,同學說,北宋的開封城被黃河淤泥吃了。一個“吃”字,令我頓時很糾結,黃河是母親河,開封是母親的一個孩子,怎么能“吃”自己的孩子們呢?還好,老開封淹沒了,開封人齊心合力又建造了一個新開封。同學告訴我,現在開封地面3米下是清代的開封城,再往下3米是明代的開封城,再往下4米才是北宋的開封城,因而出現“城摞城”的特殊景觀。我望著眼前的開封僅有的一截“老城墻”,心想,城下有10米的高度作為城墻的基礎,現有的高度再接10米,老城墻的高度肯定要創造吉尼斯紀錄。
老樹可以開新花。在我的感覺里,老開封被掩埋在地下,已經化作一種營養,供養如今的新開封。北宋年間,開封的河多,園林也多,有一百多座園林;當然,橋也多,比如《清明上河圖》刻畫的著名的橋——虹橋。虹橋已經埋在黃土之下,但紙張上的虹橋依然栩栩如生,只因北宋宣和年間翰林待詔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而不朽,畫中的樓觀、屋宇、林木、人物、市肆、橋梁、街道、城郭刻畫細致,豆人寸馬,栩栩如生。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是獻給皇帝的,皇帝見到一定喜氣洋洋。生活和藝術是什么關系,藝術家們喋喋不休,一幅《清明上河圖》就說明了這個關系,先有北宋開封的繁華,才有藝術的《清明上河圖》,也就是說,先有物,后有心。“心”可以對生活產生反作用。你欣賞完這幅畫作,就會明白什么是動靜相宜,甚至可以省悟儒家的隱世和出世之間的微妙關系。畫幅里的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動態,每個景物有每個景物的位置,一切的一切都透著一個詞——和諧;我真的有點恨自己沒有生活在北宋,如在那個年代生活,一定會和詞人李清照成為好朋友,還要拜師于蘇軾,并向宋徽宗學習瘦金體書法,不至于心如浮萍,找不到做人的根基。
我在開封街頭看到了一位放鳥老人,老人家高高地把鳥放飛到天空,這幾只鳥在天空劃出了一個弧形,依然穩穩地落到老人手中的木架上,放飛的鳥和老人激發了我對自由的思考。與現在的河南省會鄭州比起來,我更喜歡開封的寧靜和物價穩定。我在開封住了半個月,有一種慢節奏的回家感覺,不像到了南方的深圳,必須每天上緊發條去拼命工作。人是需要拼命的,也需要休閑,如果不能“中庸”一下,傳統文化也太悲哀了。
一天天漫步在開封老城區,腦海里就產生了一個哲學命題:到底什么樣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比如說開封,是如今的開封真實?還是宋朝的開封真實呢?我眼前的開封是真切的,又是虛幻的,我甚至覺得埋在黃土下10米的老開封才是真實的,因為老開封是有精神能量的。在儒家文化傳統里,官職越大,功名越大,就越能光宗耀祖,越能體現個人價值。一個人如果當了皇上,一言九鼎,可見是一件非常舒服的事。皇帝好當,北宋的皇帝不好當,因為打鐵還靠自身硬,清心、奉公、修德、貴實、明察、勸課、革弊都要做得好,需要為大臣們做出個樣子。從這個角度說,生活在北宋年代的宮廷臣子們是幸福的。宋太祖趙匡胤從當皇帝那天起,就為后代立下了一個規矩——不殺文官,這和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形成了鮮明對比。北宋的真宗、仁宗這兩代皇帝,更是好人做到了極致。我在開封府的殿堂里看到《宋真宗御制武官七條》,條條真知灼見。
水具有很豐富的象征性。戰國時期荀子說“水則載舟,亦能覆舟”, 唐初魏征是一位有智慧的大臣,和唐太宗論政治,把“水”直接比喻為百姓。我在開封看到了很多水,尤其是在清明上河園和龍廳一帶,水波蕩漾。看到了水,就好像回到了貴州;水在開封具有正能量,春秋戰國時期之所以能成為魏國的都城,后來又成為北宋的都城,都和水運暢通有著直接關系。魏國的魏惠王,從山西的安邑移都到這里,修了鴻溝,連接了淮河和黃河。北宋時期開封城內的蔡河、五丈河與汴河溝通起來,形成了完整的城市水系工程。當時的開封城,真的是得益于水路暢通,有了汴河等河流,南方的糧食可以走水路源源不斷地供給都城,養活數十萬宋軍和開封百十萬戶居民。
當然,開封得益于水,也受損于水。大善若水,使得開封承受了168年的恩惠。讓人無言的是,水也曾經成為攻擊開封城的“利器”,開封作為魏國都城大梁的時候,曾經受到秦王嬴政派來的將軍王賁的攻擊,王賁的兵士直接用水淹大梁。到了明朝,李自成的起義軍圍攻開封不下,有人開決口(史學家為是明軍開決口還是李自成軍隊開決口爭論不息),不管是誰挖開了黃河堤壩,不要忘記1642年9月15日那個夜晚吧,黃河濤濤,大水徹底淹了開封城,城內城外盡是黃黃的河水……大水過后,開封城內城外有數十萬無辜生靈葬身魚腹,成為水中冤魂。水火無情人有情,開封不僅有抗擊外族侵略的英雄,也有抗洪的英雄。明朝的于謙就是其中一個,這位杭州人時任河南山西巡撫,以防洪抗洪為己任,他力主在開封城東北方向5華里的鐵牛村鑄了一個鐵犀牛,怒視著欲破堤而出的黃河水。1841年時,黃河又一次在開封附近決口,這時,又一位抗洪英雄來到了開封,他就是在廣州燒鴉片的林則徐。林則徐是清官,也是貶官,當時已被貶到新疆伊犁。可能皇帝也知道林則徐不僅擅長焚燒鴉片,還擅長治水吧,就把他臨時調到開封。凡是實干的人,讓他混天也難,林則徐到開封就開始實干,用了半年時間,組織民工筑起了一道9公里的“月牙堤”,可謂治水業績突出,可是腐敗的清政府依然把他貶到新疆伊犁去了。
我所生活的貴州都勻市是一個小城,使勁地穿越時空看歷史,也很難找到一位對中國有影響的歷史名人,所以遠方有朋友到都勻,我只是帶著他們看青山綠水,絕不談歷史。開封就不一樣了,到了開封,就到了名人“倉庫”,滿眼都是名人:武將有抗遼英雄楊業,抗金英雄岳飛;科學家沈括,發明家畢升;畫家有張擇端、文與可、燕文貴、米芾等,皇帝宋徽宗本人就是造詣豐厚的藝術家,擅長花鳥畫,書法獨創瘦金體;米芾還擅長書法,他與蘇軾、黃庭堅、蔡襄并稱宋代四大書法家;文人就更多了,有蘇軾、范仲淹、歐陽修,還有柳永、李清照……可謂是明星閃爍,光照千秋。很多人說起北宋開朝皇帝趙匡胤就搖頭,豈不知他作為武將,竟然一手創立了文治安天下的王朝。北宋不僅經濟繁榮,文化也非常發達,哲學家周敦頤、程頤、程顥開創“理學”哲學體系,史學家司馬光寫下了《資治通鑒》;在文學創作方面,歐陽修倡導古文運動,柳永、蘇軾、李清照等開創了嶄新的宋詞時代。天才畢升用活字印刷術大量印制佛法經文,北宋創造的火藥和指南針在航海以及戰爭中被采用。
當然,生活在北宋,幸福的不僅有文臣,還有皇帝。國泰民安,皇帝就有時間去鼓搗字畫,對文學藝術傾注更多的精力,身體力行成績斐然的當宋徽宗莫屬。后代人總是埋怨宋徽宗當皇帝當得不合格,但就生命個體來說,宋徽宗趙佶的日子具有屬于自己的“價值”。評價一個民族是復雜的,評價一個人(包括皇帝)也沒有那么簡單。一個人的歷史價值和個人生命價值宜分開評述,抓住一點,不及其余,評述會越來越糟糕。
離別開封時,小心翼翼地懷揣同學送我的一幅絹制《清明上河圖》,而后揮手離開……心中有很多的不舍。這是縮小本的《清明上河圖》摹本,回到都勻,一定要把北宋時代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小心地供在書房,時刻提醒自己做人格局要大一些,為文要看得遠一些,為自己,也為文壇留下些許更加結實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