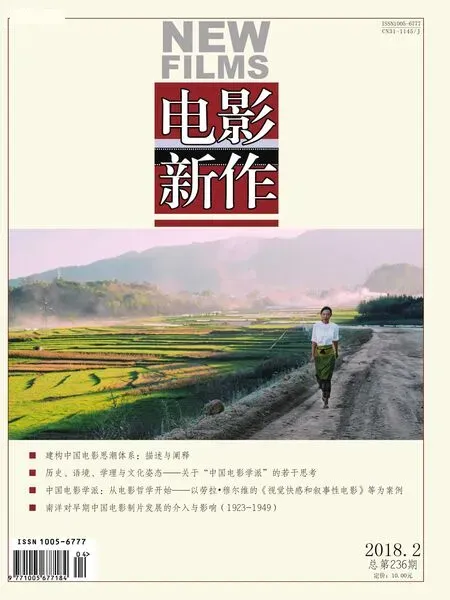經驗共享、道德訓誡與“真實”追求:20世紀20年代閻瑞生故事的媒介呈現
李九如
電影在中國誕生百年之后的今天,一些有趣的“返祖”和輪回現象開始陸續顯現。這從以《畫皮》為代表的中國式“魔幻”電影與20世紀初的神怪片的熱潮對應,以及以《歸來》為代表的家庭倫理影片的“歸來”等,均可看出其鮮明的跡象。不但如此,2014年出品的姜文電影《一步之遙》,居然再次講述了20世紀20年代初期中國第一部長故事片《閻瑞生》的殺人故事,歷史的驚人相似,在此又一次顯露無遺。本文不擬全面探討中國電影的百年輪回現象——這可能是一個很大的電影史甚至社會學和文化研究的課題——而只準備以《一步之遙》為契機,重新回到影片所講述的故事起點上,探討一下將近百年之前,中國早期的媒介——包括印刷刊物、電影,乃至當時正在改良之中的舞臺——是如何呈現這個轟動一時的案件的。眾所周知,《閻瑞生》作為中國電影史上的第一部長片,有著對于“真實”的“拙劣”追求,并因此遭受了長久的抨擊。有意思的是,《一步之遙》恰恰也聚焦于電影這種媒介的真實性(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虛假性),展開了其狂歡化的諷刺性敘事,并由此將閻瑞生故事的相關實踐闡釋為一場意識形態操控的陰謀。基于此,本文意欲從《一步之遙》的媒介真實觀談起,進而回到20世紀20年代的歷史場景中去,考察一下“真實”和電影對它的追求,在當時的歷史語境中,究竟意味著什么。
一、《一步之遙》的媒介真實觀
《一步之遙》可以說是一部關于電影的電影,即所謂的“元電影”。這種自我反射的性質,讓它獲得了一種對于電影自身的反思性。整體來看,《一步之遙》講述的正是一個原先通過操縱大眾媒介玩弄大眾于股掌之間的人,被大眾媒介及其背后的操縱者(連同大眾一起)迫害致死的故事。在這樣一個故事中,所謂的大眾媒介,除了廣播、報紙和舞臺之外——影片也展現了它們對于大眾的愚弄,比如影片開場那個借助新興的廣播技術實現“全球直播”的“花域總統”選舉活動,以及王志文飾演的王天王在舞臺上的表演——最重要的就是電影了。可以說,在《一步之遙》中參與對原先的大眾媒介操控者馬走日進行“迫害”的媒介之中,電影是極其重要的一環。影片揭露了電影所謂“真實性”的虛假,尤其是當改行為電影藝術家的前舞臺藝術家王天王發表了他那一番顯然是學習自“庫里肖夫效應”的蒙太奇理論之后,周韻飾演的大帥之女武六毫不猶豫地放棄了用電影拯救馬走日的計劃,而在此之前她是一位癡迷于電影真實性的電影愛好者。與此同時,已經被逮捕的馬走日——他的原型就是閻瑞生——早就拒絕了那個用電影拯救他的計劃,在那個計劃之中,馬走日需要按照大眾對他的想象,即一個喪心病狂、處心積慮、謀財害命的殺人犯,來飾演自己,然后在那部名為《槍斃馬走日》的電影中,用替身為自己在大眾面前死掉。值得注意的是,這個計劃中的欺騙性,武六顯然是默許了的,由此可見,武六對于電影真實性的堅持,也是有所選擇的。

圖1.《一步之遙》
在《一步之遙》中,馬走日和武六拒絕了電影這種意識形態操控機器的拯救,最終只能選擇以最原始的方式做一對亡命鴛鴦。但從影片中武六對待電影欺騙性的前后態度來看,他們真正拒絕的,顯然并不是電影這種媒介的欺騙性,尤其是,在影片開頭部分,馬走日還在熟練操作著大眾媒介的欺騙技術。在這里,頗有意味的一點就顯現出來了,馬走日和武六所拒絕的,其實是在背后操控電影這種意識形態機器的人,而在《一步之遙》里,這些人就是被稱作“暴發戶”的粗鄙的大帥、他揮霍無度的兒子、投靠了洋人的項飛田以及舞臺兼電影藝術家王天王。當然,這個名單之中本來也應該包括女主人公武六,但她后來顯然被表現為一位“純粹”的電影愛好者,更重要的是,她認同了男主人公馬走日,因此她也就被排除在了這個“暴發戶”群體之外。需要注意到,在影片中似乎是作為噱頭的開頭和結尾的兩段關于馬走日和前清太后對話的講述,并不是毫無意義的。相反,它們標明了男主人公馬走日的身份,一個前朝貴族。影片中有兩處出現了馬走日與他人關于敬稱“您”的討論,由此顯現了“貴族”與“暴發戶”之間的差異。到此可以看出,《一步之遙》實質上講述了一個“貴族”在“資本主義”,或者說新的世界秩序中沒落的故事。
影片中的那些“暴發戶”們,顯然是新世界中的勝利者,而在《一步之遙》這樣一部關于電影的電影中,這些“暴發戶”又都臨時性地成了玩電影的票友。這樣的設置,高度相似于電影《閻瑞生》拍攝時的情況。在此,《一步之遙》十分明顯地透露了它對于20世紀20年代電影史的看法:那個時代的電影,是某些人愚弄大眾借以達到其利益和目的的工具。由此,《一步之遙》形成了一種頗為“精英”化的電影觀念。在這種觀念里,電影這種媒介的受眾,在很大程度上是愚昧的,可以灌輸和操控的,而它的操控者,則抱持著各種不同的利益和目的。更進一步的,這些被灌輸和操控的大眾,又會形成一種強大的壓迫力量。
顯然,在《一步之遙》看來,20世紀20年代的戲劇和電影人,至少在閻瑞生故事的相關文本中,利用或者說操控了電影這種媒介的“真實”性,從而達到自己齷齪的目的。故事片對歷史事實是否尊重并不重要,然而此處對早期電影人和電影史的看法,仍然值得商榷。要重述20世紀20年代閻瑞生故事相關文本的藝術實踐,首先要回到當時的都市語境中去。
二、都市現代性與震驚經驗
20世紀20年代的上海,正在日益成為遠東最為現代化的城市之一。在這座城市之中,工業資本主義剛剛經歷了一次大發展,各種現代消費娛樂場所正逐漸興起,摩天大樓的高度也開始不斷地刷新著紀錄,汽車這種現代化的交通工具,也正在加入日漸擁擠的城市街道之中。總之,這里正在成為一個現代性大爆發的場域。也就是在這個場域里,城市空間本身,和正在興起的大眾傳播媒介,諸如各種報紙、期刊等,不斷地向居住其間的居民和受眾,呈現和傳播著各種本雅明意義上的“震驚”經驗,很快,作為當時的新興媒介的電影,也加入了其中。
關于都市現代性,本雅明有獨特而有趣的觀點。在他看來,都市所呈現給人們的現代性經驗,集中表現為一種“震驚”體驗。借助于對波德萊爾這位“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的論述,本雅明描繪了像巴黎這樣的近代都市所帶給人們的現代性經驗,他將這種經驗集中表述為“震驚”。當談到波德萊爾的詩歌《致一位交臂而過的婦女》時,本雅明表示該詩表達了一種只有在都市空間之中才會產生的震驚感;在另外的地方,本雅明又論述了大眾的出現所帶給人們的震驚體驗,他寫道:“害怕、厭惡和恐怖是大城市的大眾在那些最早觀察它的人心中引起的感覺”。尤其重要的是,本雅明不僅描述了“現實世界”中各種類型的都市現代性所帶來的震驚經驗,他還進一步將目光投向了伴隨都市現代性的興起而來的大眾媒介,把媒介呈現與“現實世界”等而視之,同樣當做現代性震驚的源泉:照相機賦予瞬間一種追憶的震驚。這類觸覺經驗同視覺經驗聯合在一起,就像報紙的廣告版或大城市的交通給人的感覺一樣。在這種來往的車輛行人中穿行把個體卷進了一系列驚恐與碰撞中。在危險的穿越中,神經緊張的刺激急速地接二連三地通過體內,就像電池里的能量。
可以看到,在本雅明那里,“照相機(的照片)”“報紙的廣告版”與“大城市的交通”是一回事,它們共同給都市中的人們帶來了震驚感,因而它們同樣都是都市現代性的一種表征。本雅明的這種“通感”式的論述,被米蓮姆·漢森和張真等人的“白話現代主義”理論繼承了下來并有所發展。在《銀幕艷史》一書中,張真表述了她的早期電影史觀,她提出“電影的感官歷史……平行、交叉于世界語境中,都市現代性在工業資本主義濫觴擴展時代所走過的歷程,并將之具體化呈現”。由此,早期電影既被當做都市現代性的一部分,又被視為是對都市現代性的“具體呈現”。這樣的思考路徑,顯然得益于本雅明的都市現代性論述。緣自本雅明的這種都市現代性表述,將電影放置在了工業革命時代以來涌現的眾多現代性事物當中,作為它們的一員。事實上,本雅明通過波德萊爾的研究,提煉出了一套觀察現代性的認識論模式,這種模式的核心是建立在通感基礎上的隱喻,比如,前文提到的“照相機(的照片)”“報紙的廣告版”與“大城市的交通”之間的同構關系。基于這種認識論,“白話現代主義”所指涉的,不僅僅是早期電影,也包括文學、戲劇乃至當時重要的大眾媒介印刷期刊。而沿著這樣的思路可以發現,閻瑞生案件本身,以及圍繞它所出現的報紙、書籍、期刊、戲劇、電影等各類大眾媒介對案件的呈現——它們構成了早期媒介史上一種不自覺的“跨媒介”實踐——其實均可視為是都市現代性的一次集中的“平行、交叉”顯現。

圖2.《一步之遙》
三、震驚經驗的“跨媒介”呈現
如果說“楊乃武與小白菜”案件是中國卷入近代化進程以來較早的一起引起巨大影響且有大眾媒介參與的案件的話,那么閻瑞生案件大概是最早的一批真正具備“現代性”的案件之一。在當時就廣為人知、后世又不斷被搬上銀幕的“楊乃武與小白菜”案,雖然當時的《申報》有所報道,并且據稱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案件的審理,但從根本上說此案還是一起“傳統”案件。與此不同,閻瑞生案則已經是一起不折不扣的“現代性”案件,這不僅是因為它的審理機關已經是現代化的司法機關,更因為該案的當事人、作案方式、案件發展過程等等各方面,都是“現代性”的。案件的兇犯閻瑞生,是民國初年的大學畢業生,洋行里的買辦,屬于當時中國人中少有的“都市”人群;被害者是一名高級舞女。需要注意的是,她已經完全不同于傳統中國社會中的“舞女”,而是一名參照現代選舉制度推選出來的“花國總理”,這意味著她是經由公共領域產生并存在于公共生活之中的“準明星”人物;在作案過程中,當時作為現代性的標志性象征物的汽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案發之后兇犯閻瑞生的逃跑借助的是輪船、火車這樣的“現代化”交通工具;而他的被捕,又與正在變得無處不在的大眾媒介——報紙有很大關系。從根本上說,閻瑞生案件的發生,跟作為現代化進程之一部分的女性的公共化,有密切聯系。作為一個女性的特殊群體,舞女是中國最早進入社會的公眾視野的人群之一,尤其是那些“高級舞女”,不菲的收入和炫耀性的在公共場合招搖過市——一種公共性的獲得,為她們帶來榮耀的同時也招致了巨大的危險。法國漢學家安克強描述了這種危險性,他寫道:“雖然她們的出行路線是在一個相對有限的范圍之內,但一旦夜幕降臨,她們仍有遭到襲擊的危險。”閻瑞生案件的發生,就是這些新近獲得公共性的女性們遭遇危險的一個極端且典型的例子。可以說,閻瑞生案件,作為一個殘忍的血案,正是本雅明所說的那種都市中的人們所經歷的“大城市的交通”一類的現代性震驚經驗。
這種震驚的經驗,不僅屬于兇案的被害者,它也屬于處在都市中的所有人。經驗的廣泛性和公共性,來自于正日益蓬勃發展的大眾媒介。兇案發生之后,各類媒介很快進行了跟蹤報道。就在案發之后,《申報》迅速登載了“捉拿謀財害命兇手閻瑞生賞格”的啟事?,此后在兇手閻瑞生等人被捕及審理過程中,《申報》還有很多跟進的后續報道。綜觀這些報道,可以說它們構建了一個跌宕起伏、情節環環相扣的長篇故事,而它們的讀者——都市中的公眾們,則通過這些報道,嚴密跟蹤并實時觀察著故事的進展。不僅如此,兇案剛剛發生不久,商業嗅覺極其靈敏而且行動迅速的上海出版商們,就以令人不可思議的速度出版了《蓮英被害記》《蓮英慘史》《閻瑞生秘史》等書,閻瑞生被槍斃之后,又很快出現了《槍斃閻瑞生》等書。這些書籍,向都市大眾們細致講述了兇案的兩位主角閻瑞生、王蓮英的種種生活細節,以及案件本身的詳細過程,堪稱巨細靡遺,纖毫畢現。而這種敘事方式與風格,實際上也延續到了差不多同時期出現的閻瑞生戲劇以及隨后出現的電影之中。
作為對閻瑞生案件這樣的都市現代性震驚經驗的呈現,印刷媒介在那個時代顯示了它“自然主義”式的“紀實性”和極其迅速的即時性,將一種個人化的震驚經驗,迅速傳播到了更廣大的都市空間之中。有意思的是,當下已經被公認為“藝術”的戲劇和電影,面對閻瑞生案件,也在不同程度上向印刷媒介看齊,同樣著意于追求即時性和“紀實”效果,這種追求甚至到了模糊它們各自的“藝術規定性”與“現實世界”之間邊界的地步。在這個意義上,有關閻瑞生案件的戲劇和電影,典型地表征了與都市現代性之間的“平行、交叉”關系。

圖3.《一步之遙》
閻瑞生案審結之后,最先做出反應的,是當時上海的戲劇界。據稱,“就在閻瑞生伏法的次日,即11月24日,《申報》就已刊登了大世界乾坤大劇場25、26日上演《蓮英劫》的廣告”。這表明,早在案件審結之前,戲劇藝人們就已經緊盯著案件的進展,并據以進行戲劇的編排和演練。在大世界之后,當時上海的各個著名戲劇舞臺,諸如大舞臺、共舞臺、新舞臺等,也都緊隨其后紛紛上演了有關閻瑞生案件的時事京劇。時事京劇本身就是正在經歷現代性沖擊的上海所產生的一種改良式的京劇,與傳統京劇的抽象化程式相比,時事京劇有著越來越強烈的“寫實”趨向。這種趨向在有關閻瑞生的戲劇實踐中,更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綜觀各個舞臺上演的閻瑞生時事京劇,不僅劇情發展基本按照案件本身進行編排,更重要的是,在舞臺置景方面,也越來越凸顯機關布景的“真實性”,力求在舞臺上真實復現閻瑞生案件的整個流程。僅在閻瑞生被槍斃之后的第四天就上演《頭本閻瑞生》的大舞臺,在廣告中宣稱其布景“材料異常豐富如洋房書寓旅館汽車火車站跑馬廳一品香群仙戲園新世界自由廳等彩景式式俱全”。與大舞臺相比,緊隨而來的共舞臺在布景之外,又在演員上朝“紀實”性邁出了一大步:因為法租界的“政策優勢”,共舞臺得以讓女演員登臺扮演受害者王蓮英,并且該演員還由于“和上海堂子里的高級舞女頗為熟識”,因此可以“活靈活現模仿蓮英”。更進一步的是,共舞臺在閻瑞生戲劇中,首次真正打破了戲劇與現實的界限,將受害人蓮英的“妹妹”玉英邀請來,并且扮演的正是她自己。當然,將“紀實”趨向徹底發揮到模糊藝術與現實界限的,仍然要數著名的新舞臺。新舞臺的《閻瑞生》,融入了大量現代話劇成分,進一步打破了京劇藝術的原有規定性。不僅如此,它的“紀實”取向,甚至遠遠超越了話劇,在當時,“觀眾最津津樂道的是新舞臺幾可亂真的布景及真實的道具”,這其中就包括真實的汽車,乃至人造的以真實的水做的“河流”等。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新舞臺的表演,在《閻瑞生》中也完全逸出了舞臺的邊界,比如,在劇中登臺的汽車——閻瑞生的作案工具——開出劇場舞臺之后,車上的演員居然會向大街上的行人“頻頻致意”,而劇場之外的人們,居然也欣然加入這種互動之中;在該劇的另一段落中,演員表現閻瑞生躍入水中逃跑,“每當水花四濺至觀眾席上,觀眾無不喝彩”。這種奇特的景觀,當然并非現代主義意義上的先鋒探索,而是當時各種都市現代性經驗之間“平行、交叉”關系的一種體現。對于當時的觀眾來說,觀看閻瑞生戲劇,與通過印刷媒介觀察案件本身的進展,乃至在刑場親歷槍斃閻瑞生,這些經歷之間并沒有清晰的界限,它們是互聯互通的,處于一種混沌狀態。
加入這種混沌化的經驗,呈現的就是早期電影了。與處于改良之中的京劇相比,初生的中國早期電影,更加處于一種自身規定性不明確的階段。這不僅是由于它的發展尚處于幼稚階段,也是由于電影本身就是工業資本主義的一種產物,是都市現代性的直接體現,因此它更加受制于尚未獲得充分發展的都市現代性經驗。跟戲劇一樣,電影《閻瑞生》也追求與現實的高度一致性,并由此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混淆了與現實之間的界限。電影上映于1921年的7月份,此時距閻瑞生被槍斃已經過去了大半年,相比于戲劇來說,作為故事長片的《閻瑞生》,在時效性上稍微差了一點。但考慮到電影制作的特殊性,以及當時技術條件的落后,電影《閻瑞生》在“反映現實”方面,恐怕仍然是電影史上少見的“神速”了。而關鍵在于,電影天生的紀實本性,給了電影《閻瑞生》很多其戲劇版本無法具備的“真實性”優勢。根據《中國無聲電影劇本》所載的影片說明書可知,電影《閻瑞生》的故事,也是嚴格按照案情發展鋪展開來的。這就從敘事上保證了影片的“紀實性”,可以說,它基本上就是一部罪案“實錄”。雖然今天我們已經無法再看到《閻瑞生》的影片,但除了留下的影片說明書之外,當時雜志登載的劇照,也能說明本片忠實于罪案“事實”的“實錄”性質:《時報圖畫周刊》在影片拍攝期間,以一組照片,像連環畫一樣按照閻瑞生犯罪、逃跑到被捕的過程,呈現了電影《閻瑞生》的大致概貌。在演員方面,與專業的戲劇演員不同,電影《閻瑞生》的演員,在身份上與其所扮演的角色高度一致,甚至據宣傳,在長相上也非常相似。扮演閻瑞生的是陳壽芝,他與閻瑞生一樣都是洋行的買辦,甚至兩人還是“至友,據說面貌也非常相像”;閻瑞生的幫兇由邵鵬扮演,巧合的是兩人居然也是“朋友,時相往來還有杯酒之交”;最后,影片的女主角則找了一個已經不再從事相關工作的舞女來飾演,可想而知她要比共舞臺的那位熟悉舞女的女演員更為接近“真正”的舞女,不僅如此,廣告還宣稱女主角與受害人長得“一模一樣”。在拍攝方法上,電影《閻瑞生》更顯示了它相比于戲劇的優越性,本片宣稱基本都是實地取景,這要比“幾可亂真”的新舞臺布景更為“真實”。另外,或許是因為追求忠實于罪案本身的緣故,從目前留下的劇照看,作為長片的《閻瑞生》顯然比我們今天能夠看到的《勞工之愛情》的場景更為豐富,更值得注意的是,在諸多場景鏡頭中,除了大量正面取景的舞臺化的全景鏡頭之外,也出現了少量角度、景別更為多樣的電影化鏡頭:比如王蓮英梳妝的鏡頭,就是背后取景,并且利用了鏡子以呈現更為豐富的信息;閻瑞生逃跑至教堂的段落中,出現了大遠景的畫面。人們有理由質疑,這些都并不是主創人員有意的藝術追求。但有意思的地方恰在此處,主創人員刻意營造的,的確不是“藝術”,而是“真實”,這部號稱“實地表演情景逼真”的影片,如果說有什么鏡頭上的獨特之處的話,那么它也只是追求“真實”地復現罪案的訴求的副產品而已。所有這些,在為電影《閻瑞生》帶來真實感的同時,也模糊了它與“現實世界”之間的界限。

圖4.《一步之遙》
四、敞開媒介中的“道德紀實主義”
《一步之遙》通過王天王的舞臺表演再現了20世紀20年代初期各種閻瑞生舞臺劇演出的現場,對于當時閻瑞生戲劇的火爆程度、互動性等有所呈現。不過,這種再現是帶著價值評判的非客觀再現,王天王被表現為一個滑稽的丑角式人物,而觀眾則顯然是狂歡的群氓。至于在當時的劇場中那種火爆的互動場面,對于置身其中、置身都市的人們是否還意味著更多的東西,《一步之遙》并不關心。這恰是問題所在。閻瑞生舞臺劇(包括電影)演出的火爆,是否可以簡單看作一場意識形態操控的陰謀?顯然,都市現代性的視角,以及對相關歷史細節的重述,似乎可以提供另一種判斷。
從表面上看,各種媒介中的閻瑞生故事,均存在著對“真實”層層加碼的近乎執拗的追求,而這種追求看起來則很接近于我們經常提到的“現實主義”“紀實主義”或者“自然主義”。當然,如果我們就此以這些概念來評判20世紀20年代相關的閻瑞生文本,則肯定離謬以千里只差“一步之遙”了。無論是“現實主義”“紀實主義”還是“自然主義”,作為藝術觀念,嚴格來說它們指向的均是一個個自足的文本。而相比之下,20世紀20年代的閻瑞生文本,如前所述,則通通都是“敞開”的(即便是京劇,也是改良之后的所謂時事京劇,而并非彼時已經發展完備具有充分自足性的作為國粹的京劇),這不僅意味著這些戲劇和電影并不“成熟”,更表明它們與現實世界之間的“平行、交叉”關系。或者可以這樣說,在20世紀20年代的閻瑞生戲劇和電影中,對“真實”的追求,首先表現為這些文本及其承載媒介的“敞開”性,也就是它們與現實世界之間的“平行、交叉”關系。在此,所謂“敞開”或“平行、交叉”,又可與托馬斯·沙茨在描述類型演變的早期階段時所使用的“透明”一詞的意義相互參照。在沙茨看來,早期的電影類型有一個形式透明的古典階段,而在此之前,類型則比透明還要“透明”,它傾向于把電影“作為一種媒介來使用”,如果允許簡化,此時的類型簡直可以稱作社會新聞——這恰是電影《閻瑞生》所處的狀態。從這個意義上說,與其認為閻瑞生故事在追求“真實”,不如說它們追求的是一種現代性經驗的共享,或者是沙茨所說的“社會集體地對它自身的言說”。那些對“幾可亂真”“一模一樣”的執拗強調,其目的在于喚醒觀眾的現實世界視野,進而就此展開有關現代性震驚經驗的共享、交流乃至討論。由此可以說,閻瑞生故事,作為一種現代性震驚經驗,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的不斷講述,對于處在都市“危險的穿越中”的居民來說,構建了一個震驚經驗的交流場——米蓮姆·漢森稱之為“現代型公共空間”。在此公共空間中,早期觀眾得以“從感覺的層面參與進現代性的各種矛盾”,而由此“現代性的各種創傷性后果——或揚棄或否認,或轉化或強調——都會得到反映”。顯而易見,20世紀20年代閻瑞生戲劇和電影的觀眾,作為正在經歷現代性沖擊的都市居民,他們觀看閻瑞生故事的過程,恰正符合漢森所描述的公共領域機制。這種機制使得他們得以逐漸適應都市現代性的劇烈沖擊,進而在適應中確認自己新的都市現代性身份。
當然,無論是印刷媒介的報道,還是戲劇和電影的演繹,所有的閻瑞生故事,最終都呈現為一個善惡有報的道德懲戒結局。在這方面,一部極有可能由鄭正秋編劇的閻瑞生戲劇《蓮英被難記》,在廣告上有如下苦口婆心的詞句:編閻瑞生戲,正秋頗費心血,倘使多編他下流情形,變成宣講拆白教科書,豈不是要帶累看客,無形中受惡影像在腦筋里么?故此多演他犯罪后痛苦,使得大家看了回去作十日想,希望人類中減少殘殺底悲劇呢。
可以說,這種道德化的主題,是當時所有形式的閻瑞生故事的主旨,至少是主旨之一。即便是在電影史上頗受詬病的中國第一部故事長片《閻瑞生》,在震驚化的現代性影像背后,傳達的仍然是一種道德懲戒。這種道德化現象,也成為此后整個20世紀20年代中國早期電影的重要特征。實際上,道德訓誡是古老的中國社會,特別是市民階層,在面對現代性的沖擊之時,所依賴的最重要的一種安慰。在早期電影中,道德教化,更是知識分子所開出的第一例應對現代性焦慮的藥方。
事實上,閻瑞生故事的道德訓誡傾向,也清楚地說明,這些文本并不是真的在追求那種自然主義的“真實”。除去新聞報道之外,20世紀20年代所有的閻瑞生文本,如果說它們有什么藝術觀念的話,那么這種觀念可以稱之為“道德紀實主義”。這一術語一方面意味著一個道德訓誡的情節走向——比如《蓮英被難記》“多演他犯罪后痛苦”的情節取舍——另一方面,則還隱含著某種有關“真實”的道德哲學理念。與徐欣夫等人同屬電影《閻瑞生》的拍攝者,同時也是中國影戲研究社成員的顧肯夫,在《影戲雜志》的發刊詞上,指出了“逼真”的意義:現在世界戲劇的趨勢,寫實派漸漸占了優勝的地位。他的可貴,全在能夠“逼真”。照這趨勢看起來,將來的戲劇,一定要把“逼真”來做范圍。這是什么緣故呢?我們在看戲的時候,要是這出戲不能“逼真”,那么,演戲的自己明明曉得自己是正在演戲,看戲的也只曉得自己是正在看戲,戲劇感動能力的大部分,必因此減少。要是戲劇能夠“逼真”了,那么,演戲的自己已忘掉了自己是一個“扮演著”,以為是“劇中人”,能夠替“劇中人”有同一的感情。看戲的也把自己當做“劇中人”,像親身經歷戲劇中的一番情形一樣,那感動力就增加了千百倍。
顯而易見,顧肯夫是站在進化論的立場上來看待戲劇的“逼真”。進一步說,在他那里,“逼真”又是戲劇“感動力”的來源。而所謂感動,對于顧肯夫而言,即意味著“通俗教育”,實際上也就是道德訓誡。由此,在這種藝術觀念中,真實就成了道德教化的根基。事實上,顧肯夫的藝術真實觀并不孤立,就在這一時期,五四新文學的旗手之一的茅盾,站在進化論立場上攻擊鴛鴦蝴蝶派文學時,就宣稱“中國作家必須先經過自然主義的洗禮”,并且很明顯,茅盾所說的“自然主義”也并不是左拉式的自然主義,相反其中潛藏著強烈的啟蒙,或者說教化的主觀傾向。對于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后的中國知識分子而言,“進步”的即是“道德”的,而真實又被看做“現在世界戲劇的趨勢”,或者被看做文學進化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環,那么順理成章的邏輯便是,真實的也就是道德的。照此邏輯來看,閻瑞生故事對“真實”的追求,從一開始便蘊含著道德的目的和意義,而圍繞著它們所建構起來的經驗的交流場,從一開始也便是一個道德化的公共領域,而不僅僅只是一個感官經驗層面的交流場域。
結語
作為一部故事片,我們當然沒有理由要求《一步之遙》完全忠實于歷史,將《閻瑞生》的拍攝情況按照歷史的“本來”面目呈現給觀眾,但這也并不妨礙我們從其所透露出來的電影觀念出發,以之為契機展開歷史的重述。這里并不擬就電影史的本體問題做長篇大論的探討,但作為一名電影史的研究者,仍然需要指出的是,對于電影史來說,史觀固然是重要的,而歷史本身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更是值得注意的。就《閻瑞生》的拍攝參與者來說,其中的人,確實有不少是“買辦”,但他們中的許多人也的確屬于熱心于電影的知識分子,為此他們在那個中國電影還很荒蕪的時代,組織了同人性質的中國影戲研究社,甚至還創辦了最早的專業電影雜志《影戲雜志》。如前所述,在該雜志的發刊詞上,研究社成員之一的顧肯夫站在“進步”的觀念基礎上,提出戲劇要有“通俗教育的旨趣”,要達到這個目的,“逼真”是很重要的美學方法,而在所有的戲劇中,影戲恰恰是最為“逼真”的。這種電影觀念,在左翼電影觀出現之前,其實是最為主流的“進步”電影觀念之一,并且事實上與《一步之遙》中女主人公武六的電影觀有很大的相似之處。當然,由該社推出的《閻瑞生》主觀上是否完全執行了這種電影觀念,也許是值得懷疑的,但看其對“紀實”的刻意追求,以及在結尾對于善惡有報的道德觀的張揚,可以說,電影《閻瑞生》至少沒有太過偏離顧肯夫的電影觀念。至于影片上映之后,觀眾是否被灌輸和操控,以及由此是否造成了對閻瑞生這樣的個人——盡管那時他已經被槍斃——的某種壓迫。一句話,電影的上映究竟是導致了愚昧大眾的狂歡,還是某種經驗交流場域的形成,由于史觀的不同,以及諸如觀眾接受情況方面資料的匱乏,大概就只能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了。在此,本文傾向于后者,即在20世紀20年代初,閻瑞生案件及其相關文本的產生,尤其是其中的戲劇和電影,經由其“道德紀實主義”的渲染,顯然構建了一個道德化的感官經驗交流的公共領域,在此空間中,觀眾得以強化并修復其所經受的現代性沖擊,以在“危險的穿越中”適應現代性的生存。
【注釋】
①這里的愚弄大眾的邏輯,顯然跟《讓子彈飛》里張麻子以假黃四郎的死來欺騙大眾是一致的。
②這樣的電影史觀,很大程度上與《中國電影發展史》是一致的,后者在評價電影《閻瑞生》的時候,是這樣說的:“《閻瑞生》是一部極端惡劣的影片……影片繪聲繪色地描寫了閻瑞生的犯罪行為,宣傳帝國主義在半殖民地中國所豢養的買辦,如何承襲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極端腐朽墮落的品質,滲透了帝國主義和買辦資產階級的意識……投合了一部分落后小市民的低級趣味,因而也騙得了不少的觀眾。”參見程季華主編.中國電影發展史(第一卷).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1年,第45頁。當然,可以看出,在對待“閻瑞生”這個人物的問題上,《一步之遙》與此還是有很大差異的。在《一步之遙》中,以閻瑞生為原型的馬走日,是一個“正面人物”,而不是“腐朽墮落”的買辦。這是《一步之遙》在歷史觀上的一個重大修正。
③本雅明并未對“震驚”作條分縷析的界定和分析,相反,這種關于都市現代性經驗的概括,分散在他關于波德萊爾的各處論述中,但總的來說,這些論述又是集中而統一的。
④[德]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張旭東等譯)[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140.
⑤[德]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張旭東等譯)[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145.關于大眾,在那些“最早觀察它的人”中,本雅明舉出了愛倫·坡和恩格斯等人作為例子。在這些人的筆下,大眾被描述為機械的、面無表情的、行尸走肉的烏合之眾,他們——大眾們是可怕的和威脅性的。參見[德]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張旭東等譯)[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137-138、142.
⑥[德]本雅明.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張旭東等譯)[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146.
⑦參見米蓮姆·布拉圖·漢森.大批量生產的感覺:作為白話現代主義的經典電影(劉宇清等譯)[J].電影藝術,2009(5):125-134.
⑧張真.銀幕艷史:都市文化與上海電影1896-1937(沙丹等譯)[M].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2:4.
⑨參見張旭東.本雅明的意義.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9:23.
⑩參見吳鉤.楊乃武與小白菜案平反過程.http://www.21ccom.net/articles/fsyl/yulu_2013082890768_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