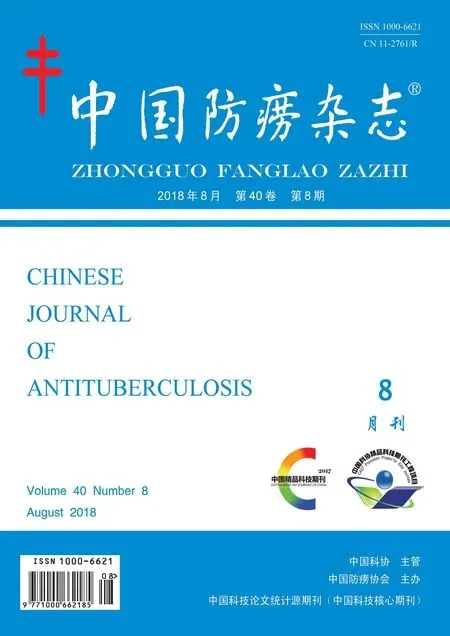兔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動物模型的建立
荀傳輝 蔡曉宇 王傳鋒 買爾旦·買買提
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即布魯桿菌侵襲脊柱引起椎間盤炎或椎體炎時所引發的病變[1],是布魯桿菌病骨關節系統的表現之一,在布魯桿菌病中的發病率可高達65%[2-4]。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患者無特異性的臨床癥狀與體征,僅靠臨床表現診斷較困難[5];臨床上對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誤診并因此延遲治療的患者仍比較多,最易誤診為脊柱結核[6]。因此,迫切需要深入進行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診治的研究,動物模型則是其研究的基礎,國內外有關構建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模型的文獻報道甚少。本實驗通過在動物脊椎體內植入布魯桿菌創建動物模型,需要直接在動物體內進行骨骼鉆孔,使用醫學手段使動物感染布魯桿菌,因而選用了兔等較大型的哺乳動物而非鼠類等體型較小的動物[7]。通過研究發現,相比非近交系兔,近交系兔在感染了結核分枝桿菌之后會造成更多的細菌繁殖,其體質更適合菌株生長,因此認為近交系兔較非近交系兔對結核分枝桿菌更敏感[8]。因在臨床工作中,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與脊柱結核較難鑒別[9],其在疾病的發病機制上有較多的相似之處[10],所以此次實驗選用純種新西蘭大白兔。由于布魯桿菌感染易致在動物體內全身播散、甚至死亡,治療成功率低,且布魯桿菌具有高致病性[11],對實驗室條件要求較高,極大地限制了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實驗動物模型的研究和發展。然而,由于布魯桿菌病發病率上升,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的發病率也隨之增高,較多患者誤診為脊柱結核,且難治患者增加,故亟需改進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的診療方法;因而建立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動物模型,進行相關實驗研究是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防治工作中不可缺少的[12]。
筆者于2017年1月1日至12月30日通過對比實驗研究,在新西蘭兔的椎體鉆孔、種植M5羊種布魯桿菌弱毒苗進行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的造模實驗,目的在于:(1)構建兔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模型;(2)從影像學、組織病理學、細菌學檢查等方面對模型進行綜合評價;(3)為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基礎研究提供理想的實驗動物模型。
材料和方法
一、實驗條件及設備
本研究獲新疆醫科大學倫理委員會審批。本研究中造模實驗由伊犁職業技術學院生物實驗室與新疆醫科大學動物實驗室聯合完成。造模術中嚴格遵守無菌操作、標準預防、動物倫理等原則。布魯桿菌為M5羊種布魯桿菌弱毒苗。所需設備有計算機X線攝影(computed radiography,CR)儀(中國東大阿爾派公司生產)、SOMATOM Definition CT(德國西門子生產);MAGNETOM Symphony 1.5 T MRI儀(德國西門子公司生產)、光學纖維儀DFC295型(德國Leica公司生產)、病理圖像分析系統(美國 Nikon公司生產)、弗氏完全佐劑10 ml(美國Sigma公司生產)、改良Sauton液體培養基(自制)、改良羅氏培養基(自制)。
二、實驗動物及分組
健康新西蘭大白兔48只(新疆醫科大學實驗動物中心提供,許可證:SCKX新2011-0001),雌雄不限,體質量為2.5~3.0 kg。按數字表法隨機將48只新西蘭大白兔分為實驗組16只,對照組16只,空白組16只。所有實驗兔均分籠隔離飼養,居住環境、喂養方式無差別。
三、主要實驗試劑
新疆天康生物股份有限公司生產的M5羊種布魯桿菌弱毒苗(M5布氏桿菌活疫苗),注射量:3×108CFU/ml,每只兔注射0.1 ml。
四、動物模型的制備
1.麻醉方法:用氯胺酮、安定、阿托品聯合麻醉,氯胺酮、安定、阿托品按 2∶2∶1比例配置,用生理鹽水稀釋一倍,約 2.5 ml/kg,耳緣靜脈緩慢推入。手術時輔助質量濃度為0.5%的利多卡因注射液5~10 ml行局部浸潤麻醉。
2.手術方式:取實驗組新西蘭大白兔16只,將麻醉好的實驗動物右側腹部剃毛,左側臥位固定于手術板上。常規消毒鋪巾,沿左側第12肋末端向下至髂嵴作長約6 cm的縱切口,經側方入路顯露第5~6腰椎(L5~6)間盤及上下相鄰椎體。于第6腰椎(L6)體上終板下5 mm處從右前方向左后方,與椎體冠狀面呈30°,采用克氏針鉆孔,孔徑3 mm,深度5 mm,骨孔道止血后填入明膠海綿[13];采用注射器在明膠海綿上緩慢浸注含M5羊種布魯桿菌弱毒苗(3×108CFU/ml)的混懸液0.1 ml,骨蠟封閉孔道。對照組新西蘭大白兔同上法顯露、鉆孔、明膠海綿填入后,采用注射器在明膠海綿上緩慢浸注含有液體培養基的生理鹽水混懸液0.1 ml,骨蠟封閉孔道。空白組16只不做任何處理。術后將所有動物分籠,于相同環境下喂養。動物房接受紫外線照射消毒,每日1 h。8周內若出現動物死亡,立即進行解剖分析后密封送醫院焚燒處理。術后8周影像學檢查完畢后,麻醉下解剖所有實驗組、對照組、空白組大白兔,取材后處死封閉焚燒處理。
五、檢測項目及內容
1.動物一般情況觀察:所有實驗兔自由活動,觀察動物每日活動、精神及進食情況、切口是否感染等。
2.影像學觀察:各組實驗兔于造模后當日及造模后4、8周行X線攝影、CT掃描三維重建、MR檢查,觀察椎間盤及椎體破壞、死骨、膿腫形成情況。
3.組織病理學觀察:造模后8周,影像學檢查完畢后在麻醉下解剖全部實驗兔,顯露L5~6椎間盤及相鄰上下椎體,取椎間盤、上下終板及部分椎體,以及病變組織、膿腫壁、肉芽組織等標本進行常規HE染色,行病理學檢查[14]。
4.布魯桿菌培養:取實驗組與對照組內所有成活兔椎旁肉芽組織0.5 g,勻漿后置于自制的改良羅氏培養基上,36 ℃恒溫培養,連續觀察6周。
5.診斷標準:按Tekk?k等[15]的診斷標準,符合以下標準中2條或以上可確診:(1)血培養或骨髓穿刺培養陽性;(2)標準布魯桿菌凝集試驗陽性;(3)X線、CT、MRI檢查或核素骨掃描證實脊柱受累;(4)病理結果證實為非結核性肉芽組織。
六、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7.0軟件進行數據分析,組間感染率、死亡率采用卡方檢驗或Fisher精確概率法進行統計學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動物成活情況
實驗組術后當日麻醉恢復順利,有2只實驗兔于4周內死亡,2只實驗兔死于造模術后4~8周,死亡率為25.0%(4/16),以上實驗兔死亡后進行解剖未見明顯異常。8周后共存活12只(75.0%),2只因術后4周切口未愈合,出現紅腫破潰被淘汰,其余實驗兔編號為1~10。存活實驗兔均出現消瘦、納差、活動減少等癥狀。
對照組1只實驗兔因麻醉意外于當日死亡;1只因進食、飲水不良于術后第13天死亡,死亡率為12.5%(2/16)。1只因切口感染被淘汰,其余13只兔術后恢復順利,質量無明顯變化,術后8周存活率為87.5%(14/16)。空白組16只實驗兔進食好,8周時仍存活,存活率為100.0%。
實驗組、對照組與空白組死亡率分別為25.0%(4/16)、12.5%(2/16)、0,采用Fisher精確概率法檢驗,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143)。實驗組與對照組感染率分別為12.5%(2/16)、6.25%(1/16),采用χ2檢驗進行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χ2=0.37,P=0.544)。
二、影像學表現
X線攝影未發現實驗組內陽性兔造模椎間隙發生明顯改變、椎體破壞、塌陷及高度喪失。CT三維重建未見實驗兔椎體出現明顯破壞,主要為椎間隙變窄(圖1)。MRI對兔椎體及周圍軟組織、膿腫、脊髓等信號顯示清晰,T1WI示造模椎體上端及椎旁呈等信號或略低信號;T2WI示椎體上端及椎旁呈混雜高信號(圖2~4)。椎間盤可見信號異常(圖5,6)。實驗組術后4周X線攝影及CT三維重建檢查陽性5只,MRI陽性7只;術后8周X線攝影及CT三維重建檢查陽性8只,MRI陽性10只。
對照組大白兔在術后4、8周X線攝影顯示椎間隙無明顯變化,椎體無破壞;CT三維重建未發現造模椎體孔徑較前減小,邊緣較正常椎體硬化,但無骨質破壞,可見椎間隙變窄,無膿腫及軟組織鈣化影;MRI表現為椎體上端及椎旁略低信號改變;T2WI示椎體上端、椎旁稍高信號,椎間盤未見信號異常。
空白組在影像學上無異常表現。
三、大體解剖觀察
術后8周影像學檢查完畢后麻醉下解剖所有實驗組、對照組、空白組大白兔。
1.實驗組:兔傷口愈合良好,無竇道形成。剝離椎前肌與椎體粘連后,可見:(1)纖維環顏色變暗,椎間隙變窄;(2)相鄰椎體上、下終板未見明顯骨質破壞,未能發現原鉆孔部位;(3)椎旁軟組織及腰大肌腫脹,未見明顯膿液;(4)椎旁未見壞死物質及肉芽組織生成;(5)解剖胸腔及腹腔其他臟器未見異常。
2.對照組:兔原椎體鉆孔部位孔洞直徑縮小,未見膿腫及椎體骨質破壞。
3.空白組:兔椎體及腹腔、胸腔臟器未見異常。
四、組織病理學觀察
實驗組組織病理學檢查:兔病椎旁軟組織腫脹區均出現大量淋巴細胞反應及少量類上皮細胞形成(圖7~10),無凝固性壞死物質及死骨形成。未見多核巨細胞反應及典型的增生性結節形成。對照組兔組織學檢查,顯示骨小梁結構正常,其周圍有少量炎性細胞浸潤,無死骨及類上皮細胞改變。
五、布魯桿菌培養
實驗組的10只大白兔肉芽組織勻漿在自制羅氏培養基上培養,10份標本連續培養6周,未見布魯桿菌生長。

圖1 CT三維重建未見實驗兔椎體出現明顯破壞,主要為椎間隙變窄 圖2~4 實驗組大白兔行MRI檢查,對兔椎體及周圍軟組織、膿腫、脊髓等顯示清晰,T2WI示椎體上端及椎旁呈混雜高信號 圖5,6 實驗組大白兔行MRI檢查,表現為椎體上端及椎旁略低信號改變;T2WI示椎體上端、椎旁呈混雜高信號,椎間盤可見信號異常
討 論
新西蘭大白兔對結核分枝桿菌敏感,常用于結核感染模型的研究。因新西蘭大白兔脊椎便于造模手術時的細菌植入,以及其后續實驗的清創、植骨等操作均簡便易行,且脊柱結核與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在診斷上較難鑒別,故本研究選擇新西蘭大白兔作為實驗動物。本研究中,實驗大白兔術后4周即發現椎旁軟組織有腫脹及膿腫形成。8周大白兔存活率實驗組為75.0%(12/16)、對照組為87.5%(14/16)、空白組為100.0%(16/16)。實驗組術后4周X線攝影及CT三維重建檢查陽性者5只,MRI陽性者7只;術后8周X線攝影及CT三維重建陽性者8只,MRI陽性者10只。術后8周,組織病理學顯示椎旁軟組織均有病變組織細胞增生及以淋巴細胞為主的炎性細胞浸潤。因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臨床上須綜合診斷進行確診,筆者在診斷人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時多采用Tekk?k的診斷標準,即結合影像學、病理學、細菌培養基實驗室檢查結果進行診斷。在人體,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主要表現以全身中毒癥狀好轉后,在脊柱局部形成以自身免疫性反應為主,因炎性反應造成椎間盤壞死、椎體不穩而造成局部的劇烈疼痛。在實際臨床工作中,布魯桿菌的培養陽性率極低,本研究建立動物模型以研究局部炎性反應及病變為重點,在診斷上以病理診斷為主。因此,結合影像學及病理學檢查結果說明造模是成功的,可為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做進一步的藥物試驗、疫苗研究、手術方法、植骨材料等的研究提供理想的實驗模型。
一、構建兔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模型的關鍵
1.選用標準的M5羊種布魯桿菌弱毒苗及適當的菌量:羊種布魯桿菌即馬耳他布魯菌,有很強的毒性及傳染性,故選用羊種布魯桿菌做動物實驗須在生物安全防護三級實驗室(簡稱“P3實驗室”)中進行,但因本次實驗須在實驗周期中對實驗對象進行影像學檢查,出于安全方面的考慮且遵守實驗室安全制度,故采用M5羊種布魯桿菌弱毒苗為實驗所用菌株。M5羊種布魯桿菌弱毒苗是一種具有較高侵襲性和傳染性的毒株,本研究選用此菌株作為實驗用菌,毒力適中,較野生菌可更好地控制菌量,可利用其較好地復制布魯桿菌病動物模型。本實驗組骨孔內浸注0.1 ml的M5羊種布魯桿菌弱毒苗,浸注菌量適中,實驗中無皮膚竇道形成。
2.選擇恰當的種植部位:解剖發現成年新西蘭大白兔腰椎椎體細長,上、下端粗大,最長矢狀徑與冠狀徑分別約為8 mm和10 mm。由兩端向中間逐漸縮窄且不規則,中間部分厚度約2 mm左右,均為皮質骨,中間為椎管,與人體不同,兔的下腰椎椎管內仍為脊髓[7]。因此,可行鉆孔種植布魯桿菌的部位僅為上下兩端終板,終板邊緣距椎間盤不超過5 mm,因此控制鉆孔深度在5 mm以內,在該部位種植布魯桿菌既符合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形成的原理,也是造模椎體體積最大的部位。
3.細菌植入方法得當:如何更好地植入細菌,目前尚無理想的方法。細菌植入方法主要有兩種:局部鉆孔與局部注射。本研究采用椎體局部鉆孔、明膠海綿填塞、石蠟封閉骨孔,布魯桿菌混懸液浸潤在明膠海綿內,可減少或避免細菌隨出血向外溢出。
二、兔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模型的影像學特點
影像學檢查是觀測兔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模型成功與否的重要方法。與脊柱結核造成的椎體骨質破壞、椎間盤信號異常及膿腫形成甚至后凸畸形不同,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主要表現為椎間隙破壞,極少見椎骨骨質的破壞,可有膿腫形成[16]。與人類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相似,本研究中術后8周行X線攝影及CT三維重建復查時實驗兔椎間隙狹窄的發生率為50%。實驗兔L5~6椎間隙模糊、變窄[17]。MRI可在人類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病變的早期發現病灶、確定病變確切范圍,較其他任何影像學檢查技術均敏感[18]。與人類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表現相似,MRI能夠早期發現實驗兔造模椎體上端、前緣炎癥變化及椎間盤破壞信號[19]。但由于兔的椎體細小、且椎體皮質骨炎癥反應輕,表現為等信號或稍低信號,加之周圍軟組織信號干擾,故MRI對早期病變椎體進行分辨較困難,但對鄰近椎間盤破壞信號表現異常的顯示較清晰。
三、兔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模型的組織病理學特征及病原學檢查
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局部病理變化與其他部位的布魯桿菌病病變相似,其病理變化與細菌的數量、毒力及機體的免疫力有關。本研究實驗兔組織標本病理檢查,可見病變區椎旁軟組織均有病變組織細胞增生及以淋巴細胞為主的炎性細胞浸潤,未見到多核巨細胞反應和典型增生性結節,這可能與病程時間短、破壞較輕有關。布魯桿菌培養是診斷兔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的“金標準”[20]。但由于受改良羅氏培養基培養的陽性率低、時間久所限,不能完全準確判定。
四、本研究的不足之處
本研究未進行多批次不同菌株量注入的對比研究,對菌株量的控制尚存在不足;本研究未進行血清滴度試驗。
本研究通過在新西蘭大白兔的椎體種植M5羊種布魯桿菌弱毒苗標準菌株,結合X線攝影、CT重建、MRI、組織病理學、細菌學培養等綜合檢查,結果說明成功建立了與人類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病理變化相似的兔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模型。該動物模型具有造模方法簡單、菌株量注入易控制、重復性強、同組實驗動物病變的個體差異小、病變較一致等優點。但是,由于布魯桿菌毒力、菌量,以及感染動物的免疫力、實驗室條件限制,建立更加標準的布魯桿菌病性脊柱炎模型,提高建模成功率,保證生物安全性,尚需做更進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