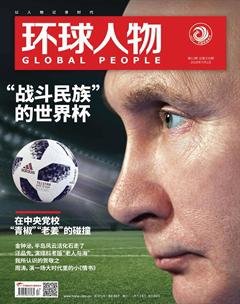特龍三次改變世界的“X教授”
尹潔
在科技創投界,幾乎每個月都有新技術問世,每個創業者都滿懷雄心壯志,覺得自己的項目天下無敵。然而能成大器者九牛一毛,尤其是一些天天喊著“改變世界”的人,往往連自己都改變不了。
大家不妨向美國“科技教父”塞巴斯蒂安·特龍請教一下,這位創業大家從不空喊口號,卻總是說到做到。即使你從未聽說過他,也在某種程度上受過他的影響,比如你正在使用的智能地圖、在線課程,將會用上的無人汽車等,都源于他的創業。現在,特龍正忙著測試他的新產品——無人駕駛飛行出租車,簡稱“飛的”。
從“斯坦利”到“X實驗室”
特龍是德國人,1995年獲得波恩大學計算機博士學位,之后進入美國卡耐基梅隆大學,成為一名計算機科學家。他專注于人工智能,尤其是機器人定位領域,研發過不少應用產品:華盛頓的一家博物館安裝了他的引導系統,可以在游客高峰期規劃不同的參觀線路;匹茲堡的一家療養院引進了他的智能機器人,可以為老人們提供多項服務;一些企業還將他的機器人用于礦山測繪。
2003年,特龍跳槽到斯坦福大學,出任人工智能實驗室主任,代表作就是著名的無人駕駛汽車“斯坦利”。他組建了一支由教師和學生組成的創業團隊,在2005年美國國防部舉辦的第二屆無人車大賽中,與一批世界頂級團隊展開了較量。
那次比賽是在沙漠里進行的,看誰能用最短的時間回到出發地,但在之前的大賽中沒有一輛汽車能開回來。“斯坦利”非常爭氣,在沙漠里跑了212公里,是第一輛成功穿越整個沙漠回到起點的無人車,特龍團隊因此贏得了200萬美元獎金。由于這件事在科技界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斯坦利”現在被陳列在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博物館里。
不過,再牛的技術,從實驗室到消費者的距離都隔著十萬八千里。不少偉大的發明創造,因為成本過高、政策限制等因素,幾乎與商業化無緣。特龍不希望自己的科技成果只限于200萬美元的變現,他選擇了一個更市場化的合作伙伴——谷歌。
從2007年開始,特龍以兼職的方式加盟谷歌,領導開發了街景地圖。他和谷歌的兩位創始人拉里·佩奇、謝爾蓋·布林非常投緣,經常在一起進行頭腦風暴,聊出不少天馬行空的構想,催生了著名的X實驗室。這是谷歌最神秘的部門,只研究那些超乎想象的前沿科技。作為實驗室負責人,特龍要求產品至少領先人類認知水平10年以上。
2011年,谷歌給了特龍團隊1.5億美元,專門研發民用型無人車。為了全身心投入,特龍放棄了斯坦福大學終身教授的職位。現在,這款產品已經測試多年,在實際道路上行駛了48萬公里。
特龍團隊的另一項成果是風靡一時的谷歌眼鏡,它具備智能手機的功能,可以聲控拍照、上網、發電子郵件。特龍希望谷歌眼鏡能商業化生產,像蘋果手機一樣普及,但由于價格、隱私問題等原因沒能實現。然而這種超前的設計和對未來的思考,依然帶給人們無數啟發。
“寓教于練比寓教于聽更重要”
X實驗室雖然充滿奇思妙想,但過于超前,離特龍的產業化目標還有很遠的距離。2012年初,特龍辭去了谷歌副總裁職務,開始專注于一個全新的項目——在線教育。
“我在斯坦福上課時,課堂里只能容納200多名學生,為了讓更多人分享,我嘗試把教學課程免費放到網上。”特龍說。這個網絡平臺就是優達學城,一個“菜鳥培訓站”,對學生背景沒有任何要求,只要注冊就可以在線觀看教學視頻、參加考試、拿學分。特龍驚訝地發現,他講授的無人車設計課吸引了來自不同國家的16萬名學生,其中年齡最小的10歲,最大的70歲,而考試成績前400名的學生中,沒有一名來自斯坦福。
特龍敏銳地意識到,在線教育時代已經到來。在得知一名9歲的印度女孩通過優達學完了整套電腦基礎技術后,他將免費課程增加到60門。
隨著優達的成功,類似的教學網絡不斷涌現,但跟風者大多套用了大學課堂的做法:教材深奧、課程繁多、作業和考試沒完沒了。但很多網絡學生白天要工作,學習進度難以統一。于是特龍堅持“短平快”的風格,每個教學視頻都短小精悍,一個知識點講完,馬上進行測試;不設教學進度表,學員不必按時上課和交作業;課堂是互動的,教師講完后學員馬上提問,有針對性地解決問題。用特龍的話說,“寓教于練比寓教于聽更重要”。
隨著注冊學員超過75萬,特龍開始思考如何盈利。他首先推出了職業發展服務,與谷歌、臉譜等公司合作,定向培養系統開發員、數據分析師等人才,學員畢業后可與招聘公司對接。此外,特龍還通過大數據對學員的擅長領域進行分析,并推薦合適的公司,每介紹成一位,相關公司就會付給優達一定的費用。特龍還設立了“納米學位”,寓意小巧靈活而作用巨大。它的課程主要教授實用性工作技能,采用在線集訓的方式,時間短、見效快。學員付費完成課程后可獲得“納米學位”證書,硅谷的不少公司對這個證書很認可。
優達已躋身獨角獸行列,目前市場估值超過11億美元,平臺上的免費課程用戶超過400萬人。
視佩奇為“重要導師”
從去年10月開始,一種外形奇特的飛行器不斷在新西蘭南島上空來來去去。它的體積介于無人機和小型飛機之間,兩個翅膀上裝著若干螺旋槳,可以像直升機一樣垂直起降,升空后再像普通飛機一樣行進。這就是特龍新公司“雛鷹”的核心產品“飛的”,即無人駕駛飛行出租車,其背后投資人是拉里·佩奇。此前他們對這個項目一直保密,現在終于進入了測試階段。特龍和佩奇希望搶在同行之前,在3年內建立一個無人駕駛飛行出租車的商用網絡。與新西蘭政府的合作讓這個計劃的速度加快了很多,幾年前即使是最樂觀的人也認為這項技術的應用至少需要10年時間。
除了商業價值外,保護環境是特龍研發“飛的”的主要目的。由于采用純電動力,“飛的”不會產生任何碳排放,也不占用地面交通資源,對人類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具有積極意義。
特龍毫不諱言,自己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佩奇的影響。“他總是在考慮未來會發生什么,人類20年、30年、60年以后是什么樣子。他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位導師,我從他那里學到的東西就是要不斷地思考未來。”
在佩奇的影響下,特龍致力于解決最難的問題,因此過程總是漫長而曲折。他曾在演講中提到,科技公司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不斷試錯,然后修正,即“建造—打破—改進”的循環。
制造“斯坦利”時,特龍經歷了多次失敗,很多想法進行到一半才發現是死路一條。他回憶,第一個實驗品出來后,剛開上路就掉溝里了,后來同樣的事情又發生了許多次,但每一次翻車后都會進步一點,在不斷的升級中,產品日趨完善。
帶著德國式內斂的特龍,既不以賺錢為第一追求,也不包裝和吹噓自己。他經常從大眾視野中消失,幾年后帶著驚世駭俗的新產品出現。有人說特龍至少3次改變了世界,享受其成果的人卻極少知道他的名字,正如媒體評論的那樣:“特龍讓我們相信,有人的確是努力在讓世界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