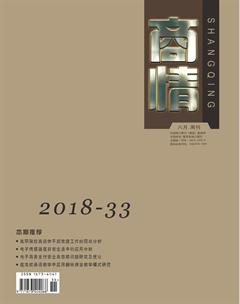地方立法權主體擴容的風性控制
劉宇喆
2015年新修訂的《立法法》一經頒布,就猶如一石激浪,引法學界眾學者競相關注。“全面賦予設區市以地方立法權”無疑是本次立法法修改的核心內容,一方面,新立法法以“設區的市”代替原有“較大的市”概念,并作廣義解釋,擴張地方立法權主體,由原有49個市擴大到284個設區的市。另一方面,為了維護法律統一,避免立法沖突,中央在擴張立法主體的同時,縮限了設區的市立法范圍,只可對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
一、地方立法權的進一步擴容需求
在2015年《立法法》修改前,設區的市立法需求早已成為其經濟進一步發展亟待解決的問題,立法需求因何而來?社會背景和現實是什么?厘清這些問題,是討論地方立法權進一步發展的前提。
1.經濟發展的需要
社會的經濟發展狀況直接影響對法律的需求,當初設立的較大的市無一不是經濟重點發展的地區。除了各省經濟最發達的省會城市,國務院批準的18個較大市其社會背景無一不與經濟發展的迫切需要相適應,比如深圳、珠海、廈門等,都是作為對外開放的窗口城市。
而今,經濟發展水平已經與當初大不相同了,我國經濟步入全面發展時期,市場經濟進一步深化,而單純依靠不平等的行政命令是不適合市場經濟體制的。大量城市只能要求要求省級政府立法,但省級政府的立法總量有限,最終導致的只能是市級政府依靠大量的“紅頭文件”進行社會治理,而“紅頭文件”,無論是上級政府的監督,還是頒布的程序,和地方性法規相比,都具有隨意性、主觀性和變動性大的問題,這無疑對未來的法治建設具有不良影響。
因此,開放設區市的地方立法權限是必由之路。一方面,地方政府已經形成“上有政策,下有紅頭文件”的對策之法,大量的行政命令已經在代替法律治理社會,另一方面,開放設區市的地方立法權,對中央監督立法、維護我國法制統一、促進地區公平等,都具有重要作用。
2.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需要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作為十八屆四中全會后我國首要的任務,其重點更是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鑒于中國原有立法體制存在缺陷,即主要存在于地方立法權授予標準不統一,地方立法資源配置不平衡等問題。“明確地方立法權,依法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就成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主要需要。
《立法法》修改前,地方立法資源配備極不平衡。在全國僅有省會城市和較大市擁有地方立法權,總共49個,而其他235個設區的市都不享有地方立法權。而且,對比這些城市發現,國務院批準較大市的標準也無法預測。僅從經濟指標來看,經過中國近年來經濟快速發展,一些非較大市的經濟規模、人口等綜合實力都超過了一些較大市,而這些更為發達的地區卻不能被批準為較大市,事實上,在1994年之后,地方立法權的下放處于暫停,在這二十多年之中,經濟的改革與發展和法律的缺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我國是一個單一制國家,維護法律統一尤為重要,但我國同樣土地遼闊,自然環境、社會習俗、經濟發展程度差異較大,單一的普遍性的國家法律無法解決各自地區的差異問題,但是各個地區為了維護社會治安、經濟秩序,必然存在特殊的立法需求。而之前“較大市”的立法模式是可以解決地區的差異性問題的,但限于下放范圍太小,社會迫切需要中央進行改革。
理論上講,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特殊的立法需求,但如果盲目下放立法權,則可能造成法律秩序混亂,得不償失,因此,我國在下放全國284個設區的市擁有地方立法權的同時,考慮到地方立法能力的差異,與中央監督力度有限等原因,縮限了其立法范圍。當然,從長遠的角度看,進一步擴容地方立法權限,是必然趨勢。甚至,在將來把立法權下放至縣級也不是沒有可能。
但是,我國作為單一制國家,維護法制統一與法制安全是頭等重要的事情,如此大規模的擴容地方立法權主體,實乃罕見。與擴容立法權主體帶來的諸多價值與效應相比,地方立法權主體擴容的風性同樣值得我們關注。
二、地方立法主體擴容風性控制需解決的矛盾:
首先,就是立法權的賦予與立法素質之間的矛盾。在立法法修改之前,享有地方立法權的49個城市無疑都具有一個共同點,即經濟與文化在特定地域范圍內相對發達。所以這些城市的法制機構相對健全,政府立法素質較高。立法主體擴容后,設區的市普遍獲得了地方立法權,但由于部分城市經濟欠發達,缺少立法經驗、立法人員,甚至缺少諸如法制委員會等立法機構,導致立法能力不足。從而造成了其享有的地方立法權與其并不具備相應立法素質這一矛盾。
在此種情況下,可能會導致如下有悖于地方立法權主體擴容之目的與初衷的情形。第一,被賦權的設區市由于立法能力受限,消極立法。第二,地方立法簡單重復上位法或者抄襲其他地方立法,造成立法資源浪費,地方立法靈活度和針對性喪失,違背地方立法權主體擴容之初衷,甚至引起立法亂象。第三,由于采取審批生效的制度,會造成省級人大常委會法制機構的工作量大增,審查地方性法規人員不足的問題。
其次,立法權的濫用與法制統一的矛盾。我國作為單一制國家,維護法制統一是最基本的憲法原則。但高度的統一必然造成地方靈活性與創造性的缺失,后兩者正是我國社會現階段發展經濟與優化政府管理的內在需求。而地方質量不高的立法活動勢必會對我國法制統一造成威脅。具體有二,第一是下位法與上位法之間的沖突,第二則是設區市級地方性法規之間的沖突,而前者對法制統一有著更大的影響。地方立法引起的法制統一問題在地方立法主體擴容之前就已不是新鮮事。而在擴容之后,這一威脅無疑擴大了無數倍。雖然我國立法法修改時意識到了上述風性的存在,制定了審批制度以及備案審查制度,但諸如此類制度的人為性較高,不能以制度和法定程序的方式對違規的地方性法規予以改變和撤銷。新《立法法》規定地方與上級人大常委會,在可能存在違反上位法的情形時,只有在經過反復的溝通、協商和反饋之后,制定機關仍然不予以修改的,才有可能啟動“撤銷”這一具有較強威懾性的外在監督機制。結合我國現實情況,強制啟動“撤銷”機制的可能性不大,造成這一制度基本處于“休眠狀態”,其制度設計的根本目的無法實現。因此,全面賦予設區市以地方立法權,立法素質較弱的城市有意或無意對立法權的濫用,會對我國法制統一造成很大困擾。
第三,立法權限收與放的矛盾。根據新《立法法》規定,對于原有49個享有地方立法權的城市與235個被新賦予地方立法權的城市來說,我們可以推導出一對矛盾;即對于原49個市,其立法權限受到限縮,與其他235個城市地方立法獲得授權的矛盾。原49個市的地方性法規只要避免法律保留的范圍,且不與上位法沖突即可,但新《立法法》頒布后,全部的設區市,包括原49市的立法權限都只能對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制定地方性法規,此種舉措的初衷不難推測,即在地方立法主體大范圍擴容的同時,限縮立法權限,把立法權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防止立法權的濫用。但全面限縮地方立法范圍會對地方政府社會管控造成困擾,尤其是原49個市以及經濟相對發達的城市來說,其立法需求遠遠不滿足于上述法定事項,《立法法》的修改在很大程度上不盡無法滿足發達城市對地方立法權的需求,相反還使得原已享有地方立法權的城市的地方立法權之權限范圍受到限制,這一不恰當的限制恐有因噎廢食之嫌。
針對上述問題,作者提供以下思路以供借鑒。
各種矛盾的解決,在于控制立法權收與放之間,權衡地方立法素質與改革目的問的矛盾。誠如上述,此次《立法法》的修改以擴充地方立法主體為核心內容,雖良處頗多,但同樣存在很多風性,究其原因就是中央未能權衡好地方立法權收與放的平衡。“一放就怕,一怕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又放,放收并序”用這種態度對待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不僅無法管理好中央與地方的關系,也無法進一步提高我國政府的治理水平。于地方立法權主體的擴容這一層面而言,中央對于控制主體擴容所導致的風性的防范和控制,重點在于實現地方立法權的收放平衡。
收權:是否平衡了與地方城市立法需求。
此次《立法法》的修改,收權的舉措有兩個方面。即賦予了235個設區市以有限的地方立法權,與限縮了原49個城市本身享有的地方立法權以城鄉建設與管理、環境保護、歷史文化保護等方面的事項為限。雖然《立法法》規定,在此次立法法修改之前已經訂立的地方性法規,即便涉及上述規定范圍之外,也繼續有效。但是這次《立法法》的修改,對于此類城市無疑是使其已經相對旺盛的立法需求受到抑制,而且根據立法法規定,對于那些已經制定但需要修改或者廢止的地方性法規,由于其喪失了法定范圍之外的立法權,當然也喪失了修改和廢止的權力,于這兩個層面而言,這次立法法的修改無疑是與之前已經擁有地方立法權城市,立法需求進一步發展的大趨勢所背道而馳的。
其次,對于那些新獲得地方立法權的城市而言,此次地方立法主體擴容的舉措顯然在某種意義上滿足了其立法需求,然而在現實中,對于立法范圍的種種限制,也無法全面滿足這些城市的立法需求。但立法范圍事關我國法制安全與法律統一,不可簡單而論。總之,這次《立法法》的修改,其收權的措施,抑制了原49個已經擁有地方立法權的城市立法需求,部分滿足了新獲得地方立法權城市的立法需求。
放權:須結合地方立法素質與監督體系。
地方立法主體擴容乃是順應社會潮流的一項正確舉措,其包含的社會治理、民主價值都可以提現擴容立法主體的正當性。但是,怎樣落實中央的舉措才是重中之重,否則,放權行為的風性過高,無法得到落實,反而會拖后和擾亂我國法律體系。在放權的考量上,我們主要需結合地方立法素質與監督體系結合考量。
放權應該考慮城市的立法素質,采用循序漸進的放權模式。我國《立法法》第七十二條第四款規定:除省、自治區的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經濟特區所在地的市和國務院已經批準的較大的市以外,其他設區的市開始制定地方性法規的具體步驟和時間,由省、自治區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綜合考慮本省、自治區所轄的設區的市的人口數量、地域面積、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以及立法需求、立法能力等因素確定,并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和國務院備案。這項規定雖考慮到了循序漸進的放權模式,但是由于其規定的條件存在模糊或過于抽象,在實踐中難以完全避免放權過于松懈的情況。
最后,監督體系的建立與完善。前文所言,雖然立法者考慮到了這一點,并且制定了相應的規定,采用事前批準與事后備案審查的方式,但結合我國具體實踐,在當下政府強勢,地方人大的意見容易受政府左右的狀況時,我們難以對人大的批準權以及備案審查抱有較大期望。
結語:此次地方立法權主體的擴容,緩解了地方政府的立法需求,優化了政府社會治理能力,使以前“摸著石頭過河”的改革方式于法有據。因此地方立法主體擴容是一項重要且必要的立法改革。但是,經過風性的評估,地方立法權的行使過程中仍存在許多弊端,我們有必要針對并加以有效的控制。否則,地方立法權主體的擴容非但達不到立法目的與預期,甚至有可能造成諸如法制統一性等更加嚴重的后果。所以,探究地方立法權主體擴容的風性防范與控制,無疑是需要我們認真對待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