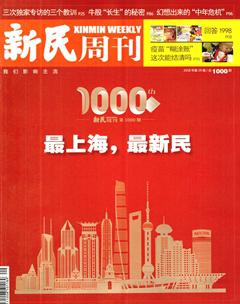疫苗,該怎樣才能管好?
應琛

1986年,美國政府出臺了《國家兒童疫苗傷害法案》,為疫苗受害者獲得救濟確立了法律依據。1988年,美國國會通過并實施《疫苗傷害賠償程序》,該程序是為解決疫苗傷害索賠而特定的無過錯責任體系。
疫苗作為特殊藥品,實行最嚴格監管,整體安全性高于治療性藥品,而中國疫苗監管體系在2011和2014年都通過了世界衛生組織(WHO)的評估,這意味著中國疫苗監管體系達到國際標準。前國家食藥監局藥化監督司司長李國慶曾對媒體表示:“我國疫苗監管體系總體水平,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
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國際先進水平的監管體系還頻出事故呢?
監管存在查缺補漏的空間
造成疫苗接種異常的原因也各有不同,包括不良反應、疫苗質量事故、接種事故、偶合癥和心因性反應這五種類型。即便完全合格的疫苗,也存在造成接種對象死亡或者后遺癥的可能性。按照中國疾控中心公布的數據,出現這類疫苗不良反應概率是百萬分之一到百萬分二。這是全世界都無法避免的問題,日本將其稱為“惡魔抽簽”。
“惡魔抽簽”雖無法避免,但有效的監管卻是保證“不出人禍”的關鍵。
在WHO評估指標中,所有內容圍繞著監管體系是否規范,能否保障疫苗產品的安全、有效。
在中國,疫苗監管法規其實還是很健全的。監管單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實施條例》、《藥品生產監督管理辦法》、《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認證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對疫苗生產流通的各個環節進行監督管理。
全同現有3478個疾控中心,依法監督指導20多萬家疫苗接種單位。2016年3月24日,山東“非法經營疫苗案”發布會上,時任國家衛計委疾病預防與控制局局長于竟進曾表示:“疫苗的生產、流通企業直接向接種點供應疫苗,點多面廣,同時各個地方發展又不平衡,監管的難度就比較大。”
中國現有45家疫苗生產企業,可生產63種疫苗,預防34種傳染病,年產超過10億針劑。截至2018年初,中國有4個疫苗得到WHO的預認證,得到預認證是國產疫苗走向國際市場的前提。
在生產環節,約束疫苗廠家最核心的是《藥品生產質量管理規范》(GMP),這套規范是用于制藥等行業的強制性標準,目的是及時主動防范質量事故,以最大限度保證上市藥品質量,保證公眾用藥安全。簡言之,藥品企業只有按照GMP的要求,在質量管理、人員配備、設備、物料、產品發運召回、自檢等多個方面達到要求、通過審核后,才能獲得“GMP證書”,投入疫苗生產。
另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藥品必須按照同家藥品標準和國務院藥品監督管理部門批準的生產工藝進行生產,生產記錄必須完整準確。長春長生公司編造生產記錄和產品檢驗記錄,隨意變更工藝參數和設備,這一行為明顯違反管理法,對應疫苗的藥品GMP證書被收回。
由于藥監部門的日常檢查難免滯后,疫苗上市之前還有一道重要審批“批簽發”。批簽發是WHO要求的同家疫苗監管六項職能之一,由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院負責,即確定疫苗的安全性和確定疫苗的有效性。
按照《生物制品批簽發管理辦法》,我國對既往因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被責令停產后經批準恢復生產的生物制品,會按照注冊標準進行全部項目檢驗,至少連續生產的三批產品批簽發合格后,方可進行部分項目檢驗。
中檢院年報顯示,近年疫苗批簽發不合格率較低,歷年不合格率均低于0.5%。去年10月長春長生公司的百白破疫苗問題,就是中檢院抽檢中發現的。
在流通環節,疫苗問題主要有兩個方面:儲存運輸和批發銷售。疫苗是特殊生物制品,我國對儲存運輸過程中使用的設備和保存方式都做了專門規定,比如溫度、冰箱種類、溫度計擺放位置等。
2016年,山東非法經營疫苗案中,總價值5.7億元的疫苗正是由于沒有經過嚴格的冰柜儲存和運輸而發生變質。非法經營者繞過正常流通體系進行違法銷售,經過多年才被發現。
這起案件也暴露出疫苗流通的潛規則:南于每個環節都有利可圖,上下游形成產業利益鏈集團。疫苗分銷商進行疫苗跨地區降價銷售,疫苗批發商賣疫苗給沒有經營資質的下線,接種單位不設防私自購入失效疫苗。南此可見,疫苗流通環節的監管短板還有待補齊。
至于接種環節,中國早在2005年就已建立接種疫苗后不良反應監測系統,疫苗接種后出現的懷疑與預防接種有關的不良反應均需要報告和監測。
如果問題疫苗已經上市,快速查出疫苗的流向就顯得至關重要。中國曾在2006年對疫苗等特殊藥物實行電子監管,通過在疫苗外包裝盒上賦碼,試圖將疫苗生產、經銷、使用企業、單位各級掃描電子監管碼錄入流通信息,對疫苗流通過程進行監管,以便在出現問題時第一時間追溯流向,盡快回收,減少危害。
但實際操作中卻存在諸多問題,藥品電子監管碼與疾控機構自建的信息網絡不兼容,不同地區預防接種信息不相同,還可能遇到個別疾控機構的“阻攔”。單環節職權與全鏈條監控存在沖突。
今年7月12日,上海市衛生計生委透露,上海已建成市疫苗和預防接種綜合管理信息系統,在全國率先實現基于信息系統覆蓋第一類疫苗和第二類疫苗的采購、供應、倉儲、物流和接種等的全環節、全過程、可追溯綜合管理。
除了依據《疫苗流通和預防接種管理條例》的規定進行補償之外,我同目前也已開始嘗試建立補償體系。2016年,國家衛計委等4部委下發通知開展補償保險試點,廣東、江蘇等納入試點范圍的地區已陸續制定方案并實施。補償體系還處在初始階段,距離成熟完善的補償機制還有一段距離,未來還需要更多的摸索與嘗試。
美國,走過彎路后
就算在疫苗監管最嚴格的美國,也曾發生過疫苗安全事故。1955年加州伯克利的卡特制藥廠在制作脊灰疫苗時沒有殺死所有的病毒,導致12萬接種該疫苗的兒童中有4萬兒童染病,最終113人終身癱瘓,5人死亡。
法院判決認為,卡特制藥廠不存在刑事犯罪,“罪魁禍首”是負責疫苗監管的國家衛生研究院,理由是1954年已有研究報告了一些猴子接種這種疫苗后癱瘓,但國家衛生研究院生物控制實驗室主管威廉·錫布雷爾對此視而不見。
隨后,包括錫布雷爾和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負責人奧維塔·霍比在內的一大批人丟了“官帽”。這起事件更深遠的影響則是促使美國建立起嚴格的疫苗監管體系。
1986年,美國政府出臺了《國家兒童疫苗傷害法案》,為疫苗受害者獲得救濟確立了法律依據。1988年,美國同會通過并實施《疫苗傷害賠償程序》,該程序是為解決疫苗傷害索賠而特定的無過錯責任體系。
在監督環節,美國設置了總協調機構——全國疫苗計劃辦公室。在生產環節,食品和藥物管理局設置了三道實驗門檻和兩道認證,一項疫苗要獲得許可需要經歷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在允許上市后,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和食品和藥物管理局還會對疫苗流通環節進行嚴格監管。
在60余年的時間里,美國政府為了恢復民眾對疫苗的信心,費盡心血。
除了美國,不少歐洲國家也都有著嚴格透明的疫苗監管機制。
愛爾蘭嚴格控制疫苗生產廠商資質,這些授權的疫苗生產商都是大型的、符合聯合國衛生部組織規定的生產商,生產商數量很少。愛爾蘭衛生部設有專門的疫苗資質審查、管理機構,要取得生產資質,必須通過嚴格考核,如研制能力、生產設備、資金等。
生產商是安全疫苗的第一步,那么供應渠道就是安全疫苗的另一保障。愛爾蘭疫苗在從經銷商到私人診所或醫院的運營過程中,都由愛爾蘭藥物委員會或歐洲藥品評價局發放許可,有在證明有效且安全后才允許使用。
愛爾蘭取得疫苗渠道嚴格,預定的過程中有官方監管。運營疫苗過程中,運營商必須填寫詳細信息,且全程透明化,保證能隨時取得聯系方式。
與美國一樣,由于疫苗對溫度敏感,愛爾蘭衛生管理局對疫苗的貯藏方面要求非常嚴格,一旦違反相關溫度控制,必須立即由衛生部緊急召回。
在英國,為了保障疫苗的安全性和穩定性,英國衛生部是英國疫苗唯一的合法賣家,其購買具有壟斷性,英同衛生部在與生產商的合作中占主導地位,雙方商定的合同價低于市場價。由于疫苗生產利潤微薄,許多企業望而卻步,這使得疫苗生產商越來越少,但疫苗的品種越來越多。即便如此,疫苗生產商的資質也被嚴格控制,生產商的研制能力、生產設備、資金等方面,都要經過英國衛生部的嚴格考核。
日本的“政府賠償”制度
和中國類似,日本的疫苗也包括“定期接種”和“自選接種”兩大類。根據相關法律,“定期接種”由各地方政府主導實施,民眾可免費接種(部分需要自己負擔)。“自選接種”即民眾可以根據自身需要追加的接種項目,費用為民眾各自承擔。
在疫苗接種和管理方面,口本也曾走過彎路,有過血的教訓。據日本厚生勞動省推測,日本有110萬至140萬人感染乙肝病毒,其中有近40萬人是因為人為過失導致感染的。由于管理不嚴和衛生條件有限,從1948年到1988年,數十萬的日本民眾用重復使用的針頭接受了預防接種。這導致大量民眾感染乙肝病毒,甚至死亡。
此外,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日本還發生過“流感疫苗副作用事件”。口本從1962年開始流感疫苗接種,到1971年為止發現至少有21人因接種流感疫苗死亡、16人留下后遺癥。
一系列事件使得同本的《預防接種法》多次被修正,并建立相關救濟制度。一旦發生疫苗事故,先明確“結果責任原則”,地方政府立即成立預防接種健康受害調查委員會,收集相關信息。如判定是疫苗本身存在問題導致事故,政府部門負擔受害者的醫療費、補助費:導致殘疾的,對未滿18歲的人員發放殘障兒養育年金,對18歲以上的人員發放殘障年金;造成死亡的,政府需要負擔喪葬費等。
日本還有疫苗監管制度,有專門的《藥事法》來監管疫苗生產廠家。日本厚生勞動省指定相關檢驗機構對疫苗的有效性、安全性進行嚴格檢查,任何一種疫苗都要經歷開發、審查、認可之后才能進入生產和接種階段。這些檢驗機構主要由政府主管的藥事食品衛生審議會、醫藥品醫療機器綜合機構、國立感染癥研究所等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