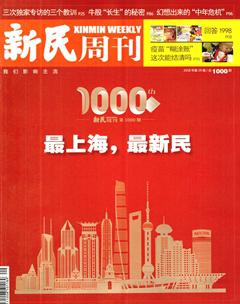路名的密碼
沈嘉祿
上次我在專欄文章里寫到了清末到上海來打拼的潮州人,有讀者很感興趣,希望我講講外成瓜街的來歷,因為今天的青年人都搞不明白這條馬路為何與醬瓜扯上了。
這是個不大不小的題目,我就長話短說了吧。假如你打開黃浦區的地圖,就會發現老城廂的路名相當“古老”。不少路名代表了種種業態,這是上海城邑自給自足內循環的寫照。
比如雞毛弄,過去是收購整理家禽羽毛并制作雞毛撣子的地方。面筋弄.自然是加工豆制品的了。蘆席街是編織蘆席的,引線弄就是縫衣針作坊與商店的集中場所。大東門外南北向的內篾竹街和外篾竹路,曾經有好幾個竹木器作坊,當然也是篾匠的炫技所在。花衣街形成很早,本埠商人在此開設棉花堆棧和棉花商行,每年秋末棉花采摘季節,由江南一帶車船載來的棉花出售給這里的商行,而后由廣東、福建客商來此收購棉花,一路南運。這條小路靠近十六鋪,也是鴉片戰爭之前洋人窺察風土民情與商業機密的窗口。
糖坊弄就在我家東北面,在南方的砂糖進入卜海之前,這里以熬制麥芽糖(學名叫飴糖)而得名。直到康熙年間海禁廢弛,福建泉州、漳州商人將大量蔗糖運進上海,飴糖生產才大幅萎縮最終被砂糖取代。硝皮弄,就是硝制皮毛的,想必當年這一帶污水橫流,臭氣沖天,蚊蠅群舞。進入民國后,硝皮弄成為洋廣衣業集中的地方,所謂“洋廣衣”,就是做西裝與時裝,當時有許多廣幫、奉幫裁縫在此同框競技。
還有一條悅來街。親們不要以為它是娛樂一條街,其實集中了一些專供沙船保養與維修的用品——比如桐油、苧麻和鐵釘的小街,而相當于今天的汽配一條街。鉤玉弄,并不是加工玉器的,最先是養狗殺狗的所存,“狗肉”兩字不大好聽,不知哪個紳士大筆一揮改成鉤玉弄,立時就雅馴多了。
還有一條豬作弄,明擺著足殺豬場所,后來又改為薩珠弄——“殺豬卉”的諧音。與豬作弄異曲同工的是火腿弄,曾經是集中制售咸肉火腿的地方。豆市街,以豆業“宋菽堂”所在以及豆市集中而得名,是上海豆、麥、米、食油批發交易中心,如果受臺風影響,從牛莊來的貨船在海上耽擱數天,豆米行情就會上漲。
最后就要說到成瓜街了。外咸瓜街,里咸成瓜街.足一對“雙胞胎”,它們均為南北向,平行相伴,南端罕復興東路,北端至東門路,以城墻為界分作一里一外,這是一兩百年前約定俗成的。
咸瓜,不少人塑文生義,認為也許是腌制、經銷醬瓜的地方。錯!這里曾是上海海產腌貨的集貿市場。話說清朝乾隆年間,福建泉州、漳州一帶的海船商人是最早進入上海的商人之一,后來還在小東門建造了泉漳會館,這個會館就存今天的白渡路以北,外咸瓜街與里咸瓜街之間。
那時,每年五月為東海大黃魚的汛期,漁民大量捕撈后,成為福建船商運抵十六鋪的主要物產之一。按照行業習慣,大黃魚捕撈后.漁民即在船艙內加冰塊進行冷凍處理,一部分也會撒上海鹽腌漬風干。福建人和寧波人都將冰鮮的海貨叫作“冰鮮”,將腌漬風干后的大黃魚叫作“咸瓜”。直至今天,寧波人還將黃魚叫作“黃瓜”,所以“咸瓜”一詞在這里就專指腌過的咸黃魚,亦即黃魚鲞!
靠著泉漳會館和市場的影響力,這兩條街就慢慢發展成為冰鮮海產品和腌鮮咸貨的集貿市場.兼及桐油與砂糖等。直到上世紀七十年代,外咸瓜街還是上海主要的海產品集貿市場。再后來,里咸瓜街開出了一些小規模的金銀飾品店,成為城隍廟金飾品市場的延伸。天津水果業公所、信業公所、藥業公所、參業公所、腌臘業公所等都建在這兩條街上。現在里咸瓜街已經消失,外咸瓜街還在,但一家腌咸魚店都找不到了,道路兩邊建起了金外灘花同、濱江名人苑等高檔樓盤,憑欄遠眺.風景獨好,只可惜煙火氣散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