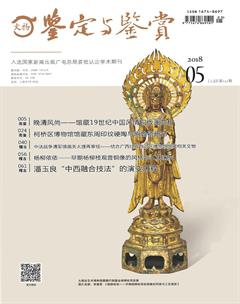楊柳依依
李慧君
摘 要:楊柳枝觀音是中國本土常見的觀音變相之一,以手持楊柳枝和凈瓶為基本標志。文章主要探討銅像形制的楊柳枝觀音立像的起源,及其自北朝誕生,隋代過渡成型,盛唐達到高潮,至晚唐走向衰滅各個階段在風格和鑄造工藝方面的演變歷程。
關鍵詞:楊柳枝觀音銅像;風格;工藝;演變
“凈瓶甘露年年盛,斜插垂楊歲歲青。”[1]《西游記》中白衣飄飄、手持楊柳枝、遍灑甘露的觀音形象深入人心,是當下中國人對觀世音菩薩最普遍的集體想象。而楊柳枝的意匠源頭為何?楊柳枝和凈瓶的組合模式的圖像志特征有何變化?最早的楊柳枝觀音出現于何時?早期銅像形制的楊柳枝觀音風格與制作工藝有怎樣的演化歷程?本文試圖對以上問題進行探討和闡釋。
1 楊柳枝與凈瓶
“楊柳觀音”一詞最早見于《千光眼觀自在菩薩秘密法經》,指代以持楊柳枝為特征的觀音[2]。楊柳枝的功用可見隋天臺智者大師《請觀音經疏》:“楊枝拂動以表慧,凈水澄渟以表定。楊枝,又二義:一拂除,即對上消義;二拂打,即對上伏義。”[3]此處楊枝的“拂除”“拂打”功用疑與后世持拂塵觀音的出現有關。
楊柳枝觀音以手持楊柳枝和凈瓶為典型標志。其中,凈瓶是佛教重要的法器之一,與觀音關系密切。在中國本土紀年造像中最早可見凈瓶的或為博興博物館收藏的北魏太和二年(478)落陵委造蓮花手觀音銅像。其后,又出現有兩手分持楊柳枝與凈瓶的觀音造型。千手觀音的重要法器之一也是凈瓶,唐宋后的水月觀音、白衣觀音等都伴隨有凈瓶出現。較之于凈瓶,楊柳枝的搭配模式相對單一,多與凈瓶組合出現。至于楊柳枝的源頭,學界一般觀點認為應與流行于印度次大陸地區的“齒木”(在漢譯佛經中被譯成“楊枝”,故楊柳枝觀音又稱楊枝觀音)有關。“齒木”經咀嚼有清除牙垢之效,被神話為佛教法器,如《華嚴經·凈行品》中“手執楊枝,當愿眾生,皆得妙法,究竟清靜”[4]。此說法正確與否仍需考證,但楊柳枝觀音在中土流傳地的盛行無疑與中國古典文化本身對楊柳這一意象的喜戀有關,如《詩經·采薇》中的名句:“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如此一來,楊柳枝從印度“嫁接”至中土文化土壤后,迅速形成了“柳成蔭”的盛況。至少在元代,柳樹已被佛化為“觀音柳”,如謝應芳《觀音柳》即云:“肉髻珠纓自在身,何緣化作柳中人。”[5]
在觀音造像中,楊柳枝常伴隨凈瓶成對出現。從圖像志角度而言,楊柳枝與凈瓶的搭配呈現如下幾種組合模式:雙手分執楊柳枝和凈瓶,多見于東魏至唐末觀音立像,而此圖式造像至唐末后鮮見。宋元以后,可見雙手或單手執插柳枝凈瓶造型,或是插柳枝凈瓶作為觀音題材作品背景。另也有楊柳枝單獨出現或與其他法器搭配的情況,甚至在宋代文人影響下楊柳枝變為竹枝的情況,在此不一一細述。
2 早期楊柳枝觀音銅像的風格演變
本文重點考察的是以銅像形制為代表,中國北朝至唐代最早一批楊柳枝觀音立像的風格演變。縱觀此間三四百年間的楊柳枝觀音銅像,除手持物和站姿外,可發現其整體上具有較強的共性,如形制較小,體量多在10~30厘米之間,由此可判斷此類銅像用途依然為家庭祭奉及隨身攜帶;多為光背、像身、底座組合的形式,且較之更早期的銅像,此三部分的結合已多改一體澆鑄為分體合鑄的形式等。而細看此時段的楊柳枝觀音銅像,亦可發現其自誕生、成型,至高潮、衰退,在特定的發展階段,同樣呈現出不同的時代特征。
2.1 初現:北朝
目前研究記錄最早的楊柳枝觀音像是東魏興和元年(539)的銅鎏金觀音像[6]。事實上,由于此件銅像收藏不明,可追溯的信息極為有限,且造像本身風格與工藝仍存在諸多可疑處,筆者更傾向于認為故宮博物院收藏的北齊天統二年(566)銅鎏金馬崇暉造觀音像為現今可查證最早的紀年楊柳枝觀音造像(圖1)。該銅像為舟形火焰紋背光,背光中陰刻有雙層項光和身光。觀音頭戴三葉冠,系寶繒,左手下垂提瓶,右手上舉一直立葉狀物,跣足立于圓形素臺上,下為四組方座。座上刻有發愿文。背光與像身目測為一體澆鑄。該銅像無論是整體風格還是雕刻制作手法,都依然沿用自北魏興起的蓮花手觀音銅像模式,拉長的舟形背光也與北齊前后施無畏印和與愿印的觀音銅像一脈相承。另可見,以楊柳枝觀音為代表的觀音造像至此都未擺脫“悉達多太子說”等印度宗教淵源的影響,依然以偏男性或至少是中性形象示人。類似造像可見芝加哥藝術學院收藏的銅鎏金楊柳枝觀音像(圖2)。
由于在印度本源地尚未找到同類可供參照的圖像典范,或可大膽推測,楊柳枝觀音形象的誕生也許是其時工匠在獲得“楊枝凈水”概念后,在現有觀音像基礎上拼接改造而成。遺憾的是,此類型觀音造像存世數量極少(可能隋代之前未廣泛流行),紀年為該時期的幾件銅像又被陸續判定為后代仿造,如首都博物館收藏的北周保定元年(561)銅鎏金楊柳枝觀音像[7]、東京藝術大學美術館收藏的陳太建元年(569)銅鎏金楊柳枝觀音像[8],無法為初期的楊柳枝觀音像提供更多源流方面的輔證。
2.2 過渡:隋—初唐
進入隋朝,兩代帝王一改周武帝滅佛政策,尊崇佛教,不僅在政治上一統南北兩朝,佛教也開始綜合南北體系,為進入唐代大成時期奠定了基礎。隋至初唐,隨著佛教進一步本土化,佛像也更多地融入了中華審美意趣。大英博物館收藏的開皇十五年(595)銅鎏金敬遠造楊柳枝觀音像、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隋仁壽元年(601)呂□斌造楊柳枝觀音銅像與唐武德六年(623)銅鎏金彌姐訓造楊柳枝觀音像(圖3~圖5)等具代表性且較為完整的紀年銅像,可大致勾勒出楊柳枝觀音銅像逐漸走向成熟的過程。
幾尊觀音銅像頭光上普遍刻有項光和火焰飾紋,項光內有蓮瓣狀光飾,此后的楊柳枝觀音像項光也多采用此圖式。像身不再筆直站立,而顯露出略微扭動狀。除圖3外,觀音左手握凈瓶,右手翻舉持楊柳枝,枝條自然下垂,上刻有柳葉紋路——這即已形成了后代楊柳枝觀音的范式。一般而言,佛教造像遵循一定的量度規范,如圖3所示的左右手手持物相反的情況在楊柳枝觀音造像中較為少見。觀音胸飾瓔珞,下身著裙,身披帔帛,垂于兩側,線條較顯僵硬。跣足立于素面或蓮花臺座上,下有四方或盒狀鏤空趺座。另外,自魏晉至隋,金銅佛像上隨刻發愿文與紀年已成慣例。但入唐以后,銘文則銳減幾近不見,圖5是入唐后罕見的具紀年和發愿文的銅像之一。
幾尊銅像的光背由前期的全身光背演變為桃形頭光。目測軀尊、光背、趺座等采用的仍是一體合鑄形式,但故宮博物院另藏有一件隋開皇三年(583)銅鎏金金常聰造楊柳枝觀音像(圖6),該像“軀尊與趺座合鑄為一體,光頭缺失”[9],可見其時已出現了光背分鑄的情況。類似情況可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收藏的隋代銅鎏金觀音立像(圖7)。同樣,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的銅鎏金觀音像像身與蓮座處即明顯采用分鑄后焊接的形式(圖8)。
由上觀之,隋至初唐期間的楊柳枝觀音像在繼承魏晉南北朝銅像基本形制的同時,卻又發生了較大變化。其中,最突出的變化即是光背由全體身光簡化為頭光,像身從背光中獨立出來,形體甚至四肢都開始得到體現。盡管還稍顯僵硬和粗壯,但確實能明顯感受到像身由直立開始有了曲線。同時,瓔珞和帔帛的裝飾也進一步改變了原先左右對稱的呆滯模式,促進了觀音由“中性”“無性”向“女性”的轉化。另外,這一時期的觀音開始有了個性化的面孔,或莊嚴肅穆,或慈眉善目,此時的工匠已注意銅像的表情刻畫。在制作工藝方面,盡管諸多銅像仍沿用之前一體合鑄形式,但也出現了頭光分鑄的情況,應為合鑄不再能滿足造像精細度要求,且焊接或插接工藝已出現的緣故。
2.3 鼎盛:盛唐(約650—820年)
盛唐伊始,中國社會進入高度繁盛且極富藝術氣氛的時代,佛教藝術也隨之進入全新階段。楊柳枝觀音銅像即在此時到達了全盛期。該時期的楊柳枝觀音銅像不僅存世數量較之以往時代更為龐大,銅像自身也普遍充滿了奕奕神采和浪漫氣息,是佛像藝術與其時中國信眾的情感和審美需求的進一步融合。經典造像可見分別有佛利爾美術館、故宮博物院、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收藏的四件唐代銅鎏金觀音銅像(圖9~圖12)。
不難發現,較之過渡期及之前的造像,盛唐時期的楊柳枝觀音銅像突出特點為飄逸與富麗,彰顯物華天寶的大唐氣象。由頭光看之,此階段的光背多采用鏤空形式,且紋飾多繁復精細,使得銅像一改之前笨拙凝重之感,而更顯輕盈和空靈。體態與帔帛的變化同樣如此:觀音的身軀腰肢細瘦,胸部微隆,肢體扭動呈S形,曲線優美,富有質感和彈性;肩臂與手等處的刻畫也細致入微,可感受到肌膚的柔軟豐腴;身飾項圈、瓔珞等物,尤其是帔帛與柳枝飄揚飛舞,更增婀娜嫵媚的女性氣質。為了進一步加強這種飄逸修長的感覺,像身與蓮座的連接處也被刻意拔高,因此存世作品中常見從細處斷裂的情況(圖12)。蓮座下連唐代常見的尖拱形四足座。
需特別說明的是,盡管目前學界普遍將“頭頂寶冠有化佛”作為觀音的辨別標志,事實上,只有凈土往生型觀音才有此獨特標記[10],中國早期觀音造像并不具備此“化佛”標識。圖10中的觀音像頭頂化佛,也說明唐代佛教宗派更加多元和民間化。
盛唐時期的楊柳枝觀音銅像另一特征為多采用各部分分鑄形式,如圖9~圖11均可明顯見蓮座與四方底座間焊接痕跡。故宮博物院藏有一件銅像底部特征可判斷出像身原應與遺失底座插合連接(圖13)。頭光背與像身更是普遍采用了分鑄后插接的形式,圖12的光背現即已與像身分離。哈佛藝術博物館、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收藏的銅像殘件背面也留有插合部件(圖14、圖15),前者底座還可見用于插接的孔洞。這也較充分說明了現存唐代佛教造像多見光背或底座缺失的情況,此類案例不勝枚舉。
2.4 晚唐的沒落與一批“簡約派”楊柳枝觀音銅像
由于缺乏明確紀年銅像的佐證,現無法確定楊柳枝觀音銅像經歷了盛唐的繁盛后,在大唐末期會有怎樣的演變。但不容置否的是,這一時期王朝的沒落加之唐武宗滅佛的劫難,連同楊柳枝觀音在內的家庭禮佛用小型銅制佛像至宋代已幾乎絕跡。楊柳枝觀音銅像在晚唐亂世的厄運已難以還原,但無非是巔峰處戛然而止,或由精至粗逐漸衰退兩種。如果是后者,筆者確實在大量銅像中發現有一類具大唐印象卻風格迥異的“另類”楊柳枝觀音銅像。黑龍江博物館即將其收藏的一件銅鎏金楊柳枝觀音像斷代為晚唐(圖16)[11],首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圖17、圖18)等海內外機構也收藏有多件此類銅像。
金申先生在一文中提及此類銅像的鑄造時間為公元700年左右[12],但未給予解釋。西雅圖藝術博物館藏有一件同類銅像(圖19),上有“上元二年王氏女敬造”(675)銘文。與早期銅像銘文相較即知,家庭供養祭拜用佛像多用于祈佑現世或來世,因而銘文中造像目的和發愿人姓名為核心信息,紀年次之。而此例刻寫年號卻并無造像愿目,顯然不符邏輯。且此類銅像中可見“某妻”“妻某”卻未有“某氏”的先例,由此可大致判斷該像為真品偽造仿古銘文。
該類銅像一改隋唐巧密工整面貌,取其神而忘其形,細部一律不作交代,頗具簡約和抽象風范。頭光有細長頂部,疑為盛唐時期一類背光頂部有化佛圖式(圖11)的簡化。由于精細度不高,光背、像身等部位多又回到了一體合鑄的形式。另外,此類銅像鍍金情況較為常見,似可排除民間簡化制作的可能。因此,筆者更傾向于推斷“簡約派”銅像為晚唐衰落期作品。
歷史深處,楊柳枝觀音銅像曾驚鴻一現。由于社會風尚和銅像自身功能轉變,造像復雜度提高造成刻字空間減小等原因,隋唐后銅像銘文數量銳減,鮮見紀年。加之屢見后世偽造銘文的現象(圖19),楊柳枝觀音銅像的斷代仍存在很大困難。但整體而言,從北朝至唐,此類造像大體上經歷了身光逐漸褪去,女性和蓬勃的生命跡象逐漸凸顯,愈加世俗化和個性化,同時也更加注重精細鑄造和寫實刻畫的風格流變。繼續理清脈絡仍有待更多比對資料的發現和更成熟的鑒定技術。
參考文獻
[1](明)吳承恩.西游記[M].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5.
[2]李小榮.楊柳觀音與觀音柳[J].閩江學院學報,2017(6):36.
[3](日)高楠順次郎,渡邊海旭.大正新修大藏經第39冊[M].臺灣: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4]馮賀軍.漢傳佛教中觀音圖像的演變與流傳[M]//故宮博物院.故宮觀音圖典,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
[5](元)謝應芳.龜巢稿[M].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6]金申.中國歷代紀年佛像圖典[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7]劉丞.宋代仿古風氣佛造像初探[J].收藏家,2016(6):80-82.
[8]金申.解析數尊南朝的疑似佛像[J].東南文化,2003(10):46.
[9]故宮博物院.故宮觀音圖典[M].北京:故宮出版社,2014.
[10]謝志斌.中土早期觀音造像風格流變及其文化內涵[D].西北大學,2014.
[11]龐學臣.黑龍江省博物館藏佛造像[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
[12]金申.談清末民初時真品而后刻偽款的佛像[J].收藏,2015(5):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