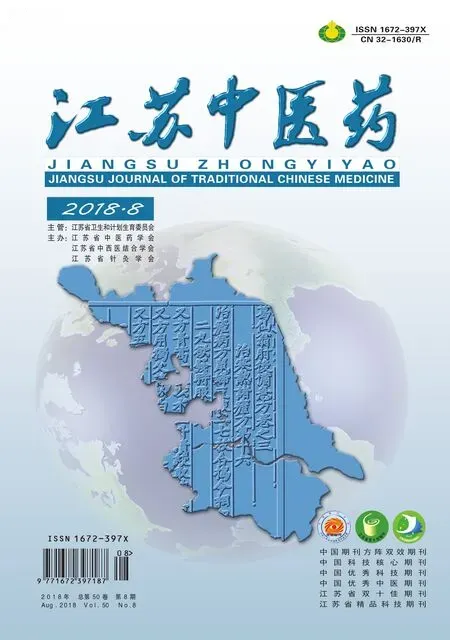慢性腎臟病3、4期伴骨質疏松中醫證型與骨代謝指標的相關性研究
——附90例臨床資料
孟憲杰 張 侃 時洪娟 王國軍 李容慶 陳桂芝
(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鹽城市中醫院,江蘇鹽城224001)
目前,礦物質和骨代謝紊亂(mineral and bone disorder,MBD)作為慢性腎臟病(CKD)患者常見的臨床并發癥,已經成為導致CKD患者生活質量下降、骨外鈣化及死亡率增加的重要原因[1]。研究表明,對于CKD3、4期患者來說,其并發CKD-MBD的臨床特征主要表現為骨質疏松(OP),包括骨痛、龜背、骨量減少、骨組織微細結構破壞以及骨脆性增加、骨折等[2-3]。中醫藥防治OP具有歷史悠久且療效顯著的優勢。但囿于中醫病因病機的復雜性,目前尚缺乏對其客觀指標量化的科學研究,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中醫辨證、用藥的準確性。近年來,隨著中醫證型診斷客觀化研究的興起,筆者認為,從CKD 3、4期伴骨質疏松的角度,探究其中醫證型與骨代謝指標的相關性,可以為CKD 3、4期伴骨質疏松患者中醫證型診斷的客觀化研究提供臨床依據,現報道如下。
1 臨床資料
1.1 一般資料 收集從2014年10月至2016年10月在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鹽城市中醫院腎病科住院的患者,共90例,其中男37例,女53例;合并有高血壓病62例,合并有糖尿病40例。根據中醫證型診斷標準分為:①腎陽虛證22例:男10例,女12例;平均年齡(58.73±6.24)歲;平均病程(3.95±1.17)年;合并高血壓病15例,合并糖尿病13例。②肝腎陰虛證18例:男8例,女10例;平均年齡(60.42±5.46)歲;平均病程(4.34±1.26)年;合并高血壓病14例,合并糖尿病7例。③脾腎陽虛證27例:男10例,女17例;平均年齡(60.34±5.18)歲;平均病程(4.06±1.03)年;合并高血壓病18例,合并糖尿病12例。④氣滯血瘀證23例:男9例,女14例;平均年齡(62.58±7.47)歲;平均病程(5.44±1.22)年;合并高血壓病15例,合并糖尿病8例。4組患者在性別、年齡、病程方面的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均具有可比性。
1.2 診斷標準
1.2.1 西醫診斷標準 CKD診斷及分期標準符合2002年美國國際腎臟基金會《改善腎臟病預后的初步行動(Kidney Diseases Outcome Quality Initiative,K/DOQI)》[4]有關CKD的定義及分期標準。其中,CKD 3、4期是指腎小球濾過率(GFR)在15~59mL/(min·1.73m2)。骨質疏松診斷參照2014版《中國人骨質疏松癥診斷標準專家共識(第三稿)》[5],T值≤-2.5可以診斷。
1.2.2 中醫證候診斷標準 同時參考《中西醫結合診治骨質疏松癥》[6]《中醫虛證辨證參考標準》[7]及《血瘀證診斷標準》[8]中相關條目,將CKD 3、4期伴骨質疏松患者進行辨證分型,分為腎陽虛證、肝腎陰虛證、脾腎陽虛證和氣滯血瘀證。
1.3 納入標準 ①符合CKD 3、4期診斷標準和骨質疏松診斷標準;②符合相應中醫證型診斷標準。
1.4 排除標準 ①合并有嚴重器質性消化、心血管、血液、內分泌、風濕免疫、腫瘤相關性疾病、活動性骨關節病等可導致繼發性骨質疏松的常見疾病;②因資料不全或不能配合的患者。
2 研究方法
2.1 觀察指標
2.1.1 一般指標 血鈣、血磷以及甲狀旁腺激素水平等。
2.1.2 骨密度測定 采用雙能X線骨密度測量儀,測定部位為腰椎(L1-4)和股骨頸。
2.1.3 骨代謝指標 采用酶聯免疫吸附法測定血清堿性磷酸酶(ALP)、抗酒石酸酸性磷酸酶-5b(TRACP-5b)水平;應用電化學發光免疫法測定I型膠原氨基端前肽(PINP)、β-Ⅰ型膠原羧基端肽(β-CTX)。所有檢測均由我院檢驗科完成。
2.2 統計學方法 所有數據均由SPSS 13.0統計軟件完成,計量資料以(±s)表示,采用ANOVA分析,多重比較采用LSD或SNK法,計數資料以頻數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為有顯著性差異。
3 研究結果
3.1 血生化指標比較 見表1。
表1 中醫證型組間血生化指標比較(±s)

表1 中醫證型組間血生化指標比較(±s)
注:與氣滯血瘀證組比較,*P<0.01。
組 別 例數 鈣(mmol/L) 磷(mmol/L) 甲狀旁腺激素(pg/mL)腎陽虛證 22 2.33±0.12 1.27±0.08 127.50±10.12*肝腎陰虛證 18 2.29±0.11 1.29±0.09 126.20±10.04*脾腎陽虛證 27 2.36±0.13 1.19±0.04 132.30±11.52*氣滯血瘀證 23 2.39±0.15 1.22±0.05 216.10±15.31
3.2 骨密度比較 見表2。
表2 中醫證型組間骨密度比較(±s)

表2 中醫證型組間骨密度比較(±s)
注:與腎陽虛證組比較,*P<0.05。
組 別 L1-4骨密度(g/cm2) 股骨頸骨密度(g/cm2)腎陽虛證 0.66±0.13 0.794±0.13肝腎陰虛證 0.63±0.11 0.783±0.10脾腎陽虛證 0.64±0.08 0.782±0.12氣滯血瘀證 0.57±0.07* 0.786±0.14
3.3 骨形成指標比較 見表3。
表3 中醫證型組間骨形成指標比較(±s)

表3 中醫證型組間骨形成指標比較(±s)
注: 與氣滯血瘀證組比較,*P<0.01;與肝腎陰虛證組比較,#P<0.05。
項目 PINP(ng/mL) ALP(U/L)腎陽虛證 42.79±8.13*# 76.43±8.17肝腎陰虛證 35.18±5.62* 73.53±6.78脾腎陽虛證 38.83±4.98* 74.52±8.01氣滯血瘀證 68.42±10.46 78.31±8.91
3.4 骨吸收指標比較 見表4。
表4 中醫證型組間骨吸收指標比較(±s)

表4 中醫證型組間骨吸收指標比較(±s)
注: 與氣滯血瘀證組比較,*P<0.01;與脾腎陽虛證組比較,#P<0.05。
項 目 β-CTX(ng/mL) TRACP-5b(mIU/mL)腎陽虛證 0.57±0.12* 4.92±0.31肝腎陰虛證 0.63±0.15*# 4.31±0.22脾腎陽虛證 0.49±0.11* 5.01±0.35氣滯血瘀證 0.76±0.16 6.95±0.54*
4 討論
OP作為全球的公共健康問題之一,已經成為我國中、老年人的常見病和多發病,給社會帶來沉重的負擔[9-10]。研究證實,CKD患者常伴有骨代謝紊亂,且這類患者的骨代謝紊亂可以被骨礦化促進劑、骨吸收抑制劑以及單味中藥、中藥復方等所改善[11-15]。因而,進一步探討CKD 3、4期伴骨質疏松患者中醫證型與骨代謝指標的相關性,對于指導中醫辨證及中藥的干預,具有潛在的應用價值。然而,迄今有關CKD 3、4期伴骨質疏松患者中醫證型與骨代謝指標之間的相互關系研究還相當匱乏。故而本研究基于對CKD 3、4期伴骨質疏松患者中醫證型以及中、西藥物的治療作用等方面的認識,采用流行病學回顧性研究方法,以期闡明CKD 3、4期伴骨質疏松患者中醫證型與骨代謝指標的相互關系,從而為CKD 3、4期伴骨質疏松患者中醫證型診斷的客觀化提供依據。
近年來,生物學標記物的研究與運用越來越廣泛。目前,骨代謝標志物檢測廣泛地應用于OP療效的評價,其中PINP、ALP被認為是最敏感的骨形成標志物之一,而β-CTX、TRACP-5b是較靈敏的骨吸收標志物,是監測骨吸收的主要指標之一。因而,國際骨質疏松基金會(IOF)和《原發性骨質疏松癥診治指南(2011)》[16]均推薦將PINP、β-CTX作為OP骨代謝主要評判的指標。本研究發現,氣滯血瘀證組患者中的PINP、β-CTX、TRACP-5b水平明顯高于其他3組患者,推測PINP、β-CTX、TRACP-5b水平可作為CKD 3、4期伴骨質疏松患者氣滯血瘀證與其他證型的客觀鑒別指標。
本研究收集的23例氣滯血瘀證患者中,CKD 3期有5例,CKD 4期有18例,觀察結果發現該組患者的甲狀旁腺激素水平明顯高于其他3組,說明CKD患者臨床中隨著慢性腎功能不全的進展,甲狀旁腺激素水平亦逐漸升高。此外研究亦發現,氣滯血瘀證組患者L1-4椎體骨密度值明顯低于腎陽虛證組患者,該結果可以為臨床研究與治療提供一些參考。
綜上所述,結合研究結果,我們大膽推測PINP、β-CTX、TRACP-5b水平可作為CKD 3、4期伴骨質疏松患者氣滯血瘀證與其他證型的客觀鑒別指標,并證實中醫證型存在客觀的現代醫學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