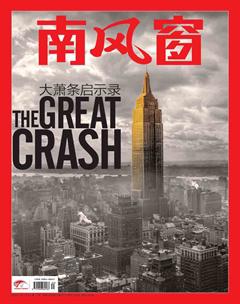不要拿走他人的棺材
李少威

倘若問我是什么東西第一次觸動了我跟哲學挨點兒邊的思考,我將回答說:“棺材。”
出身鄉土,棺材是見得多了的。童年玩捉迷藏,我有一個不被人找出來的法寶,那就是鉆進我奶奶的棺材里去。那東西除了我,沒幾個孩子敢靠近。
我奶奶的死去,是十幾年后的事情,但她的棺材早就置辦好了,并落滿了灰塵。那時的人過了中年,開始覺得自己有點往土里插的意思了,就要張羅打一口棺材的工作。打好之后,架在房梁上面,抬頭就能望見,看著就感覺踏實。
棺材閑置的時候都是絕對純天然原木色的,當它要被漆上顏色以及桐油的時候,那就是用上了。
老人把棺材稱為“大木”,雖然早已沒有那么大的樹—一截木頭就能打一口,但這個稱呼沿用下來,聽著顯得莊重、貴氣。就如年年的春聯都貼什么“金玉滿堂”“花開富貴”,從來不曾實現過,但人人都愛聽這些話。
有一次我奶奶可能又去二層上看她的棺材,從上面掉下來,受了很重的傷,她感覺可能要派上用場了,就跟父親說:“去把我的大木上漆吧。”然而她錯了,她的死去仍然是十幾年后的事情。
這么談論長輩之死亡,一般人聽著似乎有點不敬,然而這正是我的意圖。在我成長的傳統客家環境里,人們不忌談生死。我外婆活著的時候,如果孫兒輩讓她動了氣,她總是以這一句話開頭來斥責:“等哪天我死了……”
倘若問我是什么東西第一次觸動了我跟哲學挨點兒邊的思考,我將回答說:“棺材。”
和許多地方不同,我們那是二次土葬。人死之后,用棺材收斂,埋下去,過了幾年,還要挖起來,把遺骨認認真真用油擦拭一遍,納入一個壇子,那個壇子稱為“金埕”,“金”應當就是指遺骨,表示先人的可貴。把壇子入土,才有了墓碑,上一次叫“埋”,這一次就叫“葬”了。埋到葬之間,要起棺,原本很寶貴的棺材,挖出來以后就很不神圣了,丟在土坑旁邊不再去管。因為木板厚,往往仍然很結實,人們就會在需要的時候扛走,把它架在溝壑上面,聊以為獨木橋。我之所以不害怕棺材,跟走多了這種紅漆斑斑的獨木橋有關。
我奶奶最后也沒有用上她的棺材,因為她死得太晚,已經改了火葬。“死得太晚”是很多老人的真實想法,原本是城市火葬、鄉村土葬,后來鄉村也火葬了。我家后來搬到了縣城,但奶奶還在鄉下住,曾經被父親接到縣城住了幾個月。有一天她突然要求收拾東西回農村,因為她在樓下跟老頭子聊天,聽說了火葬的事情。然而回去是回去了,也沒有避免她害怕的結局。
人都怕死,但我們有辦法平衡這種恐懼。宗教有神,有來生,有極樂,這是一個辦法,但我們中國人不信宗教,至少在死的問題上不信,宗教是活著用來尋求現實幫助的。我們相信倫理,并在倫理上引申出對死后的想象。棺材保護死后的人,讓他完整,讓他面目可識別,因而就能找到先死的親人或朋友,這就是安全感的來源,棺材讓人們相信死后并不孤單飄零,仍有一個家。如果這叫迷信,那也是必要的迷信。
火葬當然是文明的,我也支持。不過我仍有困惑,我們那的土地和北方平原不同,到處是山,人死上山,墳墓和耕地以及水土保持都沒有絲毫沖突。年年掃墓,都要費盡周折披荊斬棘才能找到墳墓,因而可見它和野草雜樹也沒有什么沖突。火葬沒有給自然帶來什么變化,只給人的心靈造成了改變—人們對死后的世界,再也無法預計,不能信任,充滿恐懼,念茲惶然。
我奶奶是本鄉最后一批有棺材的老人,雖然最后沒有用上,但生前的每天,她都留心著怕被人偷去了。以我的看法,不管將來最終是火葬還是土葬,當人有棺材的時候,無論如何別拿走了,那太殘忍,非人所當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