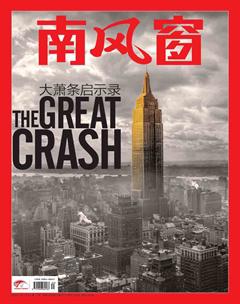啟蒙:一場沒有觀眾的演出
李少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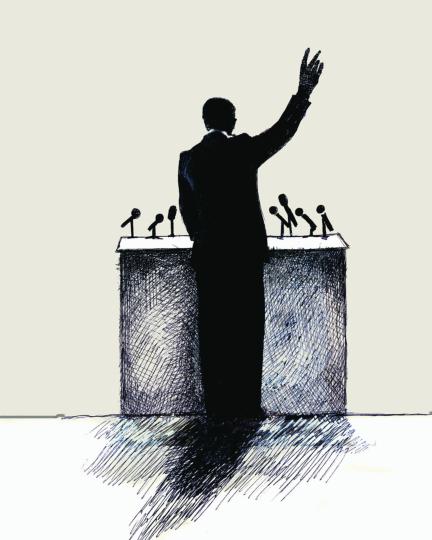
“兩袖紅塵碧雨,一枕青史黃粱。”2018年7月,象牙塔里的熊培云再次進入公眾視野時,以此為題寫了一篇文章。
不必為此絞盡腦汁,因為你永遠都不會知道這句話是什么意思。日常里,人們如果用這樣的標題來寫公眾號,那么閱讀量如能超過100,就值得出去喝兩杯了。
熊培云的出現,讓我聯想起通過《十三邀》訪談節目再次進入公眾視野的許知遠。他用純虛構的內心來面對無限真實的外界,對大眾而言,幾乎是對“作”的最完整呈現。
許知遠用一種娛樂的形式,邀來了俞飛鴻、馬東這些“娛樂業時代”的既得利益者對談,但卻一直孜孜以求地追問著反娛樂的哲學問題:你為什么不反抗這個時代?
這的確有些滑稽,就像在三伏天穿著棉衣,汗流浹背地到處問人:“你不熱嗎?”
許知遠應該感覺到冷。不管是否成功,他都曾經努力扮演過一個啟蒙者的角色,但今天不是一個啟蒙的時代,今天的大眾早已愛上了蒙在頭上的那塊黑布,舍不得把它扯下來。曾經的啟蒙者還是一樣的裝扮,但在今天已經顯得自帶幽默感。
“那時”的公共知識分子
讓人有點起雞皮,熊培云用那個超凡入圣、莫名其妙的標題,竟然是為了回應性騷擾指控。
在文章的開頭,他這樣寫:
“因為一個莫須有的污名,我不得不辜負手中的筆,背叛為自己立下的名節與誓言,為此刻無謂的名譽去戰斗,以應付無數人無休的質詢。這將是我一生中最不重要也最深感羞恥的文字。
“人要做自己靈魂的知己。我能預料或許明天就會后悔于今日的軟弱與屈從。我沒有跟著自己的鋼鐵意志走,在最忙碌的時候卻要浪費時間解釋我當時如何光明磊落。”
吸引我的不是“真相”,而是一個人面對這樣簡單、直接的指控,在發文澄清之時,仍然有心思去構筑這般精巧的文字,精巧如故宮里的自鳴鐘。
“辜負、筆”“背叛、誓言”“名節、戰斗”“羞恥的文字”“靈魂的知己”“軟弱與屈從”“鋼鐵意志”“當時、磊落”……短短150字,就包羅了幾乎所有的精神奢侈品,有一種在香榭麗舍大街瘋狂掃貨的琳瑯滿目感。
倘若放在心理分析專家的手中,這樣的文字設計,很可能就意味著指向某種掩飾內心的動作。然而心理分析如果不具備歷史意識,也會陷入一定的魔障。在我看來,熊培云并沒有要用一堆奪目的詞匯來掩飾什么。因為在十幾年前,乃至二十多年前,有一大批作者都有這樣的文風,熊培云和許知遠都是其中之一。
在那個時代里, 錘煉出這樣的文風,顯得特別有公共知識分子的范兒—這里不是指“公知”,而是曾經真正存在的公共知識分子,是紙質媒介時代自覺的啟蒙者。
對他們而言,這是一種習慣成自然的能力,就像內臟的運動—自主神經活動是不受意識支配的。
符號系統會限制人的思維,當一個人徹底被某一套符號系統所束縛,他就很難再有其他的面目。而也正因為其無意識,所以這種束縛就來得特別頑強,幾乎不可再擺脫,只要開口說話,這就是他們的腔調。在旁人看來,這是說話的一種方式,而對于他們,這僅僅是說話。
他們先有一個神秘的公式,然后把自己的身體一件件拆下來,裝配在這個公式的骨架上。
公式的主要功能在于,往它上面一套,那么任何簡單不過、平淡不過乃至無聊不過的話題,都會顯得特別有意義或特別無意義。無論是何者,都頃刻帶上了人文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光環,用來匹配一臉的人間憂憤,有時會顯得十分矯情乃至肉麻,唯局中之人不覺。他們會在任何千變萬化的場合都套用這一公式,包括原本只需簡單明了的回應指控。
屬于許知遠、熊培云他們的時代,跟現在不一樣。那時的公共知識分子,都有從內到外的文青氣質。這或許是因為那個時代里人們對漂亮的文字還有深深饑渴感,詩歌已經死去,散文式的表達彌補了紙面的干涸,潤澤了閱讀者的心靈。
通過不斷的重復性想象,他們創設了一個意識世界,這個世界和現實世界幾乎完全對立。在這一點上,許知遠顯得比熊培云更典型,他孜孜不懈地和每一個世俗者談論著一尊“神”,這尊“神”只有他一個人能夠感知。
這確實是一種挺蒼涼的場景。
屬于許知遠、熊培云他們的時代,跟現在不一樣。那時的公共知識分子,都有從內到外的文青氣質。這或許是因為那個時代里人們對漂亮的文字還有深深饑渴感,詩歌已經死去,散文式的表達彌補了紙面的干涸,潤澤了閱讀者的心靈。
任何一種文化的痕跡都產生于當時的歷史、社會現實,具備這種自然奢侈的文字能力的人,也都是被時代“捏造”出來的。只不過他們從不承認,而堅稱自己的氣質獨立于時代。
也正因為他們是被決定的,因而我倒更愿意相信在奢華的文字、憂郁的眼神背后,仍然是真誠的內心,至少許知遠、熊培云是這樣。
被打斷的啟蒙
本文的目的不是揶揄熊培云和許知遠,事實上我認為他們是最后一批啟蒙主義者的代表,是有信仰的人—不管他們本身的能力是否匹配這種歷史角色。
他們的內心里其實有一種文字的不朽情結,因而特別苛求字面上對一般大眾的超越性。他們相信,只有一眼掃過去就明顯具有形式上的超越性,文字才會被閱讀者認真對待。
至少十幾年前,我們的社會還崇拜這樣的作者。這是對1980年代啟蒙傳統的延續,也是強弩之末。在啟蒙時代,無論精英還是大眾,每一個人都愿意面對內心,對于問題的解析,是“求諸己”而不是“求諸人”的,解析的目的,也是為了規范自身,而不是規范他人。
正因為求諸己,所以人們在表述思想的時候,就會在文字里間夾著許多個人心理活動,而且見縫插針地顯示內心追尋的理想境界,今天看來迂腐且肉麻,但在特定背景下,卻營造了一種竊竊私語的交流感。
但今天早已不是一個啟蒙時代,這是許知遠、熊培云這一類知識分子一說話就和現實格格不入的原因。
這個判斷的前提,不是啟蒙已經完成,而是啟蒙已被打斷。
與當下有直接的歷史關聯的啟蒙,是從清末發軔、在新文化運動中大張旗鼓地對理性、現代性和光明世界的追尋。正如歐洲著名歷史學家史傅德在《公民社會與啟蒙精神》中的描述:“精神在覺醒,人們意識到四周一片混沌,要在個體和社會的精神層面重建秩序,恢復光明。康德把這種狀態比作沸騰的海洋中間的一座小島,社會層面的魯濱孫式的覺悟。”
無論西方還是中國,啟蒙的主要媒介,甚至是至關緊要的工具,都是印刷術。15世紀出現的古登堡印刷術催生了西方的啟蒙時代,書報雜志都多了起來,而且變得便宜,更多的讀者可以得到知識,而作為知識生產者的精英也受到傳播的激勵。現代民族國家借此奠定社會意識基礎,而更深層的現代性范疇,也在民眾中散發、接受和內化,成為現代理性社會運行的大背景。
以印刷術為依托的現代性啟蒙,對于寫作者和閱讀者雙方,都是沉靜的、耐心的,因而其內容可以做到全面、系統、深刻,追求“富有邏輯的復雜思維、高度的理性和秩序、對于自相矛盾的憎惡、超常的冷靜和客觀”,同時還可以對文字進行精心的修飾與設計,讓它變得機簧精巧。
對于現代西方國家,這個啟蒙過程在19世紀就已經完成了,而中國那時剛剛起步。中國人真正有條件廣泛接受印刷啟蒙,是20世紀80年代以后的事情。但在20世紀,電子媒介開始興起,并逐漸取代了印刷媒介對思想交流和傳播的統治地位。用尼爾·波茲曼的概括,是“闡釋時代”逝去,“娛樂業時代”出現。“娛樂業時代”的主要特征是信息的碎片化,無意義的、只能用作娛樂的信息成為人們接受的主體、沉醉不歸的樂園。
一般大眾早就沒有耐心細讀那些經過深思熟慮的文字。中國與西方的不同在于,在時代轉換的節點上,西方的現代性啟蒙早已完成,而中國還在進行中,卻因此進行不下去了。
此即所謂“打斷”。
余暉中的啟蒙者
啟蒙主義者如魚得水的時代,必須滿足兩個條件。
一是有一批知識精英,自覺地擔當文化使命,看到社會的所見缺乏廣度、精神缺乏秩序、美好的價值有待普及,從而去打開一扇窗,去努力建立秩序,去做價值普及的工作。
二是有一個大眾環境,愿意承認自己的鄙陋,并以鄙陋為恥,自覺地從內心需求出發去接受啟蒙。他們相信一個事實—在庸眾的生活之外,還有絢麗奪目的世界,云層之上,還有星空。
概括起來,精英和大眾之間要存在巨大的認識落差,這種落差要被公認為值得縮短,而且雙方都樂意這樣做。其關鍵所在,是精英對大眾擁有一種不言自明的知識權—啟蒙的應有之義是要逐步搗毀神圣的偶像,但要實現這一目標,啟蒙者本身卻要成為臨時的偶像。
但今天早已不是一個啟蒙時代,這是許知遠、熊培云這一類知識分子一說話就和現實格格不入的原因。這個判斷的前提,不是啟蒙已經完成,而是啟蒙已被打斷。
然而因為“娛樂業時代”的到來,這些條件幾乎是一夜之間消失了。原本舞臺上那些啟蒙者,突然發現觀眾紛紛起身離開,直到席上空無一人。許知遠的每一次尬聊,熊培云的讓人起雞皮的“供詞”,都是觀眾已經離席,而演員的表演卻還停不下來的象征。
原本被追捧的啟蒙精英氣質,剎那間變成了一種怪異的存在;大眾不再仰視啟蒙精英,而把欽佩投向了娛樂精英和財富精英。大眾變了,原來的一些啟蒙者還沒有變,結果是看上去后者反而需要被啟蒙。
大眾不再是原來的接受者,而成為了世間萬事的裁判,他們無所不知,在認識上不需要任何權威。因為今天不缺知識,尤其不缺人文知識,沒有任何一種人文知識能在今天帶來文化震驚。
除了少數關注邏輯、關注思想、關注知識之間的內在聯結的人,大部分人都不會再感受到知識有何美妙可言;除了少數穿透物質、穿透現象、穿透熙攘紅塵的外在浮華的人,大部分人都不會再意識到社會有何危機隱伏。
也就是說,隨著啟蒙時代逝去,知識誠然俯拾皆是,但知識的社會內化機制已經停擺了。不同階層、不同身份、不同年齡、不同知識層次的人對有價值的知識的公認,以及對這些知識的共享、探討和實行,已經難得一見。知識對大多數人而言,都成了一種可以便捷地獲取的外在之物,而不是頭腦和心靈的動能。
許知遠在《十三邀》中對任何人都試圖挖掘一點什么精神意義、總是提出一些脫離實際的問題的表現,被認為是“自戀”的。這正是大眾所偏愛的解釋一切現象的方向,這毫無意義,事實上在脫離歷史眼光的社會里,人們根本不打算解釋任何問題。今天的主流思考,都建立在對外的攻擊性上,每個人都假設自己是一個聰明人,蘇格拉底、曾子那種內省式的探討問題的方式,已經顯得非常可笑。
最后的啟蒙者在余暉中繼續想象一個應然的世界,仍然忍不住要說話,但一張口就傳遞給人們一種恩格斯所說的“年老色衰、孀居無靠”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