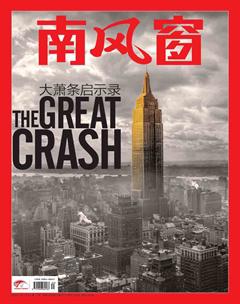邂逅蕭紅
榮智慧
去香港的時候,我一般會住在上環。不像尖沙咀或者中環那么熙熙攘攘,也不像深水埗或者新界那么破敗。上環的好處就是干凈、幽靜,同時充滿了市井氣息。有時結束工作后有一點閑暇,還可以沿著街道慢慢散步,爬爬山。
從住處向北往山上去,經過一所學校:圣士提反女子中學(St. Stephens Girls College),校門口有塊牌子“慶祝建校112周年”,看來是1906年建立的。這么一心算,思緒就回到了“現代文學”時代,這才猛然驚覺,蕭紅的一部分骨灰就埋在這里。繞著學校走了一圈,大門緊閉,也沒有其他指示標志,想來即使是這里的工作人員,也并不知道著名作家蕭紅長眠于此。
小學四年級第一次聽說蕭紅,語文課學了她的《火燒云》。有時放學回家看見天邊的彤云,都會想起她寫的“晚飯一過,火燒云就上來了。照得小孩子的臉是紅的”。初中去看她的《呼蘭河傳》,才發現她也是東北人,呼蘭河離我的家鄉也并不太遠。而且,我還找到了《火燒云》的原文,就在《呼蘭河傳》里。
原文里還有一句國罵,是喂豬的老爺爺看到小豬在夕陽下變成了金色時說的,但是課文中給刪了。于是對蕭紅很有好感,覺得她很有趣,很“敢寫”。后來又斷斷續續看了她的一些小說,還有給蕭軍寫的信,里面也經常夾一句“他媽的”,令人忍俊不禁。
蕭紅1911年出生在黑龍江省呼蘭區。她從東北流亡到上海、北平、重慶,最后到香港。1942年,纏綿病榻的蕭紅所在的瑪麗醫院被日軍接管,她被轉至一家法國醫院。很快,法國醫院又被日軍占領,蕭紅被送到圣士提反女校設立的臨時救護站。1月22日6時陷入昏迷,10時逝世。1月24日火化后,部分骨灰安葬于淺水灣麗都酒店前的花壇里,1957年遷至廣州銀河公墓;另一部分骨灰由端木蕻良埋在圣士提反女校后院的土坡下。

雖然她的創作時間只有9年,去世時也不過31歲,但在現代文學史上的地位并不低。她和蕭軍、端木蕻良、駱賓基、舒群等人被稱為“東北作家群”,開創了抗日文學的先聲。自蕭紅起,第一次有人將自己的生活與東北廣袤的黑土、鐵蹄下不屈的人民和茂盛的高粱、玉米融在一起,以濃郁的、對鄉土的眷戀和敏銳、明麗的風格震動文壇。
《呼蘭河傳》是她的代表作。蕭紅寫出了自己記憶中的家鄉,一個北方小城鎮的單調的美麗、人民的善良和愚昧。富有東北風俗的畫面不僅僅表現了地方色彩,更包含了巨大的文化含量和深刻的生命體驗。在近100年里,很難找到像蕭紅那樣,文字細膩平實,融合強烈的感情又內含英武之氣的作家。即使是后世最嚴苛的文學評論家,也常常把“天才”的名號送給她。
蕭紅短暫的一生過得并不開心。雖然她得到了魯迅的關懷,小說《生死場》作為奴隸叢書出版,在文學界是一顆冉冉上升的新星,但三次不愉快的婚姻、喪失的兩個子女、未完成的事業,都令她滿腔憤懣。去世的三天前,她因為裝了呼吸管而不能說話,寫下“我將于藍天碧水永處,留得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有一次,她給弟弟寫信,還說沒想到我們都到了靠近大海的地方。我站在圣士提反女子中學的門外,心想,從遙遠的、一年有4個月飄雪的東北來到炎熱的香港,蕭紅也許更沒有想到,她將永遠面對大海,目送著一代代的女孩子讀書、成長。那些平淡的幸福是她不曾有的,但一定是她樂于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