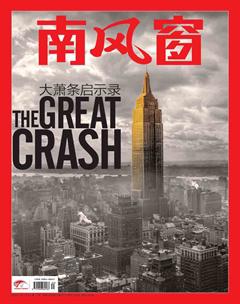資源型城市突圍的徐州樣本
黃靖芳

以往的徐州被煤灰和煙囪籠罩,作為江蘇省唯一的煤炭生產基地,煤炭生產曾是當地的支柱和基礎產業。
在從不缺乏“明星城市”的中國東部經濟區,位列其中的徐州正努力擺脫過時的標簽,試圖以不同于過往“資源型城市”的形象為人所知。這座城市正在積極求變。
2013年,徐州被列入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名單中。這是一個我們不陌生的名詞,目前在廣袤的國土上,分布著262個同類型的城市,它們被過去引以為傲的資源所絆倒,曠日持久的開發帶來了沉重的積弊—生態和社會問題突出,發展內生動力不足。
機遇的天平還會傾向它們嗎?
2017年12月,習近平總書記將十九大后的首次地方考察設在了蘇北城市徐州,一定程度釋放了肯定當地轉型實踐的信號,“資源枯竭地區經濟轉型發展是一篇大文章,實踐證明這篇文章完全可以做好。”
徐州在尋求轉型和突圍過程中,所經歷的發展困惑和認知變遷,也許能為其他同類城市帶來借鑒和思考。
煤炭的記憶
徐州的礦區分別位于銅山區、賈汪區和沛縣境內。其中處于東北部的賈汪區又是最重要的煤炭基地,轄區最多時有煤礦250余座。
現在不管走在賈汪還是徐州市區的街頭,除了藍白路牌上偶爾出現的“煤建路”“煤港路”等地名,已經很難找到煤炭留下的直接痕跡。但這些因為地殼變動而深埋于地下的遠古積淀,深刻影響了整個城市的生活方式。
陳先楊在賈汪泉西村居住了30多年,他說在這里只要問起上了年紀的人,幾乎都藏有跟煤礦相關的生活記憶,他曾經當兵的父親未退休前,就是在礦務集團所屬的水利廠當廠長。小的時候,每條村里幾乎都開有一口礦井,這組成了村里主要的經濟收入。大量的采掘需求吸引了各地的勞動人口,包括四川、山東省,以及鄰近的鹽城等地區的青壯年都紛紛前來打工。
處于鼎盛時期的煤炭業也提高了相應職業的地位,在徐州礦務集團(以下簡稱“徐礦”)張雙樓礦工作的吳建群,80年代末的時候跟隨父親的腳步成為了一名一線工人,做的是掘進的工作,負責在礦層中開掘井巷,為后續的采煤做準備。那時候他看中的是成為正式工能帶來的穩定收入和糧票、油票等福利,讓他有“吃皇糧”的優越感。
在20世紀70年代,徐礦的發展也達到新的高峰,不僅全局(當時還稱為“徐州礦務局”)產量超過千萬噸,躋身全國十大礦務局行列,在相應的改革措施中也敢于大膽嘗試。
“80年代我們已經率先實行了煤炭經濟的總承包”,徐礦集團投資發展部部長莊建偉向《南風窗》記者表示,這是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大背景下,為煤炭行業順利走向市場的首次試水。
徐州市財政局的資料顯示,1988年煤炭行業的工人占到全市職工總數的25.83%,工業產值占到全市的9.3%,實現稅金占6.8%。與多數資源型城市的生長路徑相似,資源型產業無可置疑地成為了支柱產業。
其實,煤礦工人除了優越的一面,也隱藏著比其他職業更多的風險。同樣是本地居民的老王,在十八歲的年紀就輟學,被家里帶去下礦打工,礦道里只有半米高的空間,他在里面作業需要一直趴著前行。每次上井出來后,他的臉都被蹭得漆黑,“連皺紋里都是黑色”。有一次,在井下爆破施工過程中,因為通知不及時,兩個還在前方處理的礦工被突如其來的炸藥炸掉犧牲,嚇得他把這份干了半年的工作辭掉了。盡管收入不算低,但是他覺得實在是太苦了。
1988年煤炭行業的工人占到全市職工總數的25.83%。
在發展中,端倪初現的是環境問題。因為地下煤炭資源的過度開采,導致采煤塌陷地叢生,成為困擾城市進一步前進的難題。2017年的數據顯示,有超過三成的塌陷地在賈汪,面積一共有13.23萬畝。
生態修復
在總書記對徐州結束考察當天,新華網刊發了相關文章,為目的地“首選”徐州做出了解釋,“徐州和全國一樣人均GDP都在6萬元上下,城鎮化率都在60%左右,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都在2.3萬元左右……就幾個主要統計數據來說,徐州的發展水平和全國平均水平相似度極高。”
由此側面可窺見,徐州身上不僅具有了資源型城市的身份,還有與平均水平接近的發展水平,因此徐州的發展可以說是既有普遍性意義,又有特殊性的經驗。特殊性之一,就體現在對于生態修復的重視。
盛夏的潘安湖濕地公園水生植物郁郁蔥蔥,如今當出租車司機陳先生從機場拉人到賈汪的時候,肯定少不了提起這個濕地公園。不過在這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他其實都不怎么踏入這個區,因為那時候道路兩旁都是黑乎乎的,是他不敢去的臟地方。但是現在,他接到的以此為目的地的游客越來越多;在公共假期來臨的時候,六七公里外就開始大排車龍。
在此之前,這里是徐州集中連片、面積最大的采煤塌陷地。據區委書記曹志向媒體披露的情況,當時政府只能拿出5億元的資金,最終是通過各種途徑,成功融資22億元的資金,開啟了對其進行為期五年的集中治理。
對采煤塌陷區進行綜合治理是一個世界難題,國內傳統的模式主要為采煤塌陷穩沉后進行治理,即采煤塌陷—補償損失—塌陷地閑置—治理,但是這個過程一般非常漫長,也導致了閑置土地不能有效利用。潘安湖的模式可以說是突破了以往的傳統模式,集“基本農田整理、采煤塌陷地復墾、生態環境修復、濕地景觀開發”四位一體的整治。即便如此,因為資金和資源投入的巨大,潘安湖的模式也難以進行大規模的復制和模仿。
據曾參與徐州城市規劃調研、對礦區修復有專門研究的中國礦業大學教授常江向《南風窗》記者回憶,對于以塌陷區為代表的生態治理修復,是一個動態的深入過程,不管是管理者還是普通市民,都經歷了認知的不斷變化。
同是常江研究團隊成員的另一位礦大教授羅萍嘉曾經在其發表的論文里提出這樣一項觀察,在2004年編制、2014年修訂的《徐州市城市總體規劃(2007-2020)》中,主要礦區區域大多處于尚未被規劃覆蓋的區域,對于工業廢棄地也尚未提出具體有效的生態規劃策略。也就是說,對于規劃中還沒有體現針對塌陷區的系統規劃設計。
當然,這只是以徐州為例的一個普遍情況。事實上,徐州的采煤塌陷地綜合治理工作起步很早,在1988年就開始了,是全國最早的三個采煤塌陷地農業綜合開發復墾國家級示范區之一。但這更多反映的,是當時國內對城市生態規劃普遍不夠深入的思考。
常江也承認,在塌陷地開始出現之初,人們習以為常地以為這塊地就應該被廢棄,也默認這就是采煤帶來的正常現象。觀念的改變源于客觀形勢的催化。當90年代城市化浪潮席卷,對建設用地的需求逐步上升后,對于塌陷地的利用開始逐步提上議程。在這方面,徐州從以示范工程為抓手開始,逐步推進修復的工作,從立體養殖到小片區的湖區改造,在國內取得了比較好的示范效果。
塌陷地的修復意義除了能為城市生態景觀和形象帶來改變,更是為城市進一步的轉型發展留出了空間儲備。逐步認識到恢復生態的重要性后,現在的賈汪區更是以生態為支點,在區政府相關負責人回復《南風窗》記者的文件里提到,“推進轉型發展過程中,賈汪區把生態轉型作為突破口和主軸線,以生態轉型帶動和倒逼其他轉型”。
后煤炭時代
2011年,徐州市賈汪區被列入全國第三批資源枯竭型城市名單。
作為資源枯竭面臨的后果之一—生態的治理其實需要投入大量的資金。莊建偉向記者透露,徐礦在徐州形成的采煤塌陷地就有24.2萬畝,多年來已經累計投入了42.47億元,主要用于建設濕地公園、水源涵養區和新農村特色小鎮。
煤炭開采的邊際成本愈加提高,城市的產業結構也亟待更新注血,進入后煤炭時代的城市,應該如何是好?
事實上,徐州是國內較早轉型的資源型城市之一,在十幾年前就開始了對產業的轉型升級。
轉型有客觀上的倒逼影響。徐州煤炭的開采歷史悠久,而且承擔的是江蘇省唯一能源基地的重擔,莊建偉形容,這是一個“經濟大省,能源小省”,綜合因素決定了其面臨枯竭的時間會比其他城市更早。進入21世紀,徐州礦區的剩余可采儲量僅剩3億噸。
城市化浪潮席卷,對建設用地的需求逐步上升后,對于塌陷地的利用開始逐步提上議程。
作為立足在徐州的能源企業,徐礦的轉型路徑是和徐州整體轉型的步伐一致的。在面臨著資源接替、人員轉移等緊迫的問題后,2003年開始徐礦向外創業,到西部和境外開發能源,也由此帶動了一批原本的失業人員異地安置和就業。而徐礦的定位也從主要提供煤炭能源向發展煤電化核心產業、服務江蘇能源安全保障的特大型省屬能源集團轉變。
尋找替代性產業也是城市轉型的主要出口,徐州現在已構建以裝備制造、食品及農副產品加工等6個優勢產業為主體,新能源、新材料、新醫藥等6個戰略性新興產業為先導的“6+6”現代工業產業新體系,“徐工提出提前一年在2019年實現世界前五、2024年實現世界前三的目標,”在裝備制造業的代表企業徐工集團回復《南風窗》的文件里提到,“其最關鍵支撐是落地‘技術領先、用不毀行動金標準”。
當然,轉型的陣痛和遇到的困難也仍然明顯。光是在賈汪,就仍舊還有6萬余畝塌陷地未能完成治理,如何籌集資金、因地制宜進行開發利用,都是未來必須面對的實在問題。
在接受采訪時,莊建偉也直言,自從20世紀70年代被當時的煤炭工業部劃歸到江蘇省后,徐礦就轉變成了一家為江蘇省服務的省屬企業,這樣的性質也讓徐礦在與其他能源央企競爭時處于劣勢,難以獲取最優質的資源和政策的傾斜。
而同時,徐州也在不斷走向戰略的高位。2017年6月,國務院正式批復《徐州市城市總體規劃(2007-2020)》,明確了徐州淮海經濟區中心城市的定位。值得一提的是,以江蘇、山東、河南、安徽等20個城市組成的淮海經濟區,容納了多座資源型城市和老工業基地,大多面臨著相似的資源衰退、環境治理的難題。
未來的徐州的進一步發展有其優勢,比如優越的交通區位,地處蘇魯豫皖四省交界,徐州是京滬線、隴海線兩大鐵路干線的交叉,高架快速路和公路資源都相當發達,京杭大運河徐州港是全國主要的內河港口之一。
同時,常江向記者分析說,徐州作為蘇北城市,能享受到更多來自省內的政策支持。由于近年來蘇南蘇北城市發展差異的拉大,蘇南的產業在十多年前就開始有策略地向蘇北轉移,帶動了當地工業迅速增長,也讓徐州的轉型道路有了更多的保障。
徐州還有很長的道路要走,這個探索過程也將有益于其他資源型城市的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