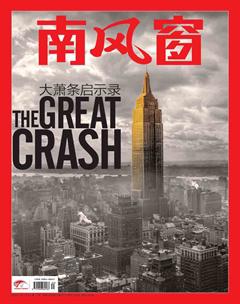劉鶴: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
本文為 《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總報告摘編,兩次危機分別是指始于1929年的大蕭條和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該書主編、總報告執筆人劉鶴,時任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現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

危機的影響
本項研究的基本邏輯是歷史的周期律。周期性是歷史變化和自然界的本質特征,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重要特點。研究的主要任務,是試圖發現在兩次繁榮蕭條之中那些最引人注目的事件發生的先后順序和相似程度,更準確地說,這項研究是試圖理解兩次危機發生前技術和經濟背景的類似性,刻畫在這樣的背景下政府行為和大眾心理的特征,描述兩次危機的宏觀發展軌跡,從而為應對危機的決策提供依據。
非常明顯,兩次危機對人類社會造成災難的程度不同。從危機爆發初期的情況看,1929年大蕭條造成的經濟總量損失和商業破壞要大大超過本次金融危機。但本次金融危機的后續發展演變日趨復雜,美國失業率連續兩年多居高不下,持續維持在9%上下,房價仍在低位徘徊,復蘇過程曲折反復;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影響不斷深化,經濟社會政治產生共振,負向反饋,不確定性和風險持續提高。總的來看,這次危機盡管短期殺傷程度要輕,但調整可能需要更長時間,深度影響難以估計。
大蕭條后,資本主義國家吸收社會主義理論,社會保障制度在發達國家普遍建立,宏觀經濟管理制度從無到有且日趨完善,經濟和社會發展建立了穩定器和剎車系統。另外,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基于對上次大蕭條的認識,主要發達國家政府都對經濟進行了快速的直接干預,在較短時間內改變了經濟自由落體的狀態。因此,本次危機對經濟和社會的短期損害還沒有達到上次大蕭條的程度。

“基辛格定律”可能被再次驗證。基辛格在他的名著《大外交》一書中開宗明義地指出,世界每隔百年會出現一個新的全球大國。這個判斷可能被兩次危機所證實。大蕭條后世界經濟重心由歐洲轉向美洲,美國在世界經濟中發揮主導作用,美元占據支配地位,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誕生,世界經濟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變化。這次危機發生后,全球發展的重心向亞太地區轉移,二十國集團(G20)平臺產生,世界實力對比正在急劇變動,國際經濟秩序正在發生變化。
從這個意義上看,危機不僅具有對生產力發展的破壞作用,也有積極的創新作用,更有強烈的再分配效應。總之,大危機所分配的不只是一個國家國內的財富,而且是國家之間實力的對比。危機的再分配效應是無法抗拒的,世界經濟秩序將繼續發生穩步但不可逆轉的重大變革。
家庭債務迅速增長,成為推動美國總體債務率從1916年占GDP的170%上升到1933年300%這一歷史高點的主要因素。
負債問題
兩次危機爆發前都存在由寬松貨幣和金融環境支撐的不可持續的過度債務。20世紀20年代,美聯儲采取寬松貨幣政策,貼現率由1921年的7%下降到1927年的3.5%,信用消費與廢棄付款迅速增長,到1926年約70%的小汽車采用分期付款方式銷售。家庭債務迅速增長,成為推動美國總體債務率從1916年占GDP的170%上升到1933年300%這一歷史高點的主要因素。
2008年美國信用卡總債務接近1萬億美元。由房貸機構降低貸款標準發放的次級貸款總額達1.5萬億美元。聯邦政府財政赤字在小布什政府時期不斷擴大,美國總體債務水平危機前再次上升至歷史至高位,2009年達到GDP的370%。
并且,兩次危機都處在金融監管大寬松的時期。1933年以前,美國金融業處于自由放任時代,沒有金融立法,也無存款保險制度和現代央行制度。商業銀行除經營存貸款業務外,還可經營證券經紀或自營業務。股票購買杠桿率高,只需付10%的保證金,其余資金可從銀行獲得,大量銀行資金進入股市。金融市場中投機、欺詐及內幕交易盛行。
1970年代后,美國開始新一輪金融自由化浪潮。1999年頒布《金融現代化服務法》,取消分業經營限制。證券業普遍進行高杠桿交易,2007年杠桿率達到30倍。商業銀行將發放的貸款證券化,投資銀行將證券化產品重組為擔保債務憑證(CDO)出售,還發展了信貸違約掉期(CDS)以對沖風險。房地產相關金融產品過度膨脹,2008年在1.5萬億美元次貸的基礎上發行了2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BS),10萬億美元的擔保債券憑證(CDO)和62萬億美元的信用違約掉期(CDS)。
私人過度舉債、金融部門杠桿率提高、企業過度投資、貨幣政策過于寬松在兩次危機發生前都有表現,政府債務水平攀升在這次危機應對中表現明顯,其實質都是在產業轉型滯后、缺少新增長點的情況下,通過短期中用債務擴張和債務轉移的辦法來擴張消費和投資需求,以試圖解決技術驅動力弱化、產業利潤下降、生產出現過剩等長期問題,其實這樣做只會使消費和投資超越實際支付能力和現實需要,制造出難以持續的虛假繁榮,并不能根本解決由技術長周期末端導致的產能過剩,最終會以危機方式被迫收縮。
吸取兩次危機的經驗和教訓,結合我國發展的實際,當今和今后時期在處理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的關系方面,我們要特別注意三點:首先,貨幣金融環境不能助長債務型經濟過度發展;第二,加強宏觀審慎監管和系統性金融風險防范;第三,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
貧富分化
收入分配差距過大是危機的前兆。大蕭條期間所表現出的,是私人占有和社會化大生產之間的矛盾,表現形式是實體經濟產能過剩和有效需求不足。這一次危機則與全球化、互聯網和知識經濟的發展、經濟虛擬化程度提升、不同國家人口結構的變化有更多的關系。但最突出的表現是,生產資料名義所有權和實質支配權分離,權力集中到虛擬經濟領域極少數知識精英手中。
通過增強教育公平、完善財稅體制、促進創新就業等措施,遏制在地區、行業、城鄉、人群中收入分配差距的進一步擴大,均衡提高需求支付能力。要建立合理水平的社會安全網,既能夠“托底”,又不養懶人,還要長遠可支付,做到公平、效率和可持續性的統一。要促進社會公平正義,暢通民意表達渠道,倡導理性平和心態,防止觀點和立場極端化傾向造成社會分裂,推動社會共識達成。
最突出的表現是,生產資料名義所有權和實質支配權分離,權力集中到虛擬經濟領域極少數知識精英手中。
要促進機會公平,防止權力同金錢結合造成的社會結構固化和政府服務人民的宗旨背離。要堅決防止有民粹主義傾向的政策,最低工資過快上漲、勞動者過度保護、工資水平提高過快,會使勞動力成本高出均衡,反而會增加失業和降低經濟競爭力。
貿易博弈
大蕭條時美國的危機通過貿易、金本位渠道向其他工業國家擴散。一方面,受危機沖擊在全球貿易萎縮的同時,各國提高關稅、增加進口配額等“以鄰為壑”的政策使全球貿易被進一步拖累,全球貿易總額從1929年的360億美元縮小到1932年的120億美元;另一方面,處于金本位制度下維持貨幣平價的需要,各國陷入競爭性的提高利率和對黃金的爭奪中,美國通貨緊縮通過金本位迅速向全球擴散,帶來各國經濟同步衰退。
全球危機造成全球需求同步萎縮,國經濟貿易關系“零和博弈”性質增強,合作應對危機難度加大。大蕭條后通過貿易保護來搶奪市場,最終通過戰爭拉動需求,消耗過剩產能。這次危機發生初期時,各國聯手合作應對,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有效遏制了危機的深化和蔓延。但在形勢有所好轉后,繼續合作應對危機的難度提升,貿易戰、匯率戰、投資限制等各種形式的保護主義抬頭,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試圖通過“再平衡”來轉嫁調整責任、通過制造全球通貨膨脹來削減債務負擔。今后對商品、市場和資源的爭奪越來越成為主導國際經濟關系的首要因素。
美國在大蕭條和二戰中,通過適時保持中立,避免卷入戰爭,完成全球霸主地位的最終確立。我們也要抓緊做好的自己事情,密切關注外部環境變化對我國的影響,不輕易對外承諾,在萬余歐債危機救助、擴大對外投資和購買等問題上,要謀定而后動,選擇最佳出手時機,最大程度實現我國的國家戰略意圖和利益。還要認清順差國家時機上在“再平衡”過程中處于主動,不能在“再平衡”壓力下,承擔過多國際經濟調整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