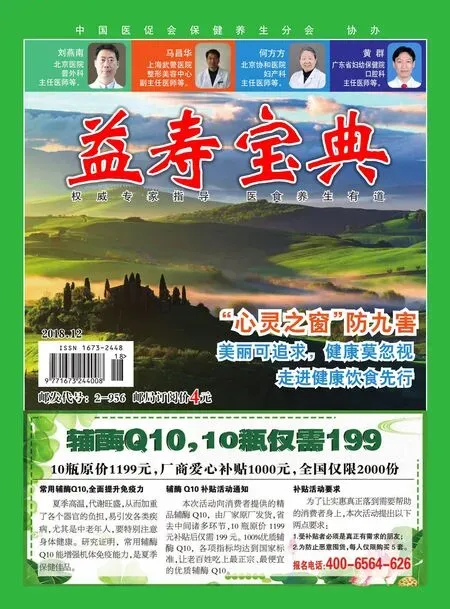孫思邈與搖鈴行醫
文/陳昂

孫思邈與虎撐
舊時,行醫賣藥之人終日走街串巷登門看病,但他們卻不會吆喝“看病呀”之類的話,因為要避諱給人送去晦氣。但為了達到知會人們的目的,他們通常是手搖一種類似銅圈的響鈴,肩挑藥囊(簍),身負藥箱,懸掛葫蘆,以示“報與君知,懸壺濟世”。而他們手中所執之鈴叫作“虎撐”,又稱“虎銜”、“串鈴”和“報君知”,是鄉間市廛的一種廣告形式。
“虎撐”有大有小,小可繞指,大可拿捏。通體鑄有八卦圖飾,寓意去兇辟邪,趨利向善。鈴的外側留有半指的開逢,中間有兩顆鐵彈丸。使用時將食指和中指插入響鈴的中間,借助拇指的力量,手掌快速晃動,手臂配合上下浮動,使中間的彈丸來回撞擊,以此發出清脆震耳的響聲,隨走隨搖,在寂靜的山村或戈壁村寨,聲音亦可傳出很遠。
說到“虎撐”的起源,還有一則傳說。相傳藥王孫思邈晚年于山中采藥時,忽現一頭猛虎,猛虎將孫思邈的去路攔住,情急之下孫思邈欲以挑草藥的長扁擔自衛,誰曾想這頭猛虎竟俯身跪地,并未向他撲來,正當孫思邈松下一口氣時,猛虎突然張開血盆大口,以一種似人般可憐的眼神望著孫思邈,孫思邈心懷好奇緩步移向猛虎,出于職業的敏感性,他發現在猛虎的喉嚨中卡有異物,細看之下是一根碩大的獸骨。醫者仁心,孫思邈欲助猛虎取出這塊骨頭,但畜生畢竟是畜生,難保它獸性大發突然閉嘴,為保手臂不被咬斷,孫思邈摘下藥擔子上的銅圈,放進虎口撐住老虎的上下顎。將手從銅環中央穿過,伸進虎口中迅速地拔出骨頭并麻利地在傷口上敷抹藥膏。待手術完畢后,孫思邈在虎口中取出銅圈,正當要轉身離去時,猛虎長嘯,向孫思邈點頭搖尾,以示感激。虎有靈性,不復危害人畜,感恩孫思邈,從此為其守護杏林,并充當藥王的坐騎。藥王死后,此虎哀嘯三日,不知去向。
搖鈴高度有講究
藥王的奇遇一經傳出后,江湖上的行醫之人紛紛效仿孫思邈,銅圈便成了外出采藥、看病時的必備之物,后人逐漸將銅圈改成手搖的響器,作為行醫的標志,一來可以彰顯自己是藥王的弟子,自己的醫術也如藥王孫思邈一般高明,他們每到一地,便手持搖鈴(虎撐)挨家挨戶,邊晃邊走,一聽到“虎撐”的聲響,當地百姓便知是看病賣藥的來了。二來是因孫思邈以銅圈救虎而未被吃掉,故行醫之人上山采藥時便把它作為傍身之物,借著虎威行走天下。
行醫之人在使用虎撐時也是要講規矩的,身份、醫術一般的游醫,只可將虎撐放在胸前搖動;醫術較高且稍有名氣的游醫則可將虎撐與肩齊平搖動;至于醫術高明、醫德高尚的游醫則可將虎撐高高舉過頭頂搖動,以象征其身份。但不管在什么位置,凡經藥店門口皆不可搖動虎撐,因為藥店里都供奉有藥王孫思邈的牌位,倘若搖動,便有欺師滅祖之嫌,藥店的人可將游醫的虎撐與藥籃一并沒收,同時還必須向孫思邈的牌位進香賠禮。
截、頂、串與賤、驗、便
與儒醫群體著書立說不同,鈴醫每天都要肩背行醫布囊,不避寒暑地游走鄉間為百姓診治疾病,因此民間又稱他們為“草澤醫”、“走方醫”。清代著名醫藥學家趙學敏編撰了第一部總結鈴醫經驗的著作,名曰《串雅》。“串雅”的意思就是讓搖串鈴的鈴醫登上大雅之堂。他首先總結了鈴醫的截、頂、串的3種治療方法(即汗、吐、下三法),并給予高度評階,認為鈴醫的治療方法是“操技最神,而奏效甚捷”。又把鈴醫的用藥特點歸納為賤、驗、便三字訣:“一曰賤,藥物不取貴也;二曰驗,以下咽即能祛病也;三曰便,山林僻邑倉促即有。”鈴醫治病多重視經驗,常無理法方藥、君臣佐使之理可尋,用藥簡單,追求快捷,擅用單方,一般不會有服藥幾十劑、幾個月的治病風格,也極少用補藥。
從古至今,作為平民的老百姓總是遠遠多于皇親貴族,他們沒有經濟條件去坐堂醫那兒配好藥,而同樣出身民間的鈴醫正是迎合了這一需求,因此,鈴醫廣受鄉民的歡迎。
關于“搖鈴行醫”的記載還有許多,百年老號宏濟堂的創始人樂鏡宇的祖上——樂良才也有在北京走街串巷、行醫賣藥的故事。歷史上也有許多有名的“鈴醫”,李時珍的祖父即為鈴醫,李時珍的父親李言聞繼承了其祖父衣缽,一生都在為所謂“下九流’的百姓治病。再有如民國時期,廣東澄海樟東一帶常有“走鄉醫”穿街過巷的例子。
總的說來,鈴醫多是無名之輩,在經驗傳播上幾乎都是師徒口授及身傳,并需要個人的實踐體悟,很多經驗性的技術無法用文字準確全面地表述,所以長期以來都被認為是雕蟲小技,得不到正統醫家的承認。但細看中國醫學史,就會發現其實鈴醫在千百年來中醫的傳承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是我國民間醫學的傳承體系之一。可以說,鈴醫對中醫學的發生、發展以及成熟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我國實行執業醫師制度的今天,鈴醫已幾近消失,但作為民間醫學流派,我們不要忘記,其為炎黃子孫的繁衍生息做出過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