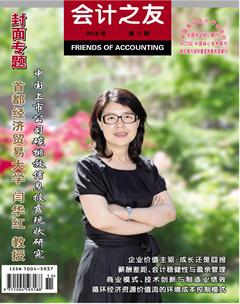“金科產”融合發展的現實困境與金融支持效率研究
李華軍
【摘 要】 進一步推動“金科產”的融合發展需要突破金融發展與實體經濟不協調、財政金融協調機制不完善、金融資本供給結構性問題等現實困境的制約。文章運用DEA方法對廣東省“金科產”融合發展過程的金融支持效率進行實證分析,研究表明金融支持效率受到經濟環境、金融資本形態、技術創新階段等因素的影響,并呈現不同程度問題。因此,深化金融領域供給側改革服務實體經濟和創新驅動,在關注金融資本總量供給的同時,更應當關注不同金融資本形態在技術創新階段各環節配置結構的優化、使用效率的提升以及規模的合理性。
【關鍵詞】 “金科產”; 融合發展; 現實困境; 效率評價
【中圖分類號】 F83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18)11-0103-06
引 言
“十二五”以來,受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形勢的持續影響,我國經濟進入“三期疊加”發展階段,為此國家和地方政府出臺一系列政策和改革措施,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轉型升級。其中一項重要措施就是加強金融領域供給側改革,服務實體經濟和創新驅動戰略發展,促進金融、科技和產業(以下簡稱“金科產”)的融合發展。近年來,廣東省先后出臺科技金融創新以及金融改革服務創新驅動和實體經濟等發展的系列政策措施,深入推進“金科產”的融合發展,取得了較好成效。當前,廣東省“金科產”的進一步融合發展面臨金融發展與實體經濟不協調、金融總量與發展質量不平衡等現實困境和挑戰,融合發展過程存在資源配置結構、使用管理效率以及規模效益等問題,存在過度依賴政策性金融資本投入、以商業銀行為主體的市場化金融體系嵌入程度不高的缺陷。為此,本研究基于金融資本供給視角,在分析廣東省“金科產”融合深化發展的現實困境基礎上,研究不同金融資本形態在“金科產”融合發展過程的支持效率差異,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文獻回顧
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經驗表明,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的快速發展主要受益于成熟的資本市場和以銀行為主體的市場金融體系。為此,國外關于金融資本與創新驅動發展的研究大多圍繞銀行、風險投資和資本市場展開。在我國,受制于銀行體系和資本市場的發展程度,政府在推動金融支持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為載體的創新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近年來,隨著創新驅動經濟的發展,越來越多的學者從資本形態、區域、產業等視角對“金科產”融合發展進行了相關研究。李俊霞等[ 1 ]、烏蘭等[ 2 ]在研究科技金融支持我國高新技術企業產業發展的效率中發現市場科技金融相對于公共科技金融具有更高的效率,在提升方面還具有較大空間;金浩等[ 3 ]、國際昌和葉蜀君[ 4 ]、薛曄等[ 5 ]從區域角度研究了科技金融的促進作用、支持效率及差異或影響因素;許一帆和楊有振[ 6 ]從產業角度以新能源為例研究了金融的支持效率及影響因素。上述研究對于“金科產”融合發展的相關問題研究提供了一定的借鑒。
廣東省“金科產”融合發展的實踐探索較早,取得了一定成效,部分學者開展了研究,但總體來說理論研究滯后于實踐探索。劉佳寧[ 7 ]、羅莉萍和徐文俊[ 8 ]從理論與案例分析角度對廣東省“金科產”融合發展的現狀、問題進行了分析,并提出相關對策建議;鄧彥和盧鵬光[ 9 ]以上市公司為例,考查了廣東省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金融支持效率,研究表明整體支持效率不高,但呈上升趨勢;劉湘云和吳文洋[ 10 ]以廣東省高新技術產業為例,通過實證分析考查了在廣東省“金科產”融合發展過程中科技金融政策的作用路徑和效果;江湧等[ 11 ]運用DEA方法研究了廣東省的科技金融政策作用效果,研究結果表明金融的高投入不一定能有效提高科技產出,而優化科技金融內部結構才能實現科技、金融的協調發展。
綜合國內外相關研究現狀,發現當前圍繞金融與科技、產業融合發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科技金融視角考查與產業發展或技術創新的關系以及支持效率等,而基于不同金融資本投入形態的效率差異以及結合技術創新兩階段的差異進行比較分析和研究的較少。另外,當前廣東省“金科產”融合發展的理論研究滯后于實踐探索,少數融合發展效率方面的定量評價結果也與現實情況不盡符合。為此,基于以上文獻梳理和分析,本研究在借鑒相關學者研究成果基礎上,運用DEA分析方法,結合廣東省“金科產”融合發展的現實困境,構建不同的評價模型進行比較分析,試圖更為客觀地評價“金科產”融合發展視角下金融資本的支持效率及差異。
二、廣東省“金科產”融合發展的現實困境
(一)金融發展與實體經濟不協調
近年來,廣東省金融業快速發展,金融總量不斷擴大,增加值占GDP比重均從2012年的5.7%逐年增長到2016年的8.2%,在推動實體經濟發展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對比GDP增長速度、工業增加值增長速度以及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結構變動趨勢,廣東省金融業的發展同全國一樣,面臨與實體經濟不協調的問題(見表1、圖1)。在廣東省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各項比重結構中,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占比、短期貸款占比、中長期貸款占比分別由2014年的65.81%、23.12%、37.91%下降到2017年(截至11月)的54.83%、18.60%、32.33%。其中:非金融企業及機關團體貸款占比逐年下降趨勢明顯,中長期貸款占比的下降趨勢在2017年有所扭轉。上述數據間接反映了當前廣東省“金科產”進一步融合發展的現實困境。
(二)銀行面臨效益企穩與風險控制雙重挑戰
近年來,金融領域推進供給側改革提升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在“三去一降一補”等方面取得顯著成效,但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如銀行業風險加大、利潤下降、轉型乏力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與世界銀行于2017年12 月聯合發布的關于“中國金融部門評估規劃”(FSAP)更新評估核心成果報告中就提示了銀行資本金、資產質量以及金融創新等方面的風險。從在廣東省業務市場較為成熟度的四大國有銀行和其他商業銀行所在的上市公司有關財務狀況來看,“十二五”以來,受國際金融危機和經濟形勢的持續影響,以及互聯網金融的沖擊,銀行業的盈利能力、持續發展能力以及資產質量狀況整體下滑趨勢明顯(見表2)。當前金融領域供給側改革過程中,盈利能力的企穩、資產質量的提升、經營風險的防控,也是銀行業自身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問題。而在創新科技金融服務、深化“金科產”融合發展過程中,面對“輕資產、高風險、高投入”的科技型企業和創新型企業,銀行業(尤其是非國有商業銀行)的效益企穩和風險防控更具挑戰。
(三)金融資本供給結構性問題明顯
當前,戰略性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作為創新驅動戰略實施的重要抓手,在產業培育和發展過程中面臨以銀行為主體的金融資源配置結構性問題較多,如金融資本供給與產業發展階段、產業特征結構以及企業類型、企業生命周期、企業需求特點等不匹配,同時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金融資源的供給水平也參差不齊。2015年底珠三角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成立,這一政策及平臺有力地推動了大批優質創新資源和金融資源集聚當地,促進了這些地區“金科產”的融合發展。但是,積極效應發揮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科技金融發展水平的兩極分化——更多的創新資源集結在珠三角,并與之形成良性互動發展;粵東西北地區原本經濟、金融發展程度不高,更加無法吸引和獲得優質的創新資源和豐富的金融資源。同時,受地方財力限制,粵東西北地區地方政府出臺的科技金融政策相關獎補資金額度、風險補償力度都遠低于珠三角地市,這也將影響各創新主體參與“金科產”融合發展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四)政策引導效應尚未充分發揮
近年來,廣東省政府先后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著力建立健全科技金融服務體系,政府財政投入等政策性金融的投入力度不斷加大,引導和吸引了包括銀行、擔保公司、風投公司等市場資本的融入。但是,從“金科產”的實踐來看,還存在以下問題不同程度地制約“金科產”的進一步融合發展。一是政策體系尚未健全,部分運作模式還處于試點和探索階段,如國家前兩年開始試點的“投貸聯動”政策及模式;二是受制于珠三角與粵東西北地區經濟發展程度和金融發展水平的差異,部分政策得不到執行,或示范、引導效應有限;三是財政金融政策之間缺乏統籌協調,“金科產”融合發展的財政投入及獎補機制、銀政企的風險共擔機制和利益分配機制還不完善,如風險補償率、補償期限等條件無法滿足銀行的風控考核要求,制約了銀行等金融主體的參與積極性。
三、廣東省“金科產”融合發展的效率評價
(一)研究界定及指標設計
1.金融資本形態界定及投入指標設計
鑒于現有學者對金融資本不同形態在“金科產”融合發展的作用效果差異研究較少以及廣東省“金科產”融合發展的現實困境,本研究基于金融供給視角,結合“金科產”融合發展過程與技術創新階段特征,將金融資本形態界定為廣義金融資本和狹義金融資本兩種形態:一是廣義金融資本形態,主要指“金科產”融合發展過程與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相關的金融總供給,本研究以政策性金融和市場化金融兩個要素為代表考查廣義金融資本投入總量在“金科產”融合發展過程的支持效率(政策性金融資源投入用政府的“財政科技支出”數據代表,“財政科技支出”包括了所有創新主體在創新活動投入中的政府資金部分;市場化金融資源投入用非金融機構“中長期貸款”來代表,“中長期貸款”主要用于研究開發以及推動科技成果產業化相關的生產經營或生產性投資活動,在“科技貸款”指標數據的缺失下該指標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是狹義金融資本形態,主要指“金科產”融合發展過程中廣義金融資本集中投入到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產業化相關過程的具體形態,包括人、財、物等,本研究以R&D;經費內部支出、R&D;人員全時當量和新產品開發費為代表考查狹義金融資本投入總量在“金科產”融合發展過程中的支持效率。
2.技術創新階段界定及產出指標設計
遵循大多數學者的研究思路及成果,將技術創新全過程分為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兩個階段。在具體產出指標設計上,結合“金科產”融合發展的機理,有所區別。一是在考查技術創新全過程的產出指標設計上,參照多數學者思路,以技術合同成交額、專利授權量、新產品銷售收入和高技術產品產值為代表;二是在考查技術創新過程中的科技成果轉化階段,根據“金科產”融合發展的政策,設計目標最終為推動新興產業和高技術產業發展,為此產出指標以新產品銷售收入和高技術產品產值為代表。
3.投入產出滯后期假定
從現有研究來看在考查技術創新效率問題上,多數學者根據技術創新兩階段的特征將投入產出滯后期假定為兩年;但在考查科技金融支持效率上,多數學者將投入產出滯后期假定為1年,使得最終評價結果與現實情況不吻合。本研究基于技術創新階段特征以及“金科產”融合發展過程,將投入產出滯后期假定為兩年。
(二)模型構建及研究設計說明
根據上述研究界定及指標設計,結合廣東省“金科產”融合發展現狀及困境,構建4個模型進行比較分析,具體模型以及研究設計思路如表3所示。
(三)數據來源與數據處理
本研究以廣東省為例,采用廣東省2001—2016年“金科產”融合發展的相關投入產出數據(數據來源于廣東統計年鑒、廣東科技年鑒、中國統計年鑒以及中國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根據投入產出的滯后期假定,分別選擇對應的投入數據和產出數據。同時,為剔除價格因素影響,以2001年為基期,對投入指標(R&D;人員全時當量除外)用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進行平減,對產出指標用(專利授權量除外)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進行平減。在模型構建、指標選擇和數據處理基礎上,利用Deap2.1軟件對廣東“金科產”融合發展過程不同金融資本形態在不同創新階段的支持效率狀況進行比較分析。
(四)結果分析
1.模型Ⅰ和Ⅱ結果對比分析(表4)
(1)整體效率分析。2001—2014年,模型Ⅰ和模型Ⅱ的14年綜合效率均值分別為0.975和0.945,說明狹義金融資本在“金科產”融合發展的整體支持效率還算可以;模型Ⅰ和模型Ⅱ近5年綜合效率均值分別為0.931和0.871,與14年均值差距明顯,均呈規模報酬遞減狀態,說明近5年效率不理想,主要原因為金融經濟危機的影響;從近5年綜合效率的變化趨勢來看,都經歷了下降到上升的過程,說明政府在投入總量和配置結構方面采取了一些優化調整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
(2)階段效率分析。從14年和近5年整體情況來看,模型Ⅰ的綜合效率、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均值均高于模型Ⅱ,說明狹義金融資本在技術創新全過程的支持效率高于科技成果轉化階段,間接說明在科技創新階段的支持效率高于科技成果轉化階段。
(3)效率內部結構分析。從14年整體情況來看,模型Ⅰ的技術效率均值高于規模效率均值,而模型Ⅱ相反,說明狹義金融資本在科技創新階段的配置結構優于科技成果轉化階段;從近5年來看,模型Ⅱ技術效率均值與規模效率均值差距較大,說明狹義金融資本在科技成果轉化階段配置結構問題相對科技創新階段較為突出。
2.模型Ⅲ和Ⅳ結果對比分析(表5)
(1)整體效率分析。2001—2014年,模型Ⅲ和模型Ⅳ14年綜合效率均值分別為0.960和0.941,說明廣義金融資本在“金科產”融合發展的整體支持效率較好;模型Ⅲ和模型Ⅳ近5年綜合效率均值分別為0.903和0.875,與14年均值差距明顯,規模報酬狀況不穩地,說明受金融經濟危機影響近5年效率也不理想;從近5年綜合效率的變化趨勢來看,經歷了“上升—下降—上升”的過程,說明政府在投入總量和配置結構方面不斷優化調整,取得了一定成效。
(2)階段效率分析。從14年和近5年整體情況來看,模型Ⅲ的綜合效率、技術效率均值均高于模型Ⅳ,說明狹義金融資本在技術創新全過程的支持效率高于科技成果轉化階段,間接說明在科技創新階段的支持效率高于科技成果轉化階段。
(3)效率內部結構分析。從14年整體情況來看,模型Ⅲ和模型Ⅳ的技術效率均值大部分低于規模效率均值,說明廣義金融資本在科技創新兩階段的配置結構存在問題;從近5年來看,模型Ⅳ技術效率均值與規模效率均值差距較大,說明廣義金融資本在科技成果轉化階段配置結構問題相對科技創新階段更為突出。
3.模型Ⅰ和Ⅲ結果對比分析
(1)整體效率分析。2001—2014年,模型Ⅰ和模型Ⅲ14年綜合效率均值分別為0.975和0.960,說明狹義金融資本在“金科產”融合發展過程整個技術創新階段的整體支持效率優于廣義金融資本,但優勢并不十分明顯;近5年與14年整體狀況差距問題二者都很明顯。
(2)效率內部結構分析。從14年整體情況尤其是近5年情況來看,模型Ⅰ的技術效率優于規模效率,模型Ⅲ則相反,說明在整個技術創新階段,廣義金融資本支持效率的問題主要在于配置結構方面,而狹義金融資本則在投入規模方面。
4.模型Ⅱ和Ⅳ結果對比分析
(1)整體效率分析。從14年整體情況和近5年情況來看,狹義金融資本在“金科產”融合發展過程科技成果轉化階段的整體支持效率略高于廣義金融資本,但差距不明顯;近5年與14年整體狀況差距問題二者都很明顯。
(2)效率內部結構分析。相對于14年整體狀況,近5年模型Ⅱ和Ⅳ的技術效率均值與二者的規模效率均值差距明顯,說明近5年廣義金融資本和狹義金融資本在配置結構方面的問題相對突出。
四、結論及建議
本研究基于金融資本供給視角,通過構建不同模型比較分析廣東省“金科產”融合發展過程不同金融資本形態在不同階段的支持效率,盡管在指標選擇和數據來源上存在一定局限,但不影響整體結論。根據上述分析結果,得出以下基本結論以及相應的政策建議。
(一)基本結論
1.金融資本在“金科產”融合發展過程中的支持效率受經濟金融環境影響較大,2010—2014年,不論是狹義金融資本還是廣義金融資本,綜合效率都出現較大的問題。
2.狹義金融資本和廣義金融資本在技術創新整體過程(包括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階段)的支持效率較好,而在科技成果轉化階段的支持效率相對較差。
3.從近5年來看,狹義金融資本和廣義金融資本在技術創新整體過程中的效率結構存在不同程度問題:狹義金融資本規模效益問題較為明顯,廣義金融資本配置結構問題較為明顯。
4.從近5年來看,狹義金融資本在科技成果轉化階段的配置結構問題相對科技創新階段較為突出;廣義金融資本在科技成果轉化階段的配置結構問題相對科技創新階段更為明顯。
(二)政策建議
1.“金科產”融合發展過程金融資本的支持效率受經濟環境的影響較大,在當前經濟形勢下,需要深化金融供給側改革,尤其是要進一步引導市場化金融資本體系(如商業銀行等)服務實體經濟,創新驅動發展,強化資本鏈與創新鏈、產業鏈的協同與融合,促進金融經濟協調發展。
2.金融供給總量對于“金科產”融合發展的作用效果具有積極的影響,但并非越多越好。在當前經濟形勢下,在加大金融供給總量的同時,要注意規模的合理性以及配置、使用的有效性,避免出現規模報酬遞減現象。
3.金融供給自身結構以及在技術創新階段的配置結構對“金科產”融合發展的支持效率差異明顯。為此,需要合理優化金融資本不同形態的投入結構以及創新階段的配置結果。總體來說:狹義金融資本投入更加要注重規模效率問題,并適當加大在科技成果轉化階段的投入;廣義金融資本投入更加注重配置結構問題,并適當加大在科技成果轉化階段的投入。
4.廣義金融資本供給在“金科產”融合發展過程注意結合不同技術創新階段,優化投入模式和配置結構。在科技創新階段,注重加強政策性金融投入和結構優化(如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開發研究的結構)的同時,引導市場化金融資源進入;在科技成果轉化階段,適當進行政府干預調控金融資本服務實體經濟,注重以市場化金融為主導,以政策性金融為引導。
【參考文獻】
[1] 李俊霞,張哲,溫小霓.科技金融支持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實證研究:基于系統動力學方法[J].中國管理科學,2016,24(S1):751-757.
[2] 烏蘭,李寅龍,花蕊.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金融支持效率研究:基于DEA兩階段模型分析法[J].經濟研究參考,2016(67):63-68.
[3] 金浩,李瑞晶,李媛媛.科技金融投入、高新技術產業發展與產業結構優化:基于省際面板數據PVAR模型的實證研究[J].工業技術經濟,2017,36(7):42-48.
[4] 國際昌,葉蜀君.欠發達地區科技金融資源配置風險偏好分析:以轉型城市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為例[J].宏觀經濟研究,2017(6):44-53,82.
[5] 薛曄,藺琦珠,高曉艷.中國科技金融發展效率測算及影響因素分析[J].科技進步與對策,2017,34(7):109-116.
[6] 許一帆,楊有振.山西省能源產業的金融支持效率研究:基于DEA模型[J].會計之友,2016(8):14-17.
[7] 劉佳寧.科技、金融、產業“三融合”的廣東實踐[J].南方經濟,2015(9):112-116.
[8] 羅莉萍,徐文俊.關于廣東科技、產業、金融融合創新發展的思考[J].科技管理研究,2016,36(19):81-85.
[9] 鄧彥,盧鵬光.戰略性新興產業金融支持效率研究:以廣東省為例[J].會計之友,2016(24):71-74.
[10] 劉湘云,吳文洋.基于高新技術產業的科技金融政策作用路徑與效果評價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7,37(18):23-28.
[11] 江湧,閆曉旭,劉佐菁,等.基于DEA模型的科技金融投入產出相對效率分析:以廣東省為例[J].科技管理研究,2017(3):6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