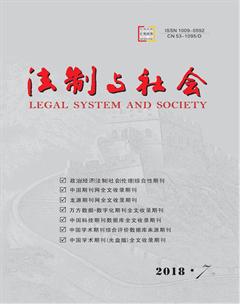知假買假的懲罰性賠償規則適用
張琦
摘 要 自《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行開始,懲罰性賠償規則對知假買假者的適用在理論與實務界引起廣泛爭議。私法領域的懲罰性賠償規則有其特殊性,違約的懲罰性賠償與侵權的懲罰性賠償適用條件亦不相同。知假買假者適用懲罰性賠償條款,首先需要具備消費者地位,其關鍵在于對生活消費目的的理解。同時對于欺詐行為,應當側重經營者主觀惡性的判斷。知假買假者適用懲罰性賠償利于維護市場秩序,但要堅持比例原則。
關鍵詞 知假買假 消費者 懲罰性賠償規則
中圖分類號:D920.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7.226
一、我國現行立法中的懲罰性賠償規則
懲罰性賠償常見于公法領域的規范當中,《消費者權益保護法》(以下稱消法)原四十九條是我國首次在私法領域對其作出規范。懲罰性賠償的私法適用是對民法平等原則的挑戰,它不僅使這種賠償方式具有制裁性,打破了民事主體之間平等的地位,也成了填補式賠償之外的另一種賠償方式。在消法等私法規范中規定懲罰性賠償是私法公法化的表現,首先,可以起到預防與警示的作用,提示生產經營者規范與誠信經營;其次,可以打擊經營者欺詐與假冒偽劣等不良市場行為;再者,利于更好的彌補消費者的損失,懲罰性賠償并未免除違約責任與損害賠償責任,而是使消費者在此基礎上獲得更多賠償。
私法領域的懲罰性賠償從性質上分兩類:違約的懲罰性賠償和侵權的懲罰性賠償。前者請求賠償的依據是合同關系,后者則是侵權關系。不僅如此,違約的懲罰性賠償具有法定性,而侵權的懲罰性賠償具有自由裁量性。所以,消法五十五條的兩款內容,可以分別看做是違約的懲罰性賠償與侵權的懲罰性賠償。
根據法律的規定,適用違約的懲罰性賠償具體要求:第一,經營者有違約行為,生產、銷售的產品或者提供的服務有缺陷,經營者欺詐;第二,消費者有損失,應從廣義上理解為信賴利益的損失,如為締約而支付的對價;第三經營者主觀故意,有明知產品有缺陷,卻不向消費者如實告知,依然繼續售賣;最后,消費者的損失與經營者違約之間有因果關系,即消費者支付合理對價以后不可能獲得預期使用價值。而適用侵權的懲罰性賠償條件的特別之處有二:第一,要求經營者有侵權行為,該行為具有侵害消費者人身財產權益的現實危險;第二,給消費者造成損害,且要達到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嚴重損害的程度。
二、實務中的爭議
實務中,不同的法院對待知假買假者態度不盡相同。在羅某與中山市古鎮海洲波記購物廣場產品責任糾紛一案二審中,廣東省中山市中院駁回了上訴人羅某請求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理由是其在短期內多次向不同銷售者購買商品,并起訴要求價款十倍的賠償的行為,不是為生活消費的需要而是為營利目的。 同年,廣州市中院在吳某與廣東永旺天河城商業城有限公司產品責任糾紛案的二審判決中,卻明確表示不予采納以被上訴人多次購買同類產品主張被上訴人知情因此不構成欺詐的主張; 同案在廣東省高院再審裁定中則明確了,銷售者欺騙購買者是單方行為,購買者是否知悉欺詐并不影響欺詐行為的構成。
重慶市高院在《關于審理消費者權益保護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中明確表示“明知商品或服務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的人是消費者。但是,明知商品或服務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的人請求獲得懲罰性賠償的,因有違誠信原則,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四川省南充市中院在熊某與南充市興平藥品零售連鎖有限公司儀隴第156加盟店產品銷售者責任糾紛一案 的二審判決中,也貫徹了這種觀點,認為買假索賠不符合誠實信用原則,故而不支持熊某適用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
知假買假者在產品責任糾紛訴訟中身份尷尬,裁判結果迥然的原因主要有二:第一,知假買假者是否是受消法保護的消費者;第二,對于知假買假者銷售者是否構成欺詐,以及買假索賠與誠信原則的關系。
三、懲罰性賠償規則的適用
(一)消費者的界定
文義上,消費者是指為了生產和生活需要而消耗物質財富的人。法律上,美國《布萊克法律詞典》認為消費者是“購買、使用、持有、處理產品或服務的個人”;俄羅斯聯邦消法認為消費者是“使用、取得、定做或者具有使用、取得、定做商品(工作、勞務)的意圖以提供個人生活需要的公民”。二者都對消費行為做了拆分和列舉,明確了消費者是自然人,而后者加入了消費意圖的限制。
我國消法并未給出明確的定義,但在第二條規定:“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者是本法的保護對象。因此,在我國消費者身份主要有兩個構成要件:其一,是消費目的,應當是生活消費需要;其二,是消費行為,具體包括購買、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務。同時,我國在消法第三條接著規定了經營者是“為消費者提供其生產、銷售的商品或者提供服務”的人。通過體系解釋的方法,我們能夠看出,我國法律對消費者的認定是從兩個方面作出的,從正面規定了兩個構成要件,在反面則表明消費者是與經營者相對應的概念。從最高法公布的23號指導案例中,我們也能夠看出這樣的意味,該判決書寫明:“消費者是相對于銷售者和生產者的概念。只要在市場交易中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是為了個人、家庭生活需要,而不是為了生產經營活動或者職業活動需要的,就應當認定為‘為生活消費需要的消費者。”
對于消費目的的判斷,有觀點認為,買假的目的在于索賠,其目的在牟利,并非生活消費,因此知假買假者不是消費者。 對此觀點筆者持保留意見。
首先,消費目的是一項主觀標準,在司法實踐中具有相當調查難度,因為消費目的不應當做狹義的認定,認為只有符合消費客體預期使用用途的消費才是消費,比如購買衣服并非只有穿了才能認為是對衣服的消費行為,購買衣服用作陳列或撕毀做抹布亦應當認為是消費行為,也符合消費目的;以所謂的“經驗法則”作為判斷標準,在實務中無異于擴大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圍,固守生活消費目的之證明,在程序上亦不具有實現價值。
其次,消費目的與消費動機不應當做同義理解。消費目的是消費主體發揮消費客體價值的預設,而消費動機是消費行為的內在動力。有生活消費的目的并不必然排斥一個牟利的動機。牟利與營利不同,不應視訴訟索賠的維權行為為營利活動。相反,高額的賠償能夠激勵消費者監督不良經營行為,更好地維護市場秩序。
最后,實務中對于生活消費目的的判斷,往往借助于類似行為,如前文所提到的羅某與中山市古鎮海洲波記購物廣場產品責任糾紛案,裁判理由中正是提到了羅某之前的索賠行為,認為其是職業打假,否定了其生活消費的目的。訴訟法中重要的證據規則是關聯性規則,司法活動中應當對類似行為持謹慎態度,法院以知假買假者先前行為證明其在具體個案中不具有生活消費目的,缺乏邏輯上的合理性。
(二)欺詐行為的判斷
知假買假者區別于一般消費者之處在于“知”,他們對產品質量存在的問題是知情的,并沒有因為生產、銷售者的掩飾隱瞞乃至欺騙的行為而產生錯誤的認識。《民法總則》第一百四十八條規定:“一方以欺詐手段,使對方在違背真實意思的情況下實施民事法律行為”,表明民法上的欺詐要求欺詐手段與錯誤的民事法律行為的實施之間具有因果關系。因此從傳統民法對欺詐的構成角度來看,知假買假者因為事先的知情而不具備欺詐要求的因果關系這一要件,所以生產、銷售者對其不構成欺詐。重慶市高院就采取了這一觀點。而這種說法的弊端在于:其一,肯定知假買假者的消費者地位卻排斥其適用懲罰性賠償條款,有對消費者分類之嫌;其二,消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民法上的欺詐并不相同。
消法從性質上看屬于經濟法。而經濟法是具有獨立地位的部門法,它的調整對象是經濟關系,而民法調整的是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關系。相較民法,經濟法更多了一份行政性。消法自然在立法的目的、宗旨上,調整法律關系的手段方式上,有別于民法。民法在法律效果上追求的是恢復原狀,賠償與損失掛鉤,超出損失的賠償構成不當得利。消法則不然,同是作為市場主體的消費者與經營者之間存在現實地位上的不平等,隨著生產的社會化和專業化,民法無法解決信息偏在等問題。賦予消費者懲罰性賠償,正是對消費者進行的傾斜保護,鼓勵其與不法生產、經營者積極對抗。其實質上體現的是國家干預,目的在于反欺詐。
從消法的立法目的出發,應當將民法上的欺詐與消法上的欺詐行為區別對待。對消法中欺詐的因果關系應當做擴大理解,經營者的掩飾隱瞞、虛假說明行為,只要對社會一般消費者具有誤導作用,足以使一般消費者陷入錯誤認識即可,而不要求每一個現實具體的消費者都要因此作出錯誤的意思表示。因為這一組法律關系不僅是合同買賣雙方間的關系,也是消費者與經營者間的關系。作為經營者,其面向的對象具有不特定性、廣泛性和普遍性。所以,不法經營者對知假買假者應當構成消法上的欺詐,適用第五十五條的懲罰性賠償規則。
現實中,許多裁判理由提到了知假買假者違反了誠實信用原則。所謂誠實信用,要求“人們在市場活動中講求信用,恪守諾言、誠實不欺,在不損害他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 知假買假者違反誠信原則,筆者認為,僅存在于行為人借用消費者名義,通過欺詐行為侵害經營者,使其財產權益受損的行為的情況中。 這種情況下行為人不具有消費者身份,僅是單方欺騙經營者的欺詐行為人。但是本文中討論的知假買假者,是具備消費者身份的。其主觀上的“惡意”僅存在于“知情”上。換言之,知假買假行為是對不法生產、經營者先前欺詐行為的對抗。消費者作為個體,維權能力低下,維權成本過高,對假冒偽劣商品的鑒別能力不足。知假買假者的維權打假行為即便有慣性,相對普通消費者維權經驗豐富,但是面對經營者,在經濟關系中依然是弱者。因此,不能將消費者對不誠信經營者欺壓的反抗,視為不誠信。
買假索賠類案件反映出我國立法的不完善,執法的不嚴格,但根本的原因在于假冒偽劣等不法生產與經營行為屢禁不止。對知假買假者適用懲罰性賠償,利于激發民眾積極維權、對抗不誠信經營的熱情。而知假買假者是特定歷史與經濟條件下的產物,必定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立法與司法的不斷完善而逐步退出歷史舞臺。我們應當在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的前提下,規范其維權行為,使之對市場發揮更加充分的監督作用。同時,懲罰性賠償規則也是把雙刃劍,在彌補消費者損失的同時,生產經營者可能借由其優勢地位將賠償風險二次轉嫁給消費者。因此,在知假買假者適用懲罰性賠償規則時,要重視對經營者懲罰的適當性,注重比例原則。
注釋:
(2016)粵20民終1314號判決.
(2016)粵01民終784號判決.
(2016)粵民申3796、3797號裁定.
(2017)川13民終2757號判決.
梁慧星.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49條的解釋與適用.人民法院報.2001年3月29日,第三版.
梁慧星.誠實信用原則與漏洞補充.法學研究.1994(2).22.
楊立新.消費欺詐行為及侵權責任的承擔.清華法學.2016(4).7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