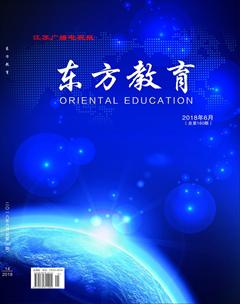生命起源的探索
張凱
摘要:此文撇開了一般資料中的觀點:生命的起源與老子的“道生一…”不搭界,相反,確認生命的起源恰恰契合老子《道德經》里:“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觀點。此文還別致地將生命初期的蛋白質分成了:優,中,劣三類。文章中引用唯物辯證法指出:內因為主,外因為輔,是生命進化的本質屬性,從而,跨越了生命起源的鴻溝。文章中還將一般資料里的“超級酶”,重新命名為“傾向性功能酶”;并推理:老子“道生一…”的觀點與達爾文的進化論是相得益彰的。
關鍵詞:生命;起源;探索;老子;道生一
就生命起源這個命題,我思考了很久,有的時候覺著這個命題太重了,想不動,解不了,放棄吧,可是在靜下來的時候,又常常想起它。幾種推測,幾種解答,被思考,被否定,幾經周折,在思考有了較為清晰輪廓的時候,我想起,也該了解一下,相關資料上的說法了吧。
搞研究,并且想有所創新的人,一般會有個通行的做法,那就是:當一個課題擺在你面前的時候,你不能著急地先去看已有的資料,那樣,會被資料中的思路帶進去,出不來;出來后,又難以有新的思路突破。
于是,我審時度勢地旁征博引地搜索了相關的資料,從而,更加堅定了自己的探索方向和理念。在研究過程中,又巧合地收看了紀錄片《史前大碰撞》,《人類的起源》等等,視頻的演繹。這樣,我在已有立場的基礎上,對收集到的信息,進行了細致的審理和再思考。
生命起源于外星球?應該是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隨機的碰撞,一種是人為的安排。
地球生命,是由其它星球傳來的兩種說法,被科學家否定過太多次了。我也是不贊成地球生命的,外來說的。那也許是在想,回避對地球生命起源的探索吧!盡管我們對生命起源的探索,已經越來越接近真相了,可是,仍然有人愿意相信,地球生命的外來說法。
地球生命外來說法的原因:一是,在地球上,暫時還沒有找到,可以產生有機生命體的確鑿證據;二是,有人不想承認,人類是從膠泥一樣的蛋白質中產生的。他們寧愿意承認,人類的起源,在聊天的時候,聽上去能更華麗一點。
一定要說地球生命是外來的話,那么,我們還可以再追問一句,外星生命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另外,人們對于生命的認識,也應該有更新的觀念了。也就是說,生命存活的新發現,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破了人們對生命認識的原有觀念。生命不僅僅能夠在零攝氏度,上下浮動幾十度的情況下存活;在有氧氣,有水,有陽光,有碳水化合物,有穩定氣壓的情況下存活。科學家們還不斷發現,生命存活的新狀態。在沒有陽光的情況下,生命能存活;在海底1000米以下,溫度在零上200-500攝氏度的情況下,仍然有蝦蟹能夠存活著;它們不靠氧氣,不靠陽光,靠甲烷氣,靠硫化物存活著,當然還有浮游生物可以食用;但是,它們身體上的蛋白質,抗住了高溫的考驗,甚至連浮游生物都抗住了高溫的考驗。這打破了人們對于動物蛋白質,在零上100攝氏度的情況下,不會存活的認知。甚至,科學家們還發現了,在火星上,沒有氧氣的情況下,也有生命體存活的現象。
地球生命外來說站不住腳,那么,生命的上帝創造說又如何呢?筆者從來就沒有認同過這種說辭。筆者以下給出的論述,自然回答了這個問題。
中國古人,老子,在2500年前的《道德經》里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觀點。筆者的探索和思考,恰巧與老子的這個觀點相契合。這是筆者的莫大欣慰和自豪,也是筆者繼續深入地探索這一課題的信心來源。中國古代的老子,是智慧的,是偉大的,怎么說他偉大,都不過分。在那個科技文明不發達的古代,能夠撥開重重迷霧,提出這樣的生命起源理論,其困難程度,其準確程度,其歷久彌新程度,其高度的哲學概括程度,乃至于其超然世外的至高境界,都是難以想象的。當然,我們現在探索這個課題,同樣,也是要撥開層層迷霧的。
自從“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理論問世以來,后人對它的解釋,就紛紛擾擾,始終沒有統一過。“道”有人說它是指,生命進化的全過程;也有人說它是指,規律性。至于其中的一,二,三,有人說“一”是指氣,“二”有指陰陽,“三”指萬物——這大體上是道家的說法。還有其它智者的解讀,就不再一一列舉。這很有點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各說個話的意思。我對老子的這句話,給出了自己的分析,供大家參考:
“道生一”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其中的“道”又指的是什么呢?“道”怎么能生一呢?一般認為:天道酬勤是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是道;太陽從東邊出來,從西邊落下是道;水往低處流也是道。但是,“道生一”的道,主要指的是:自然規律性。
如果,地球上的自然現象是沒有規律性的,地表溫度,今天是零下100攝氏度,明天是零上500攝氏度;今天大氣中含氧量是50%,明天大氣中含氧量是5%;大氣層,臭氧層,也不穩定,無規律;海水和淡水的狀態也不穩定,整個地球表層沒有一個穩定的,有規律的狀態。這也就談不上有“道”了,“道生一”也就更談不上了。
正是因為有了地球自然現象的穩定性,規律性;其中包括穩定的水,雨,陽光照射,大氣層,含氧量,溫度,濕度,季風,臭氧層,淡水熱泉;還包括穩定的潮起潮落,洋流移動;穩定的海水升溫降溫,穩定的海水化學物理性能,再有海底熱泉的穩定支持;等等。這些穩定的自然現象,在經歷了千年,萬年的物理化學變化后,產生了地球上最原始的蛋白質——這種無機生命現象。這也就是,所謂的“道生一”了。
在大自然中,能夠自然產生蛋白質。這一點,科學界幾乎是沒有爭議的。我只是認為,蛋白質的產生,契合了中國老子的“道生一”的觀點。而蛋白質是一切有機生命體的源頭,科學界對此大多也是贊同的。
有人認為,生命是從海洋中產生的。科學家在太平洋底的熱泉附近,發現了大量的嗜熱微生物;在32億年前海底的火山沉積物里,發現了有絲狀生命體的遺跡,從而證明了生命起源于熱泉,也就是海底熱泉說。
僅僅依賴隨機過程,從氨基酸到蛋白質,進而,產生有機生命體,有人質疑這樣的概率太小了,不可能。就像給猴子一臺打字機,它能夠打印出一部《紅樓夢》;也如同,有一堆零件,被風一吹,變成了一輛汽車。
66億年前,銀河系發生了大爆炸。46億年前,形成了太陽系。38億年前,地球出現原始的地殼。這個時間,與多數月球表面的巖石年齡是一致的,也就是說,這是可驗證的結論。
澳大利亞西部瓦拉伍那35億年前,巖石標本里發現了微生物遺跡,被認為,那可能是地球上最早的生命證據。
我們當今科學家所發現的,最早的,最有代表性的類人骨化石,是非洲的露西,距今已有320萬年了。
科學家一般認可,從無機生命到有機生命體,是生命起源,難以跨越的鴻溝。
我們現在還不能確切地了解,有機生命體誕生時,地球上的環境狀況。我們甚至不能確定,有機生命體誕生在,從前遙遠的那個時間段。不能了解,也就不能復制,不能證明當時由蛋白質轉化為有機生命體的過程。但是,這個過程肯定是跨過去了,而且,極其有可能的是,不只一次地跨過去了。
我們可能還不得不承認一個殘酷的現實,那就是,地球上誕生生命的溫床,隨著大自然的變遷,早已不復存在了。
然而,地球上生命的起源,所有動物的起源,以及人類的起源,只能依賴于地球自身。它一定契合,中國老子的觀點:“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由蛋白質催化出有機生命體,這是在地球上沒有生命的億萬年中,在各種條件完備的情況下,進行的。這些條件包括溫度,含氧量,進化了的蛋白質,水,能量以及進化了無數次的酶等等,等等。
海洋里能孕育生命,這一點,我是贊成的。不僅僅是因為海洋里有藻類,有玻璃海綿,有魚類;就從許多陸地動物離不開鹽來看,似乎也能佐證此說法。但是,我始終說服不了自己,生命只起源于海洋?陸地上就不能孕育生命了嗎?有那么多高高的森林,厚厚的枯枝落葉,積累了那么多的果實;又有水,陽光,氧氣,溫度,各種物理化學變化的催促著;還有火山,淡水溫泉,陸地上的條件,那一點比海洋差?
至于孕育有機生命體的具體地點,我判斷是:海底熱泉和陸地上的淡水溫泉附近,都是有可能性。那么,陸地上有陸地的生命進化史,海洋里有海洋的生命進化史。它們的原理是一樣的,時機也是相近的,是相輔相成的。
我們還要確認一個自然現象的邏輯性,那就是初級動物的出現,一定晚于它們的食物的出現。要不是這個順序的話,那么,動物出現以后,它們吃什么?從廣義上說,是食物的出現,也為以它們為食的動物的出現,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在這里還有一個形式性的問題,需要申明清楚一下。生命是由蛋白質轉化成一種,簡單的有機生命體;還是由多種含有細微差別的蛋白質,在多種含有細微差別的酶協助下,轉化成了多種簡單的有機生命體呢?
答案是:就其地球自然現實的豐富性,以及其細微差別的豐富性來說,生命的轉化也應該是具有豐富性的。這種生命種類的豐富性,只需要細微的差別性,就能夠實現,而這種細微的差別性,正是地球上自然存在的。
蛋白質的差別性,來自于環境的差別性,比如說:高溫,低溫,森林,高原,盆地,沼澤等分別影響了的蛋白質;在海里則有溫度差異的,海藻有無的差異的,有各種化學含量差異的,海水深淺差異的,等等,各種溫泉附近所形成的蛋白質。蛋白質在表面上看,幾乎是一樣的,但是,其機理需求,活力程度,壽命長短,新陳代謝能力,是有著千差萬別的。特別是,這些蛋白質,在高含氧量所造成的環境中,逐年累月的影響下,有一個類別,萌發出了更高級的生命需求。這一類蛋白質,她們自身活力旺盛,又迫不及待地需求進化,于是乎,脫穎而出了。她們在區域性“酶”的協助下,義無反顧地走上了這一進化的不歸路。唯物辯證法里有:“內因為主,外因為輔,”的發展規律。這一規律性適合于,對這一進化現象的理論性詮釋。擴展開來說,生物的進化,幾乎全部適合于,這一理論性的詮釋。
這種區域性的“酶”,它們是在獲取了區域性環境中的,特有的化學的,物理的,日積月累的,各種條件下形成的。這些條件的作用,使得“酶”是帶有傾向性的。這種帶有傾向性的“酶”,遇到了等待進化的蛋白質,將有助于,進化出來的有機生命體,有傾向地依賴于當地的環境而生存下去。
這種“傾向性功能酶”,到不是說它是有意識的。這也是大自然在經歷了有和無,發展和改良以后,熏陶形成的,是有針對性的,是有時效性的。當蛋白質的進化有需求的時候,在這個需求的量足夠大,需求的時間又足夠長的時候,大自然就衍生出一種“酶”,以此來協助蛋白質滿足這種需求。這樣一來就實現了,大自然的階段性平衡。這種“酶”的功能性,是在特定的情況下,協助蛋白質,來構建她們自身的功能器官。這聽起來似乎有一點玄乎,但實際上,只是在蛋白質需求建立功能器官時,“傾向性功能酶”起到了一點點的協助作用而已。這是大自然自己選擇的,是進化需求的選擇。我在紀錄片中聽到了這樣一句話,叫做:畢竟需求是進化之母。
這種“酶”,在一般資料中,把它稱之為超級酶;而我認為,稱之為“傾向性功能酶”更貼切一些。
蛋白質,簡單的無機生命,在各種條件的協助下,進化成了,簡單的有機生命體。再經歷一段時間以后,有機生命體的進化,又進入了下一個,更高層級的循環。從而,把簡單的有機生命體,轉化為更復雜的有機生命體。
人們期盼著在考古活動中能夠了解到,遠古的這一演變過程。但是,這一期盼,也許是極難實現的。因為,這一過程太脆弱了,一是在微觀世界里進行的,二是整個時間也許不算太長。所以,極難留下什么證據,能讓當今的科學家,在經歷了幾百萬年,甚至是幾十億年以后,還能夠查找到,她們的演變真相。
我們知道,單細胞微生物只有四分一毫米大小,但是,她已經具備了呼吸,排泄,運動,生殖和調節等,象征著有機生命體的,全部特征了。那么,我們所要探索的,最初始的,有機生命體的體量,她一定比單細胞微生物的體量,還要小許多。
我思量著有人,把這一地球歷史上,產生有機生命體的最重要一環,形容為跨越鴻溝,是合適的。人們對未知世界,總是會有著模糊性和恐懼性的。由蛋白質進化為具有新陳代謝功能的,有遺傳本領的初期動物,是一個了不起的跨越。
然而,對于地球的自然變化能力來說,由蛋白質進化出有機生命體,也不是什么特別的事情,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只是,我們對此百思不得其解,還想一步跨過去,那就困難了。
我的設想,和許許多多關心此課題的朋友的設想,基本上是一致的。大自然跨過這個鴻溝,也是分了好幾步,才完成的。
首先,是在各種待變的條件都具備的情況下,特別是在“傾向性功能酶”已經進化成功以后。最迫切要解決的是,蛋白質的分離。在大自然的活動中,蛋白質的合成一定是有差別性的。在高含氧的影響下,在進化若干年的情況下,更擴大了這個差別性,使得蛋白質中有了優,中,劣之分。那么,極有可能是,部分優秀蛋白質的小集團,在運動中,掙脫了其它不優秀的,蛋白質的粘連,脫穎而出了;或者是其它因素促成了蛋白質的分離。進而,在“傾向性功能酶”的協助下,分離了的蛋白質產生了膜,膜是用來提供自我保護的,其性質如同動物的皮膚。(實際上,蛋白質的分離,已經困擾了人們許多年,許多年。在那個極其微觀的世界里,很難想像出,還會有其它什么更科學的理由,能讓微小的蛋白質,實現自然的分離。)第二步,被膜包裹的優秀蛋白質,有延長自身活力的內在需求,在“傾向性功能酶”的協助下,鞏固了這一需求,逐漸具備了新陳代謝的功能。換一句話說,有新陳代謝功能的被膜包裹的蛋白質延長了生命,其它沒有新陳代謝功能的,則被淘汰了。被膜包裹的蛋白質并非都是球體的,因為,球體的蛋白質,其中心部分不易被置換,失去了生存能力。于是,形狀各異的,微小的,被膜包裹的蛋白質出現了。她們有的像蝎子,有的像蛇,有的像玻璃海綿等等,等等,種類繁若星辰。這樣,被膜包裹的蛋白質就能夠增加了與外界接觸的機會,有利于蛋白質的置換和接受新的能量。第三步,這些形狀各異的蛋白質,她們與外界接觸的機會是不同的,新陳代謝就有了先后,體內的蛋白質也就有了不平衡。這樣一來,就需求建立一個中樞系統,來協調新陳代謝功能的一致性。當這種內在的需求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傾向性功能酶”協助完成了,這個中樞調節系統的建立。第四步,那些形態各異的蛋白質,在她們的生存過程中,由于某個肢體的連接部位出現了萎縮,而造成了肢體的斷裂分離;分離出來的蛋白質仍有著膜,以及新陳代謝和中樞協調功能,以及原有母體的一切特征。更有可能的是,優秀蛋白質的肢體,自己掙脫了不夠優秀的母體,進而,形成了裂變和再生。這樣一來,就誕生了地球上最初的有機生命體。完成了中國老子觀點中的:“一生二”。
地球上,有機生命體的誕生,也許還有其它幾個過渡性環節。人們不要指望一次性構建起,所有的,從蛋白質到有機生命體的全部要素;要循序漸進地進行,一個環節,一個環節的進化。我們還要有耐心地承認,這其中的每個環節,大約都需要經歷幾十天,幾年,或者更長的時間,有需求就有進化的嗎。這種進化,是自然的需求,是高含氧量,多食物存在,各種環境適宜,等客觀現實所發出的綜合信息,給托舉出來的。這個進化過程,不管有多少個環節,在進化原理上幾乎都是一樣的。
在這里,還必須回答一下,最初的有機生命體誕生時,她們的食物是什么?我分析,她們的食物是:大量的,微小的,性能中等的,沒有進化能力的,蛋白質的個體;或許,還有其它的,難以想像的食物。應該說,實在是太難以想像了,在那個微觀世界里,比四分之一毫米還小的蛋白質的有機生命體,還能夠依靠其他什么食物,來完成新陳代謝。
那些最原始的有機生命體,她們像沒有起飛的蜜蜂圍繞在蜂巢周圍一樣,圍繞在蛋白質的周圍。等到有機生命體進化了幾千代,幾萬代以后,才逐漸遠離她們誕生的溫床遠一點。
有機生命體誕生的時期,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就是:高含氧量。正是由于,存在了高含氧量,才促進了其它相關條件的變化成熟,促成了有機生命體的誕生。當時,陸地上以及海洋里的含氧量,也許是現在的“兩”倍左右。這個當時的高含氧量,似乎已經被現在的科學家所證實了。
我們不要認為,這種“傾向性功能酶”是一個偶然現象。我認為這是一種必然現象。我們不要小瞧大自然的自我完善,平衡,發展,前進的能力。同時,我們也不要高估這個“傾向性功能酶”的作用,它只是起到了,不可或缺的協助而已,只是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
以上給出了,地球上誕生最初有機生命體的過程。至于,這個過程需要多長時間?不得而知;也許幾百年,或者幾千年。但是,我總認為,時間不會太長。因為,時間太長的話,大自然的綜合條件會發生變化,那時,或許就不再適合,孕育出新生命了。
大自然的本領就是:優勝劣汰,適者生存,何況還有那么多的“傾向性功能酶”,在等待著協助和鞏固新事物的誕生……
有的時候,地球上的某種現象,就是因為重復的次數太少,所以,我們很難研究它。比如說:沙塵暴,龍卷風,海嘯,地震,日蝕月蝕等等,最初,人們對它們的出現,也不甚了解,驚恐萬分。后來,就是因為它們重復的次數太多了,人們才漸漸弄明白了,它們是怎么一回事。
生命的起源這種現象,在地球上重復的次數太少了,40億年間,也許只有那么幾次,又是在那么遙遠的,基本上留不下任何痕跡的一瞬間。所以,我們對它的研究,就顯得無從下手。
人們當下,要想在實驗室里,再現有機生命體誕生這一過程,其中當時的環境狀態,就是無從復制的,還有,最難得到的是那個,“傾向功能性酶”。因為,那個“傾向性功能酶”,是在經歷了千萬年,地球上生命荒蕪的情況下,才衍生而來的,是有時效性的,是極難復制的。
地球產生有機生命體的條件,只有在地球上沒有有機生命體的千年,萬年,甚至更長時間的情況下,才會發生。當地球上有了較為豐富的有機生命體以后,這種催化有機生命體的條件將逐漸退去,直至完全喪失。隨之而來的是:有機生命體的進化,再進化,再再進化……
就生命起源的復雜性,漸進性,漫長性而言,它還能幫助我們回答另一個,困擾了人們幾千年的哲學問題,那就是:在自然界中,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我的回答,肯定是:先有雞,后有蛋。因為,就雞本身而言,它屬于鳥類的家族。它同樣也需要經歷,從原始有機生命體開始進化,再到嘴,胃,大腦,心臟等等,分步驟的進化過程。動物們最先期的,最原始的繁殖方式,大多是以裂變為主的。在動物的家族中,只有當進化達到一定程度以后,或許是幾千代幾萬代以后,才逐漸有了卵生和胎生之分。這樣,在鳥類動物的進化過程中,是不會先有個蛋,再孵化出鳥來的。所以,從事物發展的邏輯上講:先有鳥,后有蛋,這一點,是必須的。
就“生命起源的探索”這個議題,研究它,要走過的歷程是:先從理論上取得突破,逐漸獲得共識;而后,在考古研究中,一步一步地接近真相。最后,在大數據以及算機的協助下,由近及遠地,還原遠古的地理狀態;以實現,在實驗室里能夠復制生命起源,這一終極目標。
筆者,僅僅就生命起源這個課題,自我感覺與祖國先哲老子的觀點幸運地相契合了,進而試圖解釋了老子觀點中的:“道生一,一生二”,而已。我分析,當時老子寫下這一句話的時候,他也不能確定一二三,究竟各代表什么?但是,有一點,他是可以確定的,那就是:有了“道”,就一定能產生“一”,這個所有動物的源頭。而后,才有了能夠運動,呼吸,新陳代謝,遺傳和繁殖功能的動物;才有了繁若星辰的,陸地和海洋的動物世界,也就是有了二和三了。
有人認為,達爾文的進化論,和中國老子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是兩回事;我認為是一回事。只是,達爾文在他的宏篇巨著中,更側重地解釋了物種的進化歷程;而老子則是高度哲學地闡述了生命的起源和蔓延。兩者之間互為印證,互為支持,起到了中西合璧的效果,進而增加了,人們對那個遙遠的,生命起源的認可程度。
以上論述或有不當之處,謹供有同樣興趣的朋友,增加了一個新的討論空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