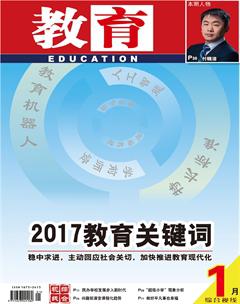孔子之風度
梅光迪

凡歷史上偉大人物,其年代愈遠,則其真相愈難明,因之其聲譽亦時升時降。宗教祖師如釋迦、耶穌,學派祖師如老子、孔予、蘇格拉底、柏拉圖,固然。即至各國之民族英雄,及其大文人大藝術家,亦莫不然。蓋以時代風尚有異,個人學識有限,遂生見仁見智之別,其是非得失,皆須由時代與個人負責,而與偉大人物之本身,固無涉也。
自吾先圣之歿,迄今二千五百余年。其歿后本身之遭遇,雖遞經波折,然未有今日之甚者。晉人尚老莊,故有以老莊賢于孔子者。南北朝好佛,故有以佛賢于孔子者。然未嘗如今日之乳臭兒,皆挾其一知半解之舶來學說,以挪揄孔子,掊擊孔子者。此非僅孔子一人之厄運,實亦吾民族文化之厄運也。孔子今日之遭逢厄運,其原因甚多。而末學者誤解孔子之風采態心,亦其原因之一。孔子固不似平原君之“翩翩為濁世佳公子”,亦不似王衍之“神姿高澈如瑤林瓊樹,為風塵外物”。然亦不似后世道學家之矯激拘墟不近人情。試就論語所記孔子飲食起居待人接物之處,細心領會,則吾人向日眼中道學化之孔子,當可湔除不少。而藹然可親意味深長之孔予乃活現于吾人想象中。
論語中為今人所詬病者,莫如鄉黨一篇,實則此篇所記瑣屑事跡最能曲曲傳出孔子之品行。如衣食固今人所重視者也。衣食要素有二。一為求其適于衛生,一為求其合于審美觀念。孔子于此二者,固嘗考之極精矣。食之方面,則“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而,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矣,“割不正不食”者。以肉質構造有定,割不合法,則其味減,此烹飪家常識。至如“不多食,祭肉不出三日”,亦皆符于衛生原則。衣之方面,則“緇衣羔裘,素衣麂裘,黃衣狐裘”,夫顏色配合適宜。稍知服裝意義者,莫不奉為第一信條。試問今人以衛生與審美觀念自夸者,其能于上舉數端一一實踐之乎。
孔子以多藝聞于當時,其于音樂,尤用力勤而興味深,如“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雖古今中外大音樂家,以音樂為其第二生命者,其沈酣亦不能過是也,其語魯太師樂,及別韶武之高下,非深通其藝者,不能言之。是孔子非但大音樂欣賞家,亦大音樂批評家也。且除欣賞批評之外,又能樂器數種,如擊罄于衛,學琴于師襄,復次則能歌、能射、能御。古代教育,本在養成此種既能。然未必人人能如孔子之精也。后世士人,除“讀死書”外,絕少其他技能,習音樂者鮮,習各種發展體育之技能者尤鮮,今則受西化之指示,樂歌列為初等課程,足球、網球、游泳,亦頗行于時。然大多數仍草率從事。國人體格之孱贏,猶如昔也。其桀黠者,則志在學校或國際競賽,以為弋名沽利之具,不又與孔子游于藝之旨,大相徑庭乎。且孔子尚武,尤尚武以御外侮者也。故其言日:“戰陣無勇,非孝也。”“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又觀于陳人之忘國恥而深惡之日:“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之青年,徒以呼口號、貼標語為收復失地之武器,而于校中軍事訓練則視若具文,況冀其荷戈遠征,與仇人相見于沙場之上乎。
惟孔子除有最深之道德修養外,更富于藝術興味,故其發于外者,不為矜嚴局踏之道學家,而為雍容大雅之君子。故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鄉黨一篇,所記其與諸侯大夫周旋進退之狀,可謂形容盡致,寫生妙筆矣。驟視之,則孔子似一老于世故面面俱到之中朝大官;細審之,則知其視禮儀為人群之必需品,須內外如一。而后人與人可相安無事。社會之秩序,人生之意味,皆可藉以維持。故曰:“禮者,所以情貌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飾之所以喻內也。”法家如韓非子,亦知禮之真意矣。孔子學說雖嚴尊卑上下之分,然此為人群全部之組織而言,至其個人交際固純然超出分位思想而實行平等主義者也。“孔子于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于阼階。”其對于不識不知之“老百姓”,一副真誠和藹氣象,實可為現代少年,以改良社會為名于“老百姓”之一切生活習慣,動輒加以非笑干涉者之對癥藥也。吾國賢士大夫之美德中,最可稱述者,莫如鄉村生活。往往顯赫一時之達官貴人,一旦退休,則與田夫野老,把酒而話桑麻,脫盡仕宦習氣,故居鄉之法,著有成書,如不坐轎,不騎馬,每為長守條例。近代曾文正尤深知此意。吾國文學饒于山野氣味、漁樵之徒,與王公大人,其在文學上聲價之相差,何止倍蓰。凡此皆孔子居鄉法之遺澤,而與老莊之超然物外開隱逸之宗者,固無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