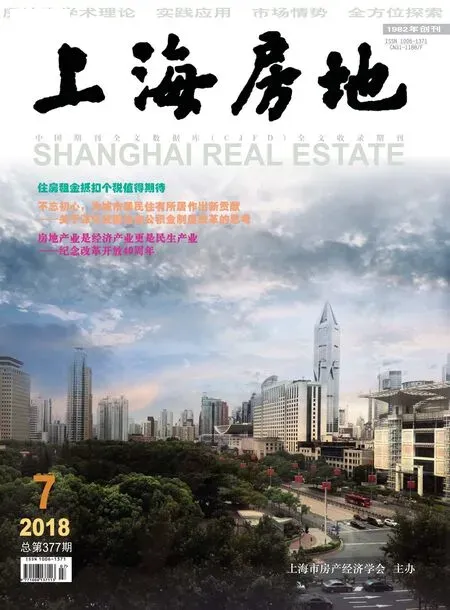上海住房保障政策發展分析
文/傅益人
在經歷了五十余年的發展后,上海已經逐步形成了由廉租住房、公共租賃住房、共有產權保障住房、征收安置住房所形成的“分層次、多渠道、成系統、全覆蓋”的四位一體住房保障體系。筆者通過對上海住房保障政策的梳理,總結了1949年以來上海住房保障政策的歷史沿革,并對當前所存在的一些問題,有針對性地提出了發展對策。
一、上海住房保障政策的發展歷史沿革
上海的住房保障政策形成主要有兩個階段,其一為1950年至1999年的福利分房階段,其二為2000年以來住房市場化背景下的保障房政策階段。
(一)1950年至1999年福利分房制度下的住房保障政策
長期以來,上海的住房政策主要是公房福利分配政策。在這一政策下,房屋的分配面向全市居民,主要是為解決住房困難家庭的住房問題。在這一階段中,住房保障制度主要呈現“低工資、低租金+補貼、實物配租”的特征,一般而言,可以將這一階段分為五個歷史時期。

首先是1950年至1956年,在這一時期,上海重點建設工人新村。例如,曹楊新村。曹楊新村建于1951年,是解放后全中國興建的第一個工人新村。此類新村主要是為了解決一些勞動模范、先進生產者的住房問題,同時為一些特困家庭提供住房。在這一時期,上海成立了由副市長牽頭、相關委辦局參與的市公房建設委員會,負責規劃、建設這批工人新村。第二個歷史時期是1957年至1965年。在這一時期,上海進行新區建設,所以要重點解決新區建設工人的住房問題,由此開發建設了包括彭浦新村、吳涇新村、張廟一條街等在內的一系列街坊公房,從而解決新區建設企業職工的住房問題。在這一時期,市房管局還協調解決了人均住房面積在1.2平方米以下困難家庭的住房問題。第三個歷史時期是1966年至1978年,在這一時期,上海成立了由市房管局、市城建局組成的住宅建設領導小組,建立了市區兩級住房供應體制,在靜安寺、康樂路等區域建設了23幢住宅樓,旨在解決人均居住面積小于 1.5 平方米住房困難家庭的住房問題。1979年至1986年是第四個歷史時期,在這一時期里,上海將國家建設與企業建設相結合,將住房建設與城市升級相結合,通過新建與挖潛,大大提高了全市住房建設的速度。在這一時期,上海成立了市住宅建設指揮部,通過政策支持,引導各單位發揮自主積極性,興建了包括長風、田林、上南等在內的一大批住宅區,旨在解決各系統單位自有員工的住房問題。1987至1999年是福利分房階段的最后一個歷史時期,這一時期,全市住房問題解決有了突破性進展,上海建立了“上海市解決居住特困戶聯席會議制度”,重點解決住房困難家庭的住房問題。在這一時期,共解決了110891戶住房困難家庭的住房問題,人均住房面積也由小于2平方米擴大到 4 平方米。此外,還頒布了《上海市住房公積金條例》。
(二)21世紀以來住房市場化背景下的住房保障制度
21世紀以來,上海不斷加快住房制度改革的步伐,確立了住房貨幣分配市場化改革的方向。這一階段主要分為三個歷史時期。

2000年至2005年,上海率先建立了廉租住房制度,旨在通過廉租住房解決住房保障問題。在這一時期,上海創新了保障模式,通過建立市區財政專項資金,初步形成了租金補貼為主、實物配租為輔的方式,解決了一部分居民的住房困難問題。2005年至2007年是這一階段的第二時期。在這一時期,上海進行了多渠道的探索,通過保障性住房、政策性住房和市場化住房三個方面解決群眾的住房問題。至此,上海初步形成了“以居住為主、市民消費為主、普通商品住房為主”的住房市場,并開始建立分層次、多渠道的住房保障體系。市場化階段的第三個時期是2007年至今。2007年8月,國務院印發《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的若干意見》,明確了住房保障工作是政府的重要職責。自此,上海市政府陸續出臺了《上海市人民政府貫徹國務院關于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若干意見的實施意見》、《上海市解決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難發展規劃(2008-2012年)》等政策文件,明確了以廉租住房、經濟適用住房為重點的住房保障政策體系。在這一階段,上海的住房保障體系基本形成。
二、上海住房保障政策的現狀
(一)住房保障范圍較小
盡管近年來上海不斷加大住房保障力度,改善住房困難家庭的居住條件,但政策覆蓋面仍然較小。截至“十二五”期末,上海累計只有11萬戶家庭享受廉租住房,只有6.6萬戶家庭簽約共有產權住房,全市共供應公共租賃住房8.77萬套,簽約出租7.45萬套,13.6萬戶家庭從中受益,征收安置住房搭橋供應42.76萬套,累計面積約3542.85萬平方米。然而,這些政策主要面向具有本市戶籍的住房困難家庭和來滬工作的高層次人才,而外來流動人口和中低收入群體中不符合住房困難標準的部分家庭,則不在此保障范圍內。從中不難看出,受制于房源供給數量,上海的住房保障范圍仍然較小。
(二)準入門檻有欠公平
目前,上海采取二次審核、二次公示的住房保障資格準入門檻制度。這一制度的引入大大提高了廉租住房、共有產權住房的審核嚴格程度,有效確保了廉租住房和共有產權住房資源能夠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通過對申請家庭的可支配收入、財產等進行審核,使一些希望借助廉租住房和共有產權住房獲益的家庭幻想破滅。然而,由于可支配收入和財產屬于家庭的私密信息,所以對于申請家庭經濟狀況的調查難以全面,在住房保障資格的審核方面難以做到全面準確地調查取證,因此仍可能存在不公平的現象。在退出機制方面,目前也存在一定的問題。由于缺乏強制性的行政處理措施,所以在廉租住房和共有產權住房的退出方面,無法強制不符合條件的家庭退出住房,無法使保障住房資源在第一時間被最需要的家庭所使用,容易造成資源浪費和不公平現象的發生。此外,在共有產權住房的房源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問題。隨著《上海市共有產權保障住房管理辦法》的頒布實施,相信2021年后,上海市的共有產權住房將陸續上市交易,從而使共有產權住房數量出現波動,如何保持穩定數量的共有產權住房也是未來需要研究的重點。
(三)住房保障的金融政策不健全
當前,上海保障性住房的金融政策相對比較匱乏,沒有形成有效的體系。保障性住房的開發、建設與運營大多是通過現有資金進行,沒有充分發揮金融政策的支持保障作用。通過對上海目前已有的保障性住房進行研究,不難發現,其在金融配套政策方面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問題:其一,已有的保障性住房金融配套大多被用在開發建設過程中,建成后的管理運營方面少有涉及。盡管商品住房的市場化運營已然形成體系,但保障性住房等的社會化運營仍在探索階段,包括資產抵押等在內的金融運營模式在上海尚未。其二,現有保障性住房的金融配套措施大多為銀行貸款,通過資產進行融資的案例還沒有出現。盡管上海已經出現房地產投資信托基金(REITs)的試點案例,但是這些案例大多為商業地產,還沒有金融機構為保障性住房開設資產融資項目。其三,缺乏全盤性的金融配套措施。對比上海與深圳等城市的保障性住房金融配套措施試點可以看出,上海在住房金融配套方面缺乏系統性的規劃。金融配套作為住房發展的必要工作,相信在未來的房地產市場中將會占到越來越多的權重,將會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然而,上海對于住房金融的試點較為保守,傾向于以點帶面地進行探索嘗試,對于商品住房的金融配套尚在試點過程之中,更遑論保障性住房,這對于保障性住房的未來開發、建設、運營殊為不利。
(四)管理模式陳舊落后
2016年以來,上海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住房保障工作,陸續出臺了相關的住房保障政策規章,旨在從源頭為保障性住房的管理提供法律依據。然而,盡管上海市在保障性住房的管理上進行了大量的有益嘗試,并不斷健全完善保障性住房的管理體系,但在實際操作方面,其管理方式與手段卻遠遠沒有跟上保障性住房市場的發展。在現實的保障性住房運營管理中,主要暴露出三個方面的問題:其一,管理機構冗余。當前市、區政府和主管部門、開發企業方面存在著多重管理的現象。在房源尋找、房源開發、房源運營等方面,市級層面有市級部門、機構、企業,區里有區屬部門、機構、企業,無法做到房源的有效匯集,甚至在部分區域還出現了市區爭搶房源的現象,這導致在保障房的運營過程中出現了多頭管理,無法實現資源的最佳適配。其二,在政策的配套和銜接上不協調。上海自2012年以來陸續出臺了《上海市經濟適用住房管理試行辦法》、《上海市共有產權保障住房管理辦法》等一系列政策規章,有些文件已然失效,而部分文件仍在發揮作用。在仍具有法律效用的文件中,由于保障性住房的種類不同,其申請人群的覆蓋面在銜接上仍存在一定的縫隙,使住房保障政策無法對住房困難家庭實現有效覆蓋,使部分家庭無法享受保障性住房所帶來的福利。其三,當前保障性住房的動態管理性較弱。由于對申請家庭經濟情況的調查缺乏動態性、精準性,對于經濟狀況有所改善的家庭享受保障性住房的狀況無法進行實時監控,使一些已經不符合保障性住房條件的家庭仍在享受實物配租和租金補貼,無法最大限度地發揮保障性住房政策的優勢,而由于住房資源的限制,一些更需要保障性住房的家庭卻無法享受政策帶來的福利。其四,上海在保障性住房的規劃方面缺乏前瞻性、系統性。目前,除《上海市住房發展“十三五”規劃》中明確提出了“十三五”期間保障性住房的建設要求外,上海缺少對未來十年、二十年中保障性住房的建設、運營、房源籌措、區域建設的明確規劃,也沒有從政策、法規、規章層面對保障性住房的建設和運營作出明確的規定,無法有效地鼓勵相關房地產開發企業參與到保障性住房的建設中。現有保障性住房的開發與建設完全依靠市屬國有企業進行,這對于保障性住房的未來發展十分不利。
三、上海住房保障政策的發展對策
通過對美國、新加坡等地保障性住房政策的研究,筆者基于上海的實際情況,對當前上海四位一體的保障性住房政策提出了一些發展對策,以期在未來能夠發揮出一定的作用。
(一)共有產權住房
共有產權房的管理重點在于對其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在不同的階段,其管理的要點也不盡相同。首先是對申請的管理。共有產權住房不同于租賃住房,其在申請后,涉及當事人的產權交易,因此,要對申請人的申請資格進行嚴格審核,防止不符合條件的家庭在其中“渾水摸魚”。同時,在申請階段,要幫助申請人合理評估自身的能力,避免出現無力購買或購房后無力還貸等一系列情況的發生。其次,要優化共有產權住房的運作形式,創新差異化的購買方式,因人而異、因地制宜地采取多種方式支持申請人群在自身條件允許的情況下購買住房。同時,要注重政策的銜接,對于由廉租住房、公共租賃房過渡到共有產權房的人群要進行平穩的政策過渡,保障這一人群住房狀況的穩定,逐步改善其住房條件。其三,要加強共有產權房交易的管理,要在分步交易中,明確產權的變化,及時進行更新,從而保證申請人的利益不受侵害。其四,要加強對共有產權房售后的管理,對于已經售出的共有產權房物業要一視同仁,繼續做好相關的物業服務,保證房屋能夠正常使用,使共有產權保障房政策能夠真正融入到房地產市場的發展中,成為上海房地產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
(二)廉租住房
廉租住房是住房保障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政府向住房困難家庭提供的主要政策福利。當前的廉租住房領域主要存在的是房屋的適配性、租賃人群的資格審核與租金動態調整等問題。因此,針對上述問題,筆者認為首先要加強對廉租住房人群的需求調研。要針對廉租住房人群的實際需要提供相關的實物配租或租金補貼。自上海2000年出臺廉租政策以來,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廉租人員狀況和廉租住房情況都發生了較大變化,政策的制定與使用應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調整與完善,避免出現租賃人群二次置換租賃等情況,最大限度地減少租賃人群的麻煩,發揮廉租政策的效益。其次,要加大對廉租住房人群經濟情況的調查,全面詳細地了解租賃人群的實際情況,對特別困難人群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對情況有所改善或者不再符合條件的人員,要進行政策過渡甚至取消政策。在這一方面,要加大全市民政、金融、房管等部門的協作力度,做到實時動態監管、動態調整。此外,要根據對租賃人群經濟情況的調查,及時調整相關的政策扶持力度,多數租賃人群在享受政策的情況下,經濟狀況會有所改善,要在堅持對這一部分人群進行經濟支持的情況下,逐步適度降低支持力度,鼓勵其自主發展經濟,同時將資金和房源向更需要的家庭和人群傾斜,使有限的房源和資金能夠發揮最大的效用。
(三)公共租賃房
公共租賃房是上海住房保障制度的又一大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說廉租住房是上海住房保障體系中的“托底資源”,那么公共租賃住房就是住房保障體系中的中流砥柱。隨著上海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越來越多的廉租住房人群在經歷了十余年的發展后,經濟情況有所改善,開始成為公共租賃住房人群,從而希望享受更好的住房條件。而公共租賃住房政策的發展與完善則重點要解決政策銜接與政策實施兩個方面的問題。首先是政策的銜接,在從廉租住房轉入公共租賃房與從公共租賃房轉入共有產權房這兩個方面,要注重政策的平穩過渡和有效銜接。確保政策的實施能夠全面有效地覆蓋需要人群,需要對全市住房困難人群有清晰的認識,能夠準確了解這部分人群的實際情況和在退出或轉換后的情況。政府有關部門應通力協作,建立相關數據庫,對數據庫人員進行動態的實時跟蹤,及時調整相關政策,及時對產生問題的家庭或人員進行精準定位、定向施策,使每個家庭或個人都能享受到政策的溫暖。其次,要充分注重政策的實施,要確保政策具有實施的基礎。因此,要確保市場上有充足的公共租賃房房源。當前,政府有關部門要在確保現有房源正常運營的同時,積極建設和籌措新的公共租賃房房源,將公共租賃房的建設納入上海的發展規劃中,尤其是在“五個中心”建設的關鍵時期,要確保來滬工作的各類人才都有房可住,使他們能夠踏實地工作生活。上海還要加大對公共租賃房運維的資金扶持,創新資金來源渠道,鼓勵社會各類主體參與到公共租賃房的建設與運營中,使公共租賃房政策能夠更好地實施。
(四)動遷安置房
隨著城市的發展進步,城市更新在所難免。在房屋征收方面,不僅要考慮到被征收房屋業主的經濟利益,還要考慮到全市房地產市場的穩定和健康發展。過去,在房屋征收過程中,市中心征收一套房,市郊補償三、四套房,但對于上海市民而言,往往會將市郊的房屋閑置,而沒有辦法使其投入到市場中。此外,還有部分人群希望通過房屋征收,獲得巨額收益。因此,政府主管部門應充分考慮到政策的平衡性和有效性,合理制定征收補償制度,使其發揮最大的效應。首先政府有關部門應對房屋的狀況和居住人員進行合理評估,采取現金或規范置換的形式,在保持市場穩定和置換房屋合理使用的情況下實現征收。其次,要明確房屋征收的本質屬性,不能帶有盈利或者福利色彩,使房屋真正回歸居住屬性。
隨著上海住房制度改革的不斷推進,上海市委、市政府積極順應國際大都市住房發展的有關規律,積極保障全市中低收入群體和來滬工作人員的住房基本權益,在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的同時,不斷提升居住生活品質,推進房地產市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未來隨著廉租住房、公共租賃住房、共有產權保障住房、征收安置住房“四位一體”住房保障體系的不斷完善,上海的保障性住房也必將發揮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