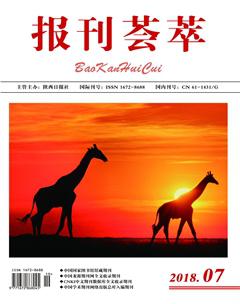王陽明“致良知”視角下醫患關系處理程序與方案研究
摘 要:緊張的醫患關系是目前醫療衛生領域最大的難題,現有體制并不能構建和諧的醫患關系。本文以新時代中國國情與醫改為導向,結合王陽明“致良知”思想,為醫患關系處理提出可行的思路與手段,促進社會外在規范和醫患個體內在道德的整合以及醫患雙方知行合一,有效提高醫患關系處理的效果。
關鍵詞:“致良知”;醫患關系處理;“知行合一”
六百多年前,王陽明提出了“致良知”的思想,其中的許多觀點和方法在當代仍然對道德教育地開展起到積極的指導作用。“致良知”思修所倡導的“良知”與醫學領域強調的“仁心”和醫道有諸多相似之處,這為該思想運用到醫療活動中奠定了基礎。在醫療活動中,日益激化的醫患關系正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當前醫患關系處理主要依靠制度和規范的約束來實現,而“致良知”思想提供的諸多道德教育方法與手段,從道德層面為處理醫患關系提供了另一種思路,醫患主體雙方個體層面的內在道德觀念轉變,比外在的制度和規范約束,更益于促進醫患關系的協調。因此,本研究對王陽明“致良知”學說中的道德教育觀點及其相關方法進行梳理,將其應用于處理醫患關系的過程中,提出可行的處理程序和方案,力求提高醫患關系處理的效果。
一、“致良知”中隱含的醫患關系處理方法資源
王陽明所提出的“致良知”思想是其心學理論的重要內容,該思想為醫患關系處理提供了許多方法資源。
(一)“良知”促進醫患關系外在規范與內在道德的整合
王陽明提出的“良知”概念實現了外在規范與個人內在意識的有效整合,擯棄了程、朱理學將“人心”完全與私和惡、公和善直接劃等號的觀點[1]。他認為人的“良知”是普遍公理與個體人心兩者的結合,其中前者包含了自然與社會兩方面的共同規律和道德規范,具有普適性、外在性和超越性等顯著特征,而后者則是王陽明重點強調的,也是其突破以往理學局限的重要手段,人的“良知”不管是表現為個人自省,還是個人的情感,都是人作為主體而獨特的態度,具有個體性、內在性和經驗性等顯著特性。他認為公理與人心只有在接觸客觀事物時,二者才有可能實現有效的統一[2],這在某種程度上減少了傳統觀念中的主觀成分,因而王陽明所提出的“致良知”學說將外在的社會道德規范與內在的社會個體道德兩者之間所具有復雜互動關系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了。
當前在處理醫患關系的過程中,醫患關系處理制度和機制起主要作用,而醫患自身的道德所起得到的作用則十分微小,依據王陽明“致良知”學說的觀點,外在道德規范與個人內在的道德觀念因為“良知”而實現了有效統一。“良知”的引入,使得醫患關系處理能夠發揮原有制度和機制外在作用的同時,也發動醫患內在的自我約束力,因而可以有效提升醫患關系處理的效果。
(二)“良知”推動醫患關系中主體的“知行合一”
王陽明提出的“良知”注重認知與實踐的統一,強調通過人的“知行合一”共同達到既定目標[3]。良知在自然情形下,通常能夠被作為主體的人所感知,但這種感知并不能避免人的作惡行為,唯有通過人后天“致知”的努力,人的良知才能夠被人自覺的實現。可以看出,“致良知”中的“致”包含了一定的不確定性,人有可能通過自身的覺悟實現符合“良知”的行為,也有可能不能感悟“良知”,從而為惡。“致”有兩種途徑:一是對人的良知進行擴充,人對良知的認識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該過程是需要持續加強和擴展的,人需要使之由粗到精,不斷完善;二是良知需要不斷實踐,“良知”只有通過人的實踐才能真正得以實現,這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朱熹等人對“知”的認識停留在認知層面的局限。
在醫患關系中,大部分醫生選擇了醫生這個職業,都有著救死扶傷的使命感,而患者在求醫過程中也是抱著對醫生的信任和感激之心而來,但這種“良知”若只是停留在意識層面,而并沒有通過人的自身努力或者實踐轉化成行為,那么必然也難以真正發揮作用,因而應引導醫患激發自身的“良知”,使之轉化為具體實踐,才能從根本上緩解醫患之間的矛盾。
(三)“致良知”為醫患“知行合一”指明方向
王陽明針對所提出的“致良知”目標,給出了實現該目標具體的路徑。他認為“致良知”首先需要個人確立志向,“立志”在人實現“良知”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需要人基于自身的主觀意愿,將社會所共同認可的道德規范作為目標,以提升自身的道德修養[4]。在立志之后,人還需要注重自身的知行合一,將所確立的意識層面的目標轉變為實實在在的具體行動。王陽明認為“良知”是整個“致良知”過程的起始點,同時也是該過程的終極目標,該過程就是要將個體自身固有的“良知”顯化為能夠被人所察覺和感知的“良知”,要達到這個目的,就需要人通過自身行為不斷實踐,知與行并不是先后順序的關系,而是相互包含和作用的關系。王陽明提出的“致良知”思想不再是以往只將道德修養放置于抽象層面的主體意識,而是依附于主體行為的道德實踐。
此外,王陽明還提出,“致良知”并不是獨立、單向的過程,而是往復循環、無休無止的過程,要求人們長期堅持該過程,不斷提升“致良知”的層次與水平[5]。顯然,“致良知”學說的這些觀點,為有效處理醫患關系在道德層面提供了具體可行的方案,醫患應當自覺確立“致良知”的目標,再通過就醫過程中的具體行為,將“良知”轉化為有助于改善醫患關系的具體活動,進而促進和諧醫患關系地構建。
二、基于王陽明“致良知”學說的醫患關系處理程序與方案
(一)促進醫患雙方個人目標與共同目標的整合
在王陽明所處的明代,個體與天理是一對激化的普遍矛盾,這是其“致良知”學說著重要解決的問題[6]。在當代的醫患關系之中,也存在著醫患之間日益激化的矛盾,醫患關系從根本上也是人的個體目標與社會共同目標兩者之間沖突,社會所制訂的一系列規范醫患關系的制度和機制對應的是“致良知”學說中的天理,也是社會共同認可的道德規范和要達成的目標,而醫患雙方各自的訴求和個人權利觀念則是個體層面的目標。隨著當代社會個人意識不斷加強,我國由以往集體價值觀主導的社會,正在轉向個人價值觀主導的社會,個人目標的實現已經成為他們日常生活主要追求的目標,因而在處理醫患關系的過程中也應當充分考慮到個人價值追求,對具體處理程序進行相應的調整。
(1)在醫患雙方的目標設定上,應當恰當地平衡醫院、醫護人員與患者之間關系。在全局層面上,必須要明確醫患關系之中既包含了社會和醫療機構的集體利益,同時也包含了醫護人員和患者的個人價值追求,應當確保醫患雙方各自正當的利益訴求能夠得到合理滿足,促進醫患雙方價值的共享,以確立醫患雙方共同的目標。從社會和醫院層面來看,其要實現的目標通常都比較長遠和宏觀,而從個人層面來看,其目標通常都更注重當下,且更加具體化,若要確保醫患關系的和諧,就必須對這兩種訴求進行充分的平衡。
(2)在針對醫患開展道德宣傳教育的過程中,應有意識地從道德層面將醫患雙方自個人層面的價值引向更高層次的社會責任。在進行醫學倫理道德觀和價值觀導入的過程中,應當盡可能的讓醫患雙方先從個體層面感知其具體意義,使之感受到這些道德觀和價值觀對個人的積極作用,促使他們自覺地去接受這樣的宣傳和教育。只有當醫患雙方都從根本上都轉變了態度,他們才會在醫患關系之中表現出親和的一面,而此時再對其加以恰當的引導,使其認知超越個體價值觀的局限,能夠積極參與到社會責任的擔當和共享之中。
(二)促進醫患雙方的知行合一
王陽明一生之中最大的貢獻就是將道德由抽象的觀念拓展到了具體的實踐,他將知行合一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上升到了全新的高度。對醫患關系的處理來說,醫患的“良知”也需要從認知層面轉化為醫患的實踐,而要實現該目標,需要對醫生和患者雙方開展科學的認識教育與實踐教育,并恰當處理好兩者之間的關系。
(1)明確知行在時間上的先后順序。當前在針對醫護人員和患者所開展的宣傳教育,主要是依照認識教育在先,而實踐教育在后的流程展開,但這種簡單的時序關系并不能充分反映知行之間所隱含的復雜關系,其主要原因在于:人的行動通常需要已經存在的意志給予預先的指導,但意志和行動又不存在這種誰先誰后的關系,因而在開展認知教育與實踐教育的過程中,二者應當是齊頭并進、互為補充的。
(2)把握知行在具體實現中的側重。“良知”主要由醫患雙方自身的觀念產生一定效應,但醫患雙方觀念上的轉變并不是“致良知”的極大目標,“良知”在醫患關系處理中是否發揮了作用,主要還是看“良知”有沒有轉化為醫患具體的行為。與此同時,這種觀念上的轉變很難通過人的觀察進行確認,觀念轉變的跡象只能通過醫患自身的行為外顯則能夠捕捉到,因而在處理醫患關系時所開展的宣傳教育重點必須放在實踐教育之中。
(3)促進知行在醫患關系中的轉化。雖然知與行在很大程度存在著相關關系,但這并不表示二者之間必然存在因果關系,或者說必然能夠實現由“知”到“行”的轉化,他們的轉變需要具備內在和外在兩個方面的條件。其中,外在條件主要指的是特定行為的難易度及其行為結果所產生的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具體到醫患關系處理而言,若醫患雙方在“良知”的影響下產生某種行為,并不要求醫護人員和患者投入較多的精力或者付出較多的成本,且能夠給對方帶來積極的影響,那么他們在內心里會相對容易轉化為具體的行為,而相反,若醫患的“良知”轉化為具體行為的條件不充分,那么醫患雙方的“良知”就有可能因此而隱藏起來。從這個意義上講,為醫患的“良知”轉化為具體行為創造有利的條件,是醫患關系處理中應當重點解決的問題。
三、結語
本研究在王陽明“致良知”哲學思想的視角下,對該思想有助于改善醫患關系的相關觀點及其方法資源進行了闡述,并將其應用到醫患關系處理之中,提出了具體的程序和方案,能夠對醫患關系處理效果的提升起到一定的參考作用。在醫患關系之中,醫患雙方既受到醫療機構和社會層面所制定的道德規范的約束,但同時也受到了自身個人主體思想和價值追求的影響,王陽明“致良知”學說所提出的外在規范與內在道德整合、知行合一等觀點,為制度、道德以及個人價值的統一,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與手段。
因此,在處理醫患關系的過程中,首先應當幫助醫患確立合理的目標,積極推動個人施救和就醫目標與社會和醫院的集體道德規范目標進行融合,促使醫患雙方個體層面的“良知”能夠及時地通過各自的行為轉化為符合社會道德規范和醫學倫理道德的相關行為,從而在根本上調和醫患二者之間日益激化的矛盾。
參考文獻:
[1]趙國利.致良知:王陽明哲學思想的正法眼藏[J].求索,2012(5):154-156.
[2]方國根.王陽明“致良知”道德哲學及其精神維度[J].學術界,2014(9):51-68.
[3]韓玉勝.王陽明“致良知”思想的倫理省察[J].廣西社會科學,2014(8):57-61.
[4]張艷婉,張元珍,喻明霞,等.醫患信任的倫理困境及解決策略[J].現代生物醫學進展,2017, 17(13):2569-2573.
[5]田浩,伍敏,肖慶,等.注重預防 妥善處理構建和諧醫患關系[J].中國衛生質量管理,2014,21(2):47-49.
[6]陸藝.我國古代處理醫患關系的優良醫德傳統分析[J].中國醫學倫理學,2015(4):514-516.
作者簡介:盧珊(1989—),女,貴州遵義人,碩士研究生。
課題項目:2017年度貴州省教育廳高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青年項目:王陽明“致良知”哲學思想視角下現代醫患關系的重建構想(課題編號:2017qn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