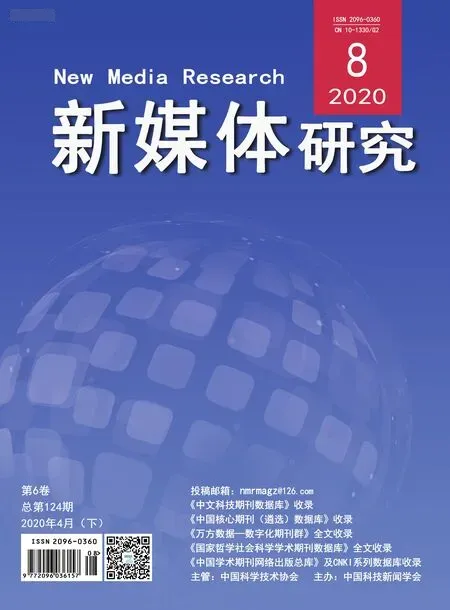知識付費
肖小麗
摘 要 內容的價值受到越來越多人的重視,知識付費成為原創內容盈利的新的出口。知識付費,簡單來說,就是為專業性、必需的知識買單,是知識共享的一種形態;除了傳統意義上的知識焦慮與消費升級因素外,付費的知識自身的內容特點、知識盈利模式的轉變也是主要的因素;但在其發展過程中,付費知識的質量與可靠性評估機制欠缺,平臺、生產者、受眾之間的矛盾依舊存在。
關鍵詞 知識付費;知識焦慮;盈利模式;評估機制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18)08-0072-02
知識付費,作為近幾年的熱點現象,從2016年開始逐漸開始壯大發展。縱觀知識付費的節點事件,2013年8月“羅輯思維”推出了“史上最無理”的付費會員制,探索出基于微信公眾號的新的內容盈利模式;2015年,愛奇藝采用會員差異化排播模式播出《太陽的后裔》,會員成為內容盈利的新渠道……從免費走向付費,不管是內容原創者還是平臺中介者,都在極大地發掘知識的價值。《中國分享經濟發展報2017》指出,2016年分享經濟市場中的“知識技能”領域達到了610億元的交易額,比2015年增長205%,使用人數約3億人[1]。得到、知乎、分答、喜馬拉雅更是成為知識付費領域的四面大旗。最近盛傳的網紅教授薛兆豐從北大離職,演講冠軍劉媛媛怒懟千聊等事件,將知識付費又再次刷屏于觀眾面前。2018年,注定又是知識付費的新風口。知識經濟不可小覷,對于知識付費這一熱點,我們也值得去思考它的來龍去脈以及發展中面臨的挑戰。
1 知識付費是何
知識付費,羅振宇本人更愿意把它定義為一種知識服務,這更加強調了知識的交付與服務特點。但從現今知識本身的共享性與商品性來看,知識付費可以看成是知識共享的付費形態,是它的一種迭代產品。那么什么又是知識的共享呢?學者王傳珍提出,知識共享,是把個人或機構分散、盈余的知識技能等智力資源在互聯網平臺上集中起來,通過免費或付費的形式分享給特定的個人或機構,最大限度利用全社會的智力資源[2]。解讀她的定義,我門分析出,現今所謂的知識,其共享實現的載體是互聯網平臺。而正是基于互聯網技術,如今的知識的可復制性共享性極大加強、公眾的版權意識減弱,知識在網絡上成為廉價的共享品,我們可以通過網絡上的任何渠道免費獲得自己想要的知識,內容生產者利益受不到保護,盜版嚴重,原創積極性不高;同時適應更為廣泛的傳播需要,知識深度和精度大大削弱,內容的碎片化、淺層化,一些知識門檻變低,變得通俗爛大街。
在某種意義上,知識付費并不是一種簡單的知識共享形式,雖然它在知識的傳播性上,具有共享的特性,但它不是一種免費的共享,打個比方,知識比作井水,知識共享就是每個人都可以從井里打到水,而知識付費則要花錢才允許打水。回顧知識共享的發展階段,我們可以看到,在知識共享1.0時期,主要以百科網站為代表(如百度百科、互動百科)進行知識信息的單向傳播,屬于靜態知識平臺;在知識共享2.0時期,主要以百度知道、知乎、新浪愛問等社區為代表,是以知識討論為核心的跟帖產品,實現傳受雙方的知識互動,屬于動態知識社區;而如今的知識共享3.0時期,涌現了大批知識付費平臺,如分答、得到、喜馬拉雅等內容社區,付費制成為這一階段的核心內容,知識付費時代正式來臨。但值得注意的是,知識付費與知識共享最大的不同在于,知識付費的內容知識,不具備易得性、免費性、共享性的特征,是需要付費而享用的高質量、專業性、獨享性的知識。
2 知識付費何起
2.1 知識焦慮,急需知識抓手
在信息爆炸的當下,我們自身的求知欲渴望更多非我的東西變成自我的東西。我們在快餐式消費的模式下,對知識碎片化、一目十行的接受方式,使得我們缺乏判斷、分析、運用知識的能力。這個時代每個人都在焦慮,焦慮時代變化太快,焦慮自己知識不夠,焦慮趕不上人家的成長速度,于是我們暗示自己:我還有許多知識需要學習掌握,我要不斷提升自己。可是在茫茫的知識大海里,我們又無法正確定位自己應該學的是什么,所以一旦有專門性的、分類化的、帶有總論性質的知識服務產品出現,我們就有可能為之付費。
2.2 消費觀念的轉變,發展性消費優先
我國中產階級群體不斷擴大,社會成員整體的收入水平不斷提高,在滿足了對衣食住行的消費欲望后,為了讓自己更加適應技多不壓身追求高精尖人才的社會變化,知識消費成為新的消費點,我們懂得用知識武裝自己,投資自己,豐富自己的知識面以及技能,發展自己。在生理需求層次滿足后,我們對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實現需求有了更強烈的消費愿望。我可以在知識付費平臺上實現對知識的獲取,與他人進行知識的交流探討,甚至可以自己成為內容生產的一份子,達到自我發展、自我實現的目的。
2.3 知識屬性轉變:獨特,優質,便捷
人們為什么會為知識付費,從知識本身的角度,也是大有原因。知識屬性從大而淺到小而精,從空泛到專業性凸顯,從學習的費時費力到快捷方便,獨特的優質的易學習的知識產品,才能吸引消費者。
獨特的知識產品。物以稀為貴,是市場的普遍規律,也是知識價值得以提升的前提。你有別人沒有的知識,當然你的知識就會被付費閱讀。像教你如何把握經濟形勢,教你如何在人際中游刃有余的知識,這既是當下受眾知識的盲點與痛點,也是受眾自身感興趣和有所需求的知識領域。知識產品能夠迎合受眾消費需求熱點和抓住市場機遇,獨家出售知識產品,吸引受眾為你的產品付費。
優質化的內容。在同類的知識產品競爭中,誰的知識產品做得好,用戶體驗感強,受眾也會愿意花錢購買。而優化知識產品,則需要從知識的專業性、用戶的體驗度方面著手。在目前的四大知識付費平臺,就各有各的優勢所在。得到,以專業化的內容生產者為優,其平臺知識的訂閱欄目以PGC生產模式為主,即專業生產內容,知識的生產者多為其知識領域的專業人士,知識的可信度和專業性有所保證,比如主打欄目《羅輯思維》,網紅欄目《薛兆豐的經濟學課》等;知乎、分答,則以UGC生產模式為主,即用戶生產內容,個人扮演自問自答的角色,既參與到陌生領域問題的解決當中來,又可以是自己熟悉領域的答主,身份轉換靈活,用戶的參與感較強,自我滿足感得到提升;喜馬拉雅以獨特的音頻模式起家,同樣注重用戶的參與欲望的滿足,但在知識展現方式上個性化突出。
便捷的學習方式。在如今快節奏、速食化的求知環境下,如何省時省力地完成一次知識的學習是受眾心中的訴求。觀察目前的知識付費產品,我們可以發現,這些知識都以比較精煉短小的形式包裝呈現,哪怕是訂閱的欄目,每期的內容時間也不會太長,且知識的展現形式也呈現多樣化,音頻+圖文+視頻等,既很好地滿足了當下人們快餐式、短時的獲取知識的習慣,也讓受眾將知識學的更高效快捷。
2.4 知識盈利模式的轉變
以微信公眾號為例,在微信公眾號紅利期,內容原創者生產的知識盈利來源主要是廣告投放+打賞。但隨著微信紅利的逐漸耗盡,那些網紅大V,專業領域的大牛們,就需要及時轉變原有的盈利手段,使自己手中的知識變現模式更加多元,價值提升。從知識的間接變現即廣告收益到知識的直接變現即知識付費,這是一種知識資源內容生產者以及知識付費平臺擁有者便捷的、收益可見的盈利模式。
3 知識付費的發展阻礙
知識付費本質上是一種知識服務行為。但平臺、原創者與受眾之間的沖突,也是現有的知識付費領域所遭遇到的困境。如近期出現的兩起新聞事件,就不得不引起我們的思考。
薛兆豐離職事件,網上對于他的身份與專業性的種種爭議,什么“知識騙子論”“舒緩焦慮論”,但歸根結底,其核心一點就在于因為缺乏對知識生產者的有效管理與監督,所以人們容易對內容生產者產生質疑,以至于會加重對他所提供的知識質量與效用的擔心。因此,如何衡量知識的質量?誰來保證知識專業性?需不需要一個第三方機構來評估知識的品質?
此外,在網上廣為流傳的一片文章《千聊:知識付費平臺的底線到底在哪兒》,揭露了內容生產者與平臺之間關系不為人知的一面。作者痛批了千聊這個知識付費平臺丑陋行徑:1)不承認已經簽好的合同,以不結算要挾原創者接受對自己更不利的修訂合同;2)不經原創者允許,鼓勵平臺直播間轉播原創者內容并且避開與原創者分成。
雖然,事后千聊做出了回應與解釋,但不管孰是孰非,這樣的事件都帶給我們對于知識付費平臺信用度以及原創者版權的保護深層次思考。平臺在簽約入駐原創者是否存在以大欺小的行為?知識生產者的相關版權如何得到有效保護?
4 結論
因此,平臺在積極簽約知識生產者時,能否考慮到內容的優質性,做好一個知識把關人角色,為受眾篩選更優質的、更符合受眾需求的知識產品,在平臺上建立更完善的優質內容識別機制,避免平臺上的知識內容走向低俗化、低值化。在與受眾互動上,能否考慮到用戶體驗感的表達渠道,讓用戶更多地參與到內容評價機制中來,這既是一個良好的使用反饋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聚合固有的用戶群體,吸引潛在的消費人群。
平臺、原創者、受眾不能是坑與互坑的關系,三者應處在一個和諧共生的有機體中,大家各取所需,形成多贏的局面。只有這樣,知識付費才能走的更加平穩,邁向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參考文獻
[1]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第39次中國互聯網發展狀況統計報告[R].2017.
[2]王傳珍.知識付費奇點與未來[J].互聯網經濟,2017(1):68-73.
[3]許森.知識零售變現模式的問題與思考——以付費語音問答服務“分答”為例[J].新媒體研究,2016(19):193-196.
[4]鄒伯涵,羅浩.知識付費——以開放、共享、付費為核心的知識傳播模式[J].新媒體研究,2017,3(11):110-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