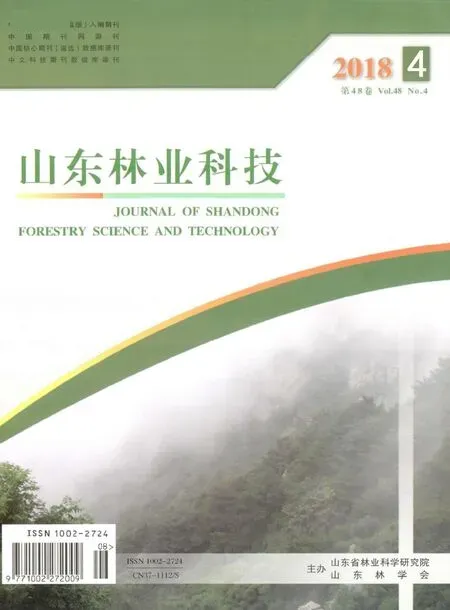淺析生態基礎設施與綠色基礎設施的共生與發展
王勝永,張天穎,李彤彤,吳 晗
(山東建筑大學藝術學院,山東 濟南 250000)
市政基礎設施規劃在傳統的城市設計中被重視,道路,橋梁和場地等灰色基礎設施形成了城市空間網絡,交通便利,同時也保證了工業化經濟的正常運行。在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灰色基礎設施日趨標準化,例如,道路都是具有單一功能的,而河道也因為只具有防洪的目的被截灣取直。客觀上來看,灰色基礎設施的提高了人們生活的便利性,但由于其忽視了適當的社會和生態功能,因而也引發了一部分的城市生態環境問題。
在這個大時代的背景下,生態基礎設施和綠色基礎設施的概念被專家學者們提出,提供了一個富有想象力的解決方案,結合灰色基礎設施的應用,創造出一個便捷又富有生態的城市生活環境。因此,研究EI和GI的內涵,對于構建城市的生態系統具有實際意義。
1 起源與發展
1.1 生態基礎設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簡稱EI)
EI在上世紀50年代萌芽,隨著生態城市的建設應用而生。隨后,“生態基礎設施”在1984年Man and the Biosphere Program報告中正式出現。它表示自然景觀和腹地對城市的持久支持能力[1]。后來有些學者擴大了應用范圍,從生物與環境保護和資源利用的角度出發,例如1988年EI的概念被用于表示棲息地網絡設計,1990荷蘭的農業、自然管理和漁業部的自然政策規劃中提出了全國尺度上的生態基礎設施(EI)概念[2]。隨后,一些科學家和研究機構開始強調自然環境和生命支撐系統在城市土地利用規劃(包括雨水花園、屋頂綠化和濕地等)以及促進環境健康方面的重要作用。
我國的俞孔堅團隊率先在2002年將“生態基礎設施”引入并應用于城市規劃之中。經過多年的發展和演變,EI的理念和優勢越來越受到科學家,工程技術人員和決策者的重視,其內涵和意義也逐漸被豐富和擴充。
1.2 綠色基礎設施(Green Infrastructure,簡稱GI)
美國是現代綠色基礎設施的發源地。1991年美國馬里蘭州綠道運動是GI概念的起源之處,希望能夠為解決城市發展過程中的建設與環境之間的矛盾提出新的思路和策略。美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于1999年發表了 “美國為21世紀創造可持續發展”,現代綠色基礎設施被明確提出。
我國最早涉及 GI研究的論文為1999年在杭州召開的IFPRA中刊登的一篇會議論文,自提出現代GI概念后,我國GI的理論與實踐研究便開始逐漸地拓展和深化。
2 概念辨析
2.1 定義與概述
2.1.1 EI
EI是一種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自然系統,它維持著城市的生態網絡的安全與健康,并確保城市及居民獲得連續的自然生態服務,是城市擴張和土地開發利用不可觸犯的剛性限制[3]。
為了提升EI理論研究的豐富性,景觀生態學、生物保護學、生態經濟學等可與其交叉研究。EI理念強調保持完整連續的生態格局,對于恢復受損生態系統,維護景觀完整性具有重要意義,是可持續發展的可行性景觀策略。
2.1.2 GI
GI在保護地球的自然生態功能和價值方面意義重大。“相互關聯的自然區域和其他開放空間網絡”是人們通常給其下的定義。GI代表綠色空間的互聯網絡時,被當作一個名詞使用。作為一個形容詞,GI描述了一個過程,提出了在國家、州、地區和地方范圍內的土地保護系統和戰略方法,鼓勵對于人類土地使用及規劃及自然生態系統具有益處的實踐。作為一個概念,GI網絡的規劃和管理可以建立一個提供保護,戶外娛樂和其他人類價值相結合的開放空間分配系統,連接已有的和未來的綠色空間資源。
截止到2010年,人工智能手段已經能夠與上述的深度學習技術實現緊密融合,因而在根源上規避了難度較大的權重訓練以及非線性分割。到了2014年,技術人員已經可以憑借圖像識別系統來辨別卷積神經網絡,此類圖像識別系統設有多層次的識別功能。至于現階段的智能交通而言,關鍵技術應當包含無人駕駛與其他相關的交通智能化操作。在這其中,無人駕駛技術本身具備突顯的典型性。這是由于無人駕駛能夠憑借網絡化手段來替代車輛的傳統駕駛方式,借助智能化措施來保障車輛平穩性以及行駛安全性。
GI是一種生態保護的方法,它將保護、基礎設施規劃及其他理念相互融合。綠色基礎設施提供了客觀、科學、理性的思維,把重點放在更有價值的方面。綠色基礎設施通過增加長期資金對開放空間的保護和管理的重要性,可以確保項目的相關性和可行性。
2.2 區別與聯系
灰色基礎設施,GI、EI的概念既區別又聯系。灰色的基礎設施是人造的、剛性的、成本高昂且功能單一。GI比灰色基礎設施更自然,生命支持系統更靈活,更復雜,成本更低。EI更加關注基礎設施的整合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強調整個系統的協調統一。生態基礎設施的概念辨析
2.3 內涵
2.3.1 EI
這是一個自然物種可以生長和棲息的生存環境,也是城市可持續發展賴以生存的自然系統。所有能夠提供這些自然服務的系統,如城市綠地,農林土地用地,保護區甚至自然和文化遺產等均屬于其研究范疇。建立生態基礎設施可以創造一個以大自然為背景的生態城市,也是在城市快速發展背景下構建城市生態結構和功能的重要手段之一。
現有的EI研究可以分為三個層次。其中國家和區域中EI的規劃空間結構是重中之重。城市規模重點是EI建設的控制性研究;微觀場地尺度的重點是如何采用生態設計的手法,進行生態基礎設施建設[3]。
2.3.2 GI
GI關注的是人與自然的關系。現在它已經成長為一個理論體系。主要涉及國家和國家公園,野生生物棲息地、森林、濕地等以及與自然發展規化景觀設計和環境敏感性相關的領域分析等。
由GI組成的綠色網絡是一個中央控制點系統,連接了上述生態系統和景觀的走廊和地點。在個人層面上,GI是圍繞綠色空間設計住宅和商業設施;;在社區層面,GI意味著創造與現有公園相連的綠色通道;從區域范圍上來說,GI是保護廣泛的景觀連接性
2.4 實踐作用研究
土人景觀團隊在俞孔堅教授帶領下,率先將EI戰略引入,并將景觀作為整合的媒介[4],通過靈活的河道建設生態基礎設施網絡,建立生態廊道作為第一功能的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增加,提高了物種的多樣性,豐富了濱海的活動空間。
浙江臺州的規劃也是一個典型案例。首先將生態基礎設施微觀化和網格化,然后再規劃道路和建筑,形成基于綠網的網格結構,構建了格網型城市結構的規劃模式[5]。
2.4.2 GI
GI的概念目前有兩種方法模式。從國家層面來看是最典型的是馬里蘭州模式,而西雅圖模式是從城市過程中演變而來。這兩者對于自然生活支持保障系統與城市的可持續發展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馬里蘭的核心理念是 “中心 (HUBS)—聯接(LINKS)的自然系統”,其模式是首先提供未開發的保護土地資源的概念。西雅圖模式的重點是關注城市規模及其建成區,重點關注農村城市建成區,對于城市高度人造的環境,建立了一套操作方法。這對于城市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新思路。

表1 灰色基礎設施、綠色基礎設施與
3 思考
綜上所述,EI和GI在首次被提及時,它們是被用來描述不同內涵的。但在逐漸發展的過程中,它們的外延不斷擴大,因此二者既有區別,又有重疊的部分,且各種情況都有主流的研究或組織支持。目前從廣義上來看,EI和GI的的區別幾乎不大,但二者的內涵卻日益相近——均對提供生態系統服務的生命支持系統具有重要性。而目前國內對于這二者的研究,仍存在一些問題。
3.1 EI
(1)只有少數的創新實踐,只停留在理論研究,生態服務功能和人類生活范圍是不對稱的,沒有適當的聯系。(2)生態服務功能并不被人們所廣泛認可,只有在生態被破壞時才發覺EI的重要性。(3)人類活動對生態服務功能的影響以及生態服務功能質量與生態健康的關系相對較少,與生態基礎設施的規劃脫節[6]。
3.2 GI
首先,目前我國GI主要專注于理論研究,缺乏實踐成果。二是政府部門參與不高,作為公共設施的GI,其發展和建設應由政府主導。但在中國,最常見的情況是,面對更多的經濟利益時,綠色空間往往被政府選擇犧牲。再者,從規劃的角度來看,GI具有單一功能。公眾參與度相對較少,主要的編制者是一些政府部門。因而GI的一些更為詳細的方面往往被忽視,往往只能在實踐中發現。
4 結語
在城市土地利用危機的背景下,EI和GI理論先后被提出。盡管它們最初的提出具有不同的針對性,但二者卻顯示了相同的本質內容:對能夠提供自然服務功能的城市自然區域和其他開放空間進行保護,是一種對土地的保護性規劃。
EI和GI是現代生態城市基礎設施的基礎,它們保護著城市的自然綠色空間,并加強自然空間網絡的連通性和完整性,發揮其重要的生態功能和價值,形成城市生存與發展的形成天然支撐,是城市“軟”的重要基礎設施。
保持自然系統的連通性,建立一個連貫的自然系統網絡,是EI和GI理論的核心概念。它們通常用于區域研究規模。正因為如此,城市通常被簡化為自然網絡上的點,因此城市邊緣和邊緣化的擴張區會被會更加注重。但是如今,現有的城市,特別是主要建成區關注度仍然較少,因此實施起來也被認為是具有一定的困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