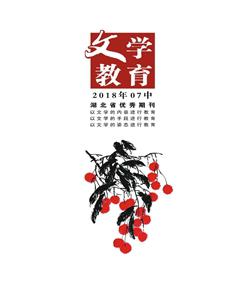“我可能V了假N”構式分析
內容摘要:“我可能V了假N”為2017年網絡流行語,經不斷發展成為流行構式。本文通過搜集分析BCC語料庫、微博、微信等大量語料,對“我可能V了假N”這一構式中的變項和常項構件進行考察,著重分析“假”的特殊含義及用法。同時,本文對該構式進行了語義解讀和語用分析。另外,本文對該構式流行的動因進行了一定探討,得出其主要動因為強勢模因、社會文化、大眾心理、互聯網環境等四方面作用。
關鍵詞:構式 “假” 語義 語用 動因
2017年1月,“我可能V了假N”系列語句出現并迅速躥紅于網絡,成為2017年網絡流行語之一。關于其來源,目前有兩種說法。一說來自電競圈用語,玩CSGO的隊員們喜歡喝酒,比賽發揮不好便將失敗歸因于酒,吐槽道“我可能喝了假酒”“假酒害人”。二說來自央視網新聞報道,俄羅斯不法商家將含有酒精的個人洗滌用品制成假酒進行販賣,導致多人因此中毒甚至死亡,“我可能喝了假酒”應運而生。隨后,紐約高中中文試卷太難引發熱議產生的“我可能學了假中文”、高校期末考試期間流傳出來的“我可能復習了假書”等使得該系列語句廣為傳播并流行。
本文基于Goldberg(2006)對“構式”所下定義,認為“我可能V了假N”的意義并不是“我可能”“V了”“假N”幾部分的簡單相加,而是形式和功能的配對,因此屬于流行構式。本文將著重分析這一構式中的常項與變項,并對該構式的語義特征、語用功能及流行動因作進一步探究。
一.“我可能V了假N”中的構件
(一)構式的變項
觀察收集所得語料,筆者發現,變項“V”一般由單音節動詞構成,“V”與“了”構成雙音節音段,符合漢語音節節奏整齊的特點和漢民族的審美心理。另有少部分由雙音節動詞構成。同時,動態助詞“了”表示動作的完成,因而變項“V”一般為具有動作性的動詞。
變項“N”一般是單音節或雙音節名詞,也可以是兩個音節以上的短語。其中,多數由單音節或雙音節名詞構成,例如“我可能過了假年”“我可能娶了假媳婦”“我可能讀了假大學”等。另外,少數也有可能由名詞性短語構成,例如“我可能收了假微信紅包”“我可能拿了假復習資料”等。
(二)構式的常項
1.常項“我”“可能”和“了”
“我可能V了假N”構式一般用于表達與主語“我”相關的情緒宣泄,“我”在該構式中充當主語。“可能”是助動詞,表示估計、不很確定。例如,“我可能學了假中文”中的“中文”實際并不假,單說“假中文”有悖常理,而能愿動詞“可能”的模糊性則使得本不合事實或邏輯的“假”合理化,從而使人們的關注點重新回到“假N”上來,以便突出“假N”的隱含意義。“了”為助詞,用于動詞之后,表示動作的完成。
2.常項“假”
“我可能V了假N”構式中“假”在名詞之前,用作定語,構成“形+名”結構“假N”。因此,我們只對“假”作形容詞的含義進行探析。《說文解字》對“假”的解釋為“假,非真也”。《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對“假”作形容詞時的解釋為“虛偽的,不真實的,偽造的,人造的(跟‘真相對)”。通過搜集整理BCC語料庫中有關“假”作形容詞時的語料,筆者發現,此前幾乎所有“假N”中的“假”均可以解釋為“與‘真相對”。例如:
(1)又訴說假李逵剪徑被殺一事,眾人大笑。(明·施耐庵《水滸傳》)
(2)偏你這些老婆們,有這們些“胡姑姑”“假姨姨”的!(明·西周生《醒世姻緣傳》)
(3)后來驚醒南柯夢,不識真言與假言。(清·陳端生《再生緣》)
(4)哪里有假,哪里取締。再也不能讓那些假貨——填食雞鴨之類,在農貿市場招搖了。(廈門日報 1985年9月2日)
我們認為,此前作為形容詞存在于“假N”結構中的“假”基本是對其所修飾的名詞屬性為真的否定。結合沈家煊(1993)對“語義否定”所下定義,“語義否定,是否定句子表達的命題的真實性,即否定句子的真值條件”,筆者推斷此前作為形容詞存在于“假N”結構中的“假”的用法屬于語義否定。
在“我可能V了假N”中,一部分“假”可以解釋為上述含義。例如:
(5)我可能爬了假長城。(新浪微博 2017年1月28日)
(6)我可能看了假兵馬俑。(新浪微博 2017年1月31日)
但是,在“我可能V了假N”中,大多數的“假”無法解釋為簡單的語義否定。例如:
(7)我可能學了假中文。(中國青年網 2017年1月16日)
(8)我可能放了假寒假。(網易云音樂 2017年1月16日)
結合大量語料來看,假“N”中的“N”并無真假之分,卻可以用“假”這個形容詞來修飾,“假”在此不是對N的語義否定。沈家煊(1993)指出,“語用否定,不是否定句子的真值條件,而是否定句子表達命題的方式的適合性”。筆者認為,“我可能V了假N”發展演變后期,“假N”結構中的“假”屬于語用否定。
二.我可能V了假N”的語義特征及語用功能
(一)語義特征
“我可能V了假N”構式最早的形式為“我可能喝了假酒”,無論是電競圈還是俄羅斯不法商家,有關其來源的兩種說法中“喝酒”均為具體事件,與社會上真實存在的造假現象有關。由此,“我可能喝了假酒”作為“我可能V了假N”構式的初始形式,其中的“假酒”屬于傳統意義上的對“酒”的真值進行否定,可解釋為“我可能喝了假冒偽劣的酒”。
隨著“我可能喝了假酒”的不斷流行,該流行語的語義發生虛化,不再局限于“喝了假冒偽劣的酒”這一具體事件,而開始運用于其他情境。例如:
(9)手疼、背疼、腿疼、膝蓋疼,我可能喝了假酒。(新浪微博 2017年5月24日)
(10)四點就要交論文定稿,我可能喝了假酒。(新浪微博 2017年5月24日)
在“我可能喝了假酒”廣泛流傳于網絡后,引發網友對其形式進行改編,逐漸發展為“我可能V了假N”流行構式,例如“我可能收到了假紅包”“我可能放了假周末”“我可能花了假錢”等,筆者認為這個過程屬于語言學層面的“類推”。在此階段,“我可能V了假N”的語義特征為反預期,且可根據具體語境細分為兩類,一類是對“N”的真值進行否定,另一類未否定“N”的真值,只是實際情況與心理預期出現偏差。
綜合上述三個階段的語義特征來看,“我可能V了假N”構式的總體語義特征是反預期,即現實情況與說話人的預期有所偏離。
(二)語用功能
沈家煊(2001)提出,“主觀性”是指語言的一種特性,說話人在說出一段話的同時表明自己對這段話的立場、態度和感情,“主觀化”是指語言為表現這種主觀性而采用相應的結構形式或經歷相應的演變過程。結合收集所得語料來看,筆者認為,表示現實違背預期的“我可能V了假N”是“主觀化”的體現。在具體語境中,這種“主觀化”有兩種不同的具體表現。
第一,多數情況下,現實未達預期,用以表達說話人的自嘲、吐槽或諷刺。例如:
(11)人人都說法語是最優美的語言,我可能學了假法語。(極課法語公眾號 2017年1月16日)
(12)我可能交了假女朋友,從不主動找我聊天。(文學魚公眾號 2017年2月20日)
第二,少數情況下,現實超出預期,用以表達說話人的驚訝或驚喜。例如:
(13)重點居然都背過,我可能拿到了假試卷。(來出書公眾號 2017年12月23日)
(14)我可能買了假插座!這款插座咋找不著插孔?(慈溪發布公眾號 2017年12月30日)
三.“我可能V了假N”的流行動因
本文將“我可能V了假N”的流行動因歸納為以下四個方面:
(一)語言模因對“我可能V了假N”衍化擴張的推動作用
Dawkins(1976)首次提出“Meme”概念,何自然(2003)將其“Meme”這一概念引進中國,譯為“模因”,其核心即為模仿與復制。因“我可能V了假N”初始形式新穎,激發網友獵奇心理,隨即被運用于多種情境場合,發生語義虛化。同時,由于其適用范圍廣、能產性高,極具調侃和諷刺意味,“我可能V了假N”在誕生后容易被宿主記住,并作為模因感染網友,在合適的語境中不斷產出,進而得到廣泛傳播。
(二)社會文化對“我可能V了假N”衍化擴張的推動作用
“我可能V了假N”中的“假”并非空穴來風,而是對當今社會生活中屢見不鮮的造假現象的真實反映,構式來源“我可能喝了假酒”中的“假酒”即為假冒偽劣的酒。后構式得以類推,也依賴于高校學生期末考試期間自嘲的社會現實情況,由此誕生“我可能復習了假書”“我可能參加了假考試”等系列語句。從社會層面考慮,“我可能V了假N”這一構式是適應當今社會發展形態,反映真實社會文化的流行構式。
(三)大眾心理對“我可能V了假N”衍化擴張的推動作用
首先,“我可能V了假N”構式中的大部分形式不是對“N”的簡單語義否定,而是一種較為特殊的語用否定,容易產生陌生化效果,符合大眾普遍存在著的求新求異心理。其次,“我可能V了假N”的主要語義特征為反預期,不管現實情況低于預期還是高于預期,說話者在說話時使用該構式均會達到一種委婉、幽默的表達效果,使得聽話者輕松接收信息。基于上述兩點,“我可能V了假N”符合求異和追求語言表達效果的心理,因此能被大眾廣泛接受且主動使用。
(四)互聯網環境對“我可能V了假N”衍化擴張的推動作用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與普及,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開始使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主流媒體也開始開通微信公眾號、官方微博等,這些條件為“我可能V了假N”構式的傳播流行創造了一定環境。同時,互聯網作為流行語的誕生地,具有時效性、交互性等特點,加之互聯網使用人群本身具有年輕多元的特點,推動了“我可能V了假N”的發展與傳播。
四.結語
本文通過分析相關語料,從組成構件、語義特征、語用功能、流行原因等角度對“我可能V了假N”這一流行構式進行了考察。從中發現,構式中的變項“V”一般為具有動作性的動詞,變項“N”一般由名詞或名詞性短語構成。“我可能V了假N”經歷初始、虛化、類推三個階段,總體語義特征為反預期,主要語用功能為主觀化。另外,“我可能V了假N”構式廣為流行有其動因,主要有強勢模因、社會文化、大眾心理、互聯網環境等四個方面。
參考文獻
[1]何自然,何雪林.模因論與社會語用[J].現代外語,2003(2).
[2]沈家煊.“語用否定”考察[J].中國語文,1993(5).
[3]沈家煊.語言的“主觀性”和“主觀化”[J].外語教學與研究,2001(4).
[4]Dawkins, R. The Selfish Gen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5]Goldberg, A. E.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M].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作者介紹:吳怡婧,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對外漢語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