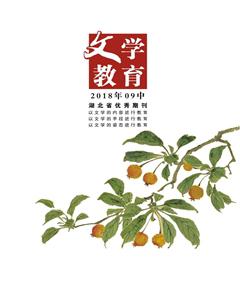權力規訓下的靈魂:評朱利安·巴恩斯《時間的噪音》
戴菊杰
內容摘要:《時間的噪音》是英國作家朱利安·巴恩斯于2016年發表的小說新作,以蘇聯作曲家肖斯塔科維奇為主人公。本文以米歇爾·福柯提出的規訓權力為理論視角,重點分析小說中呈現的規訓權力的運行機制、規訓權力對肖氏造成的影響、肖氏在權力規訓之下為了保全家人和音樂而做出的妥協以及為了維護藝術真誠和個人尊嚴而進行的消極反抗。
關鍵詞:《時間的噪音》 規訓權力 妥協 反抗
《時間的噪音》(The Noise of Time)是英國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1946—)于2016年發表的小說新作,譯林出版社于2018年1月出版了這部小說的中文譯本。2011年,巴恩斯憑借《終結的感覺》(The Sense of Ending)獲得布克獎,《時間的噪音》是他獲得布克獎之后的首部長篇小說。這是一部虛構傳記體小說,以蘇聯作曲家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肖斯塔科維奇為主人公。小說標題源自俄羅斯詩人奧西普·曼德爾斯塔姆(Osip Mandelstam,1891—1938)的同名回憶錄。曼德爾斯塔姆被以賽亞·柏林譽為“偉大的俄羅斯作家”(柏林 2011:40),他于“大清洗”期間被流放,死于蘇聯的集中營。小說標題中的“Time”既可以譯為“時間”,也可以譯為“時代”。巴恩斯給小說如此命名,既是向詩人致敬,也暗含對肖氏和曼德爾斯塔姆命運的對比。二者的相似之處在于他們的創作都曾偏離官方制定的標準化模式,成為整齊劃一時代的“噪音”;不同之處在于曼德爾斯塔姆死于流放,肖氏雖肉體幸存,卻終生活在等待被捕的恐懼之中。
肖氏是一個具有爭議性的人物,蘇聯稱他為國家最忠實的兒子,西方國家稱他為20世紀最偉大的作曲家之一。在小說后記中,巴恩斯提到他的創作主要參考了兩種素材:伊麗莎白·威爾遜的《肖斯塔科維奇:難忘的人生》和所羅門·伏爾科夫的《見證: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見證》據稱由肖氏口述、伏爾科夫記錄整理,肖氏在書中表達了對斯大林的譏諷,對“大清洗”中遇害友人的緬懷和他持續一生的恐懼。《見證》出版后在東西方都引起強烈轟動,肖氏由公開的蘇維埃政權堅定的信徒變成了私底下的異見人士,這引發了持續多年的關于其內容真偽的“肖斯塔科維奇之戰”。
巴恩斯的許多作品都呈現真相難以把握這個主題,他的小說經常運用多重視角,試圖從多角度更加全面地探尋歷史真相。在《時間的噪音》中,巴恩斯延續了他對歷史、真實、記憶、藝術的一貫關注。小說以肖氏青年、中年和晚年與權力的三次對話為中心,綜合運用意識流、第三人稱全知視角等敘述方法,在歷史真實和小說虛構之間來回切換,以碎片化形式勾勒出作曲家在權力規訓之下壓抑、妥協、消極反抗的一生,探討了權力與藝術之間的關系、藝術家面對權力規訓時的生存困境、藝術真誠和個人正直等一系列具有普世意義的問題,從而構建出巴恩斯心目中的肖斯塔科維奇形象——一個消極抵抗的懦弱的英雄。
對于這部小說,國外評論多以書評形式呈現,缺少研究性論文。目前國內學者發表了兩篇相關論文。侯志勇認為小說“揭示出作曲家在政治高壓下對藝術真誠和個人正直的追求和反思。在圍繞作曲家的種種爭議未有定論的背景下,巴恩斯創造出一個消極抵抗的偉大藝術家,塑造了一個‘懦弱的英雄”(候志勇 2016:65)。湯軼麗以文學倫理學批評為研究視角,“逐一解構死亡與生存、音樂與尊嚴以及信仰與藝術的倫理選擇,在此基礎上討論其最終做出成為懦夫的倫理選擇,剖析悲劇的不可抗性因素以及作品深處的倫理特性和價值,窺視巴恩斯的倫理情懷”(湯軼麗 2017:120—121)。
本文以米歇爾·福柯提出的規訓權力為理論視角,重點分析小說中呈現的規訓權力的運行機制、規訓權力對肖氏造成的影響、肖氏在權力規訓之下為了保全家人和音樂而做出的妥協以及為了維護藝術真誠和個人尊嚴而做出的消極反抗。
一.規訓權力運行機制及其影響
福柯認為規訓權力是一種特殊的權力,是一種精心計算的、持久的運作機制,“把個人既視為操練對象又視為操練工具”(福柯 2010:193)。規訓權力的治理手段主要有三種,即“層級監視、規范化裁決以及它們在該權力特有的程序——檢查——中的組合”(同上:194)。福柯認為最能體現規訓權力運行機制的是邊沁設計的全景敞視監獄。這種監獄的基本構造是:四周是一個環形建筑,被分成許多小囚室;中心是一座瞭望塔,它有一圈大窗戶,對著每個囚室的窗戶。因為逆光效果,瞭望塔里的監視者能夠清楚看到囚室里的一舉一動,但是被囚禁者卻看不見監視者,不知道自己是否正被監視。這種監禁模式造成權力內置,即被囚禁者自動用權力壓制自己,從而確保權力自動地發揮作用。
在《時間的噪音》中,肖氏的回憶呈現出一個全景敞視監獄模型:斯大林無處不在,“在他權威籠罩下的地球人就感覺到,或想象著他的眼睛永遠盯著他們”(巴恩斯 2018:153),這種極權狀態呼應了《一九八四》中的那句名言“老大哥在看著你”。人人都像全景敞視監獄中的犯人,時刻擔心自己正被中心瞭望塔里的官員監視,對被逮捕、流放、槍決的恐懼如影隨形,所以權力自動發揮規訓作用,民眾被規訓,也進行自我規訓。
巴恩斯描述了權力對藝術家進行層級監視,對他們的作品進行程序化的檢查和規范化的裁決。“檢查把層級監視的技術與規范化裁決的技術結合起來。它是一種追求規范化的目光,一種能夠導致定性、分類和懲罰的監視。”(福柯 2010:208)作曲家的所有作品必須經過從作曲家協會至最高權力斯大林的層級審查。權力不僅審查作品,還要審查藝術家的思想靈魂。作曲家協會給肖氏安排了思想導師,幫助他自我改造,以從源頭解決問題。執行規訓權力的“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為藝術的形式及內容都制定了規范,“作曲家被期待像礦工一樣提高產量,他的音樂被期待溫暖人心,就像礦工的煤溫暖身體一樣。官僚們在評估音樂的生產,就像他們評估其他種類的生產一樣:有標準產品,也有出了偏差的次品。”(巴恩斯 2018:33)輕微的實驗都會被定罪為形式主義,偏離蘇維埃藝術的大道。
“規訓處罰所特有的一個懲罰理由是不規范,即不符合準則,偏離準則。整個邊際模糊的不規范領域都屬于懲罰之列。”(福柯 2010:202)肖氏一生因偏離準則而受到眾多處罰。1936年,最高權力審查了肖氏的作品。斯大林和幾個政府官員去莫斯科歌劇院觀看肖氏創作的歌劇《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卻在中途離場。兩天后,《真理報》發表了據傳為斯大林本人所寫的題為《混亂取代了音樂》的社論,文章批評《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為形式主義作品,“不講政治、雜亂無章”,“用焦躁不安、神經質的音樂,撩撥了資產階級的墮落趣味”(巴恩斯 2018:34)。肖氏本人被定性為“人民公敵”,他的所有歌劇和芭蕾舞劇都被從保留劇目中清走。來自最高權力的審查和裁決給肖氏一生的創作造成致命的影響。在權力重壓之下,肖氏妥協了,他承認創作《姆欽斯克縣的麥克白夫人》犯下了大錯,而權力及時糾正了他。衛國戰爭期間,肖氏寫出了舉世聞名的《第七交響曲》,該曲符合官方準則,被評為反法西斯主義的杰作,他因此得到了權力的寬恕。1948年,日丹諾夫整肅音樂界,肖氏再次成為口誅筆伐的對象。他的《第八交響曲》遭到攻擊,因為它描述的戰爭是悲慘而可怕的,官方認為戰爭是光榮而壯麗的,必須得到贊美。權力再次給肖氏做出定性,認為他沉浸在不健康的個人主義和悲觀主義中,策劃破壞蘇聯音樂,腐化年輕作曲家,試圖在蘇聯恢復資本主義。規訓權力對此做出的裁決是:肖氏必須做公開檢討,莫斯科和列寧格勒的音樂學院都解除了他的教授職務。
規訓權力因肖氏偏離規則而對其進行懲罰,也因其遵守規則而給予獎賞。肖氏為多爾馬托夫斯基的文本寫了《森林之歌》。該劇堅稱,在斯大林統治下,甚至蘋果樹也變得更勇敢了,它們擊退了嚴寒,就像紅軍擊退了納粹。肖氏一生創作了不少符合規訓權力要求的作品,并因此獲得六次斯大林獎和其他眾多榮譽。“就像蝦被放進蘸蝦調料里一樣,他徜徉在榮譽中。”(同上:148)巴恩斯把肖氏比喻為蝦,榮譽是權力配制的調料,權力可以隨時吃掉蘸過調料的蝦。
漢娜·阿倫特認為,將人非人化的過程是通過三個階段完成的,第一步是“取消人的法律人格”(阿倫特 2011:559),第二步是“摧毀人身上的道德人格”(同上:563),最后一步是“消滅人的個體性”(同上:567)。在正常的懲罰制度之外建立集中營是取消人的法律人格的重要手段。巴恩斯描述了權力對肖氏身邊眾多無辜者的法律人格的破壞,有些被送去集中營,有些被處決,這使肖氏終生活在等待被捕的恐懼中。規訓權力對肖氏的道德人格和個體性造成嚴重破壞,迫使其人格分裂進而碎片化。1949年,斯大林親自給肖氏打電話,要求他作為蘇聯代表團成員參加在紐約召開的世界和平文化與科學大會,以彰顯蘇聯文藝在斯大林領導下取得的偉大成就。肖氏以多種理由試圖拒絕,最后在權力步步緊逼之下,被迫同意參會。會上,他作為政府的傀儡,宣讀由日丹諾夫等人寫好的演講稿,批評自己的作品,抨擊自己仰慕的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肖氏既是規訓權力的對象,也是權力用來規訓別人的工具,紐約之行破壞了他的道德人格,也給他帶來一生揮之不去的恥辱和羞愧。肖氏如瓦格納一般,總是被權力使用,根據政治需要,一會流行一會過時。斯大林去世后,赫魯曉夫掌權,蘇聯進入解凍期。1960年,赫魯曉夫政權強迫肖氏加入蘇共以擔任蘇聯作曲家協會主席,規劃蘇聯音樂的未來。因為肖氏是個人崇拜時期的犧牲品,此舉可以向世界證明個人崇拜時代已經結束,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蘇聯人民重獲自由,幸福時代已經來臨。肖氏生活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永遠不要加入蘇共,赫魯曉夫此舉摧毀了他最后的堅持,對他的個體性造成毀滅性破壞:“在權力的壓迫下,自我破碎了,分裂了。公開的怯懦和私下的英勇共生。或反之亦然。或者,更常見的是,公開的怯懦和私下的怯懦共生。但這太簡單了:斧起斧落,人的思想一劈為二。更確切的是:一個人碾碎成萬片,徒勞地想要記起它們——他——曾是一個怎樣的整體。”(巴恩斯 2018:195)
縱觀肖氏一生,他被迫在形形色色以他的名義寫的但他卻從未讀過的文章和公開信上簽名,甚至簽署針對他自己敬重的作家索爾仁尼琴的公開信。他不惜犧牲道德,甚至進行精神自殺以保全自己的家人和音樂,卻終生活在恐懼、恥辱、愧疚、自我厭惡之中。“規訓權力的在場往往表現為那種看得見的暴力的不在場”(張一兵 2013:27),肖氏終生等待被槍決,然而權力對他的規訓并不在于肉體“清洗”,而是精神虐殺——“這就是對他生活的最后的、無可爭辯的反諷:通過讓他活著,他們殺死了他。”(巴恩斯 2018:222)正如福柯所言,這種權力運行機制比酷刑和處決的儀式要有效得多。
二.反抗
盡管福柯構建出一個權力如毛細血管般無處不在的規訓社會,他還是認為權力與反抗是共生共存的,“只要存在著權力關系,就會存在反抗的可能性”(福柯 1997:47)。肖氏在權力規訓之下以自己的方式進行了或隱或顯的反抗。肖氏的保護人圖哈切夫斯基元帥被槍決后,肖氏身邊很多人陸續消失,他斷定自己也會被槍決。因為不想讓家人看見自己被捕的一幕,他連續十天每晚提著行李箱,站在電梯口,等待被捕。這一行為既是規訓權力的內置,也是對規訓權力的反抗,肖氏和他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試圖以自主選擇被捕的方式及地點來獲取對自己無法控制的命運的稍許控制權。當肖氏的思想導師指責他書房墻上沒有斯大林的肖像時,肖氏也采取了陽奉陰違策略。肖氏為了保護家人,保全自己的音樂,寫了一批迎合當局的“規范的”作品,他也寫了許多放進抽屜里,當時不能演出的音樂。音樂的特殊屬性使得他可以在作品中夾帶私貨,用反諷的形式表達個人觀點,宣泄不滿,并成功通過官方的審查。“就這樣,他把所有殘存的勇氣放進了音樂,把怯懦放進了生活。”(巴恩斯 2018:197)他希望世人不要相信他嘴里念出來的發言稿或是他簽名的文章,而是用心傾聽他創作的音樂,從音樂中理解他。
巴恩斯還描述了與肖氏同時代的其他藝術家和民眾對規訓權力的反抗。帕斯捷爾納克公開朗誦莎士比亞的第66首十四行詩時,所有的聽眾都會加入進來,一起朗誦第九句“藝術被權威綁住了舌頭”,“有的低聲咕噥,有的竊竊私語,膽子最大的會喊出最強音,但他們都揭穿了這行詩的謊言,都拒絕被綁住舌頭”(同上:111)。日丹諾夫說過,阿赫瑪托娃用她詩歌中腐爛和腐化的精神,毒害了蘇維埃青年的心靈。但是阿赫瑪托娃參加列寧格勒詩人朗誦會時,她一登上舞臺,所有觀眾本能地站起來為她喝彩。雖然規訓權力無孔不入,但是藝術家和普通民眾還是會采用自己的策略來進行反抗,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他們的個體性。
三.結語
雖然伏爾科夫的《見證:肖斯塔科維奇回憶錄》曾引起巨大爭議,但是巴恩斯在愷蒂對他的專訪中表明他認為《見證》中的肖氏具有很大的真實性,肖氏這個個案值得研究。巴恩斯在《時間的噪音》中以細膩的筆觸、精準的描寫刻畫了一個作曲家在特殊政治環境下終生被權力規訓,承受因妥協帶來的精神折磨、道德愧疚和人格碎片化,但從未徹底屈服,而是以自己的方式不斷反抗的故事,從而塑造了一個“懦弱的英雄”形象。小說零星穿插了與肖氏同時代的其他著名藝術家的事件,展現了斯大林極權主義時期和赫魯曉夫解凍時期的蘇聯文藝界概況,表達了對權力規訓之下藝術家艱難處境的深切同情與理解,也夾槍帶棒地嘲諷了部分深懷優越感、偏聽偏信的西方人道主義者和知識分子。巴恩斯借肖氏這個典型案例揭示了在特殊時代背景下眾多藝術家為了保護家人和朋友、保全自己的藝術創作而采取妥協和消極抵抗并用的策略,從而為其他類似歷史情境中個體或群體的行為提供了一個新的闡釋視角,有助于讀者從更多的角度探尋并接近難以把握的歷史真相。
參考文獻
[1]阿倫特,漢娜.極權主義的起源[M].林驤華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8.
[2]巴恩斯,朱利安.時間的噪音[M].嚴蓓雯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8.
[3]柏林,以賽亞.蘇聯的心靈[M].潘永強,劉北成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
[4]福柯,米歇爾.權利的眼睛——福柯訪談錄[M].嚴鋒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5]福柯,米歇爾.規訓與懲罰[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0.
[6]候志勇.“懦弱的英雄”——簡評朱利安·巴恩斯新作《時代的喧囂》[J].外國文學動態研究2016(4):65—71.
[7]湯軼麗.“我的英雄是一個懦夫”——巴恩斯《時代的噪音》中的倫理選擇[J].當代外國文學2017(3):119—126.
[8]張一兵.資本主義:全景敞視主義的治安—規訓社會——福柯《規訓與懲罰》解讀[J].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3(4):20—29.
(作者單位:譯林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