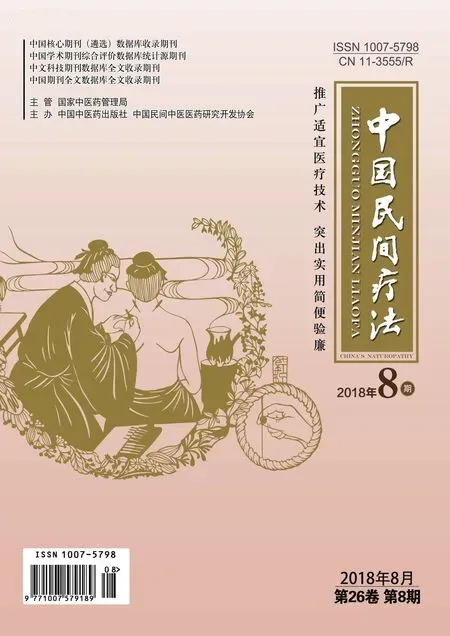真武湯治療頑固性心力衰竭的經驗總結
馮漢財,通信作者:陳國成
(廣東省廣州市越秀區中醫醫院,廣東 廣州 510030)
陳國成是廣東省首批名中醫師承項目指導老師,從醫30余年,臨證經驗豐富,對真武湯的臨床運用有獨到見解,臨床上常用真武湯治療頑固性心力衰竭,臨證中陳國成老師遣方選藥得當,療效顯著。筆者有幸跟師學習,獲益匪淺,現將陳國成老師運用真武湯治療頑固性心力衰竭經驗總結如下。
1 真武湯的源流及病機分析

《傷寒論注》云:“為有水氣,是立真武湯本意。小便不利是病根。腹痛下利,四肢沉重疼痛,皆水氣為患,因小便不利所致。然小便不利,實由坎中之無陽。坎中火用不宣,故腎家水體失職,是下焦虛寒,不能制水故也。法當壯元陽以消陰翳,逐留垢以清水源,因立此湯。”陳國成老師指出真武湯證重在坎中無陽,假使腎關不利,不由膀胱氣化,因此小便不利,水氣上泛則心下悸、胸悶,甚則氣促、肢體浮腫。如《長沙方歌括》所云:“真武者,北方司水之神也,以之名湯者,藉以鎮水之義也。夫人一身制水者脾也,主水者腎也,腎為胃關,聚水而從其類,倘腎中無陽,則脾之樞機雖運,而腎之關門不開,水即欲行,以無主制,故泛溢妄行而有是證也。”
2 案例舉隅
患者,男,75歲。10年前開始反復出現心悸、胸悶不適,活動后加重,休息后稍緩解,后癥狀逐漸加重,曾于廣東省某醫院就診,完善冠狀動脈CT等檢查后診斷為“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予以抗血小板聚集、調脂穩斑、擴張冠狀動脈及營養心肌等藥物治療后癥狀稍好轉。3年前患者開始出現氣促不適,完善B型腦鈉肽、胸片、心臟彩超等檢查后考慮合并慢性心力衰竭,予以利尿劑減輕心臟負荷等治療后癥狀緩解,但心悸、胸悶、氣促等癥狀每于天氣變化受寒后容易反復發作。1個月前患者受寒后再次出現心悸、胸悶、氣促,伴雙下肢浮腫,予擴張冠狀動脈、利尿等處理后稍好轉,但仍有反復發作。現為求中醫藥治療,遂至我院門診就診。刻下癥:患者神志清,精神疲倦,面色蒼白,心悸,胸悶,氣促,動則加重,頭暈,惡心欲嘔,發熱,畏寒,雙下肢浮腫,胃納差,睡眠一般,大便偏爛,小便清,量少。體格檢查:體溫37.8℃,血壓130/71 mm Hg(1 kPa=7.5 mm Hg);雙下肺可聞及散在細濕啰音,心率87次/分,各瓣膜聽診區未聞及明顯病理性雜音。雙下肢輕度凹陷性浮腫。舌淡,苔白,脈細弦。輔助檢查:心電圖示竇性心律,異常Q波,ST-T改變。腦尿鈉肽(BNP)812 pg/mL。西醫診斷: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心功能Ⅲ級。中醫診斷:心悸,心腎陽虛。治法為溫陽利水;予以真武湯加減。處方:熟附子25 g(先煎30 min),茯苓25 g,白術15 g,白芍15 g,桂枝5g,牛膝30 g,車前子30 g(包煎),5劑。煎煮時加生姜3片,以600 mL清水文火煎至250 mL,頓服,每日1劑,復渣再次服。
5 d后復診,患者神志清,精神一般,心悸、胸悶及氣促緩解,無惡心嘔吐,無發熱、畏寒,胃納較前好轉,睡眠一般,大便軟,小便清。查體:體溫36.5℃,血壓125/70 mm Hg;雙下肺可聞及少量細濕啰音,心率81次/分,各瓣膜聽診區未聞及明顯病理性雜音。雙下肢浮腫稍消退。舌淡,苔白,脈細弦。效不更方,繼續原方治療5劑,煎服法同前。
5 d后三診,患者神志清,精神一般,心悸、胸悶及氣促好轉,無惡心嘔吐,無發熱、畏寒,面色少華,胃納較前好轉,睡眠一般,大便軟,每日1次,小便清,量中。查體:血壓120/65 mm Hg,雙下肺可聞及少量細濕啰音,未聞及明顯干啰音,心率79次/分,各瓣膜聽診區未聞及明顯病理性雜音。雙下肢浮腫消退。舌淡紅,苔白,脈細。考慮無發熱、畏寒,水腫消退,擬在原方基礎上去桂枝,減少藥物劑量,具體方藥如下:熟附子15 g(先煎30 min),茯苓20 g,白術15 g,白芍10 g,牛膝15 g,車前子15 g(包煎),5劑,煎服法同前。1個月后隨訪,患者無明顯心悸、胸悶,無氣促,無雙下肢浮腫,病情穩定。

3 真武湯在臨床的鑒別運用
水氣是人體水液代謝異常形成的病理產物,又是重要的致病因素,常隨其停留部位及兼夾不同而產生多種病證。如《傷寒論》第40條曰:“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干嘔,發熱而咳,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其中嘔、發熱、小便不利、喘等癥狀與真武湯相似,但病機卻不同,小青龍湯證為表不解有水氣,表里皆寒實之病;而真武湯則為表已解有水氣,為陽虛水停之證。又如《傷寒論》第152條云:“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鞕滿,引脅下痛,干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里未和也,十棗湯主之。”上述汗出、干嘔、短氣亦與真武湯證中嘔、喘、汗相似,但十棗湯的主證為心下痞硬滿、引脅下痛、干嘔短氣,病機為水飲壅盛于里,停于胸脅,或水飲泛溢肢體,亦表里皆實證,舌脈以舌苔白滑、脈沉弦為主;而真武湯證為陽虛水飲內停所致,舌脈以舌淡或淡胖、苔白、脈沉細為主。正如《成方切用》所云:“青龍主太陽表水,十棗主太陽里水,真武主少陰里水。”再如《傷寒論》第355條云:“傷寒厥而心下悸,宜先治水,當服茯苓甘草湯,卻治其厥,不爾,水漬于胃必作利也。”本條亦有心下悸,伴肢體厥逆,且重在悸,不重在厥,宜先治水,與真武湯證病機亦有不同,因茯苓甘草湯證病機為太陽寒水內侵,陽氣未虛,故用桂枝溫陽化氣;真武湯證則為腎陽虛,少陰邪水泛溢,故重用附子以溫腎助陽,化氣行水。
陳國成老師根據臨床經驗指出《傷寒論》第316條后3項是真武加減證,不是主證,并強調“小便自利,心下不悸,便非真武湯證”,“若雖有水氣而不屬少陰,不得以真武湯治之”。
4 小結
頑固性心力衰竭又稱難治性心力衰竭,是指心力衰竭經過優化的內科治療,消除并發癥和誘因后,心力衰竭癥狀未能得到改善甚至有惡化傾向者,是心臟疾病發展至終末期的結果[1]。利尿劑是治療心力衰竭的基石,能減輕體液潴留,緩解癥狀,改善乏氧狀態;但長期大量應用常規利尿劑,會使血鈉濃度降低,機體產生利尿劑抵抗,從而加重水鈉潴留,進一步加重心力衰竭,形成惡性循環[2]。中醫中的心力衰竭與現代醫學意義上的心力衰竭并不完全一致,中醫心力衰竭主要包含在“心悸”“心痹”“喘證”“水腫”等疾病中,患者多表現為反復出現心悸、胸悶、呼吸困難,咳嗽、咳痰、咯血,乏力、疲倦、頭暈等表現。中醫多數學者認為,頑固性心力衰竭的主要病因病機是陽氣虛衰,血瘀痹阻,痰瘀互結,脾虛濕盛,痰瘀化熱,陰陽失衡等[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