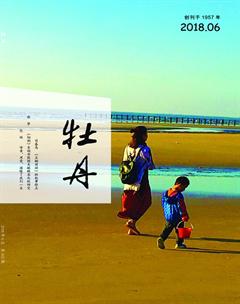《山海經(jīng)》中長生神話與西王母崇拜的關系
王亦瑋
神話時期,遠古先民相信自己的愿望有實現(xiàn)的途徑,如服食丹藥仙草、佩戴金玉靈石、吸收山水靈氣或乘上神獸鸞車等,而這些神異的物質(zhì)則歸于掌管生死職權的天神。《山海經(jīng)》對于死亡現(xiàn)象的記載不在少數(shù),有為了逐日而渴死的夸父、與黃帝頑強抗爭的蚩尤、日夜填海的精衛(wèi)和乳目臍首舞干戚的刑天等,可以看出神祇并非全部具有長生的能力。
一、長生神話中的生死觀與長生途徑
在神話時代,人們總結出一種獨特的生死觀念,這種觀念既包括對肉體可能出現(xiàn)物質(zhì)轉(zhuǎn)化的猜測,又包括對長生、高壽的熱切期盼。神話中反復出現(xiàn)可以延長生命、治療疾病甚至服之不死的植物、金玉等,佩戴靈獸或其身體的某部分可以起到同樣的作用。其實,當時并沒有出現(xiàn)獨立的醫(yī)者職業(yè),“醫(yī)”仍然屬于“巫”的范疇。“巫”是全能的存在,所以長生神話中明確表示可以治病的動植物其實都屬于巫術。他們以植物的形貌、色彩、果實、花朵以及動物的生活習性、斑紋、叫聲等主觀臆造出這些特性與疾病或災異的聯(lián)系。因為對自然的認識還處于樸素的思想狀態(tài),所以在當時的人眼中萬物皆有靈性。這種“靈”作為可分離肉體的新的載體,是可再生的、可循環(huán)的。并且,“靈”普適于一切物質(zhì),人類和自然界“靈”是平等的,都可以在肉體死亡之后轉(zhuǎn)化為新的、有生命的個體。所以,那些“不死”的傳說,并非真的讓人長生不死,而是進行了某種“靈”的轉(zhuǎn)化。在神話傳說中尋求長生的路徑有三種。
其一,人界與神界之間存在一條通道,人類可以借由這種通道與“天”對話、向神祈愿,從而獲得天神的恩賜。譬如《海內(nèi)西經(jīng)》中“帝之下都”便是這樣的通道。其在昆侖虛萬仞之高處,并由開明獸守護,尋常之人必然難以接近,只有像“仁羿”這樣的英雄才有資格進入神在人間建造的圣地。此外,“巫”作為被神選中的傳話者,同樣得到了這一殊榮。《海內(nèi)西經(jīng)》中有巫醫(yī)使用不死藥治療窫窳,令其復生的故事。我國作家袁珂曾說:“是原本巫職而兼醫(yī)職也。群巫之職任,乃在上下于天,宣達神旨人情,采藥療死,不過是其余技耳。”神會附身于巫,由巫口述神的意指,所以巫算得上是半人半神,所以擁有使用不死藥的資格。
其二,采氣養(yǎng)生是中國古代早有的現(xiàn)象,“氣”被看作支撐人體活動的唯一動力。《西次三經(jīng)》中“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泑山吸收著日氣,故此山山氣圓滿渾厚,多產(chǎn)寶玉。靠近或者居住于有如此強大之氣的地方使自己體內(nèi)的生氣得以補充,是常人最有可能做到的養(yǎng)生之法。
其三,對于神仙而言,他們的壽命亦需借助外界力量使其得以延續(xù),《西次三經(jīng)》中就有黃帝服食玉膏的記錄。顓頊、堯、舜、嚳在《山海經(jīng)》中皆有關于其墳墓處所的內(nèi)容,唯獨對黃帝的墓沒有明確記載。“這表明,《山海經(jīng)》認為黃帝是一個靠服食成仙的帝王”。后又出現(xiàn)過軒轅國“不壽者乃八百歲”的內(nèi)容,軒轅為黃帝一族,說明他的確靠玉膏延年益壽。不僅如此,《山海經(jīng)》多次提到祭祀山神需要用玉,也許玉之精華對于普通的山神來說也起到相同的作用。
二、西王母原型及其演化
從《西次山經(jīng)》關于西王母內(nèi)容的字面來看,其為一位人面虎身并且十分兇殘的怪物,也沒有關于其名字的出處,更無法直接得知“司天厲及五殘”權力的淵源。只知其有常人的面目、猛獸的軀干、神的職能。西王母居住在玉山,之前提到過玉對于神仙的作用,可見西王母的住所非尋常山丘能及。虎齒多是當時的人出于對猛虎這種野獸的恐懼心理,或是對強大力量的崇拜,將這些作為自己部落的標志去恐嚇其他部落。豹尾則是原始人類狩獵時利用動物的尾巴對自己進行偽裝,以此接近獵物。西王母的形象極有可能是以某個部落圖騰為原型的。
西王母所處方位,按五行說推算西方屬金,色白,與之相應的神獸為白虎,季節(jié)為秋。秋是萬物肅殺之季,古時處決人犯選在秋后,因此秋又代表著刑殺,這便決定了西王母的主要神職。張守節(jié)《正義》中解釋“五殘……見則五分毀敗之徵,大臣誅亡之象”,可以看出五殘為兇星。《海內(nèi)北經(jīng)》較之前文,另有“梯幾”“三青鳥”幾個新的特征,住所提到了昆侖。“梯幾”是倚靠在幾案之意,這樣氣定神閑的動作顯得雍容華貴。“三青鳥”是居住在大山中善飛的猛禽,如此一來,西王母的形象在更加貼近人類的同時,更突顯出其無尚尊貴的地位。《大荒西經(jīng)》增添一個新的要素——穴處,這與昆侖地區(qū)族群的居住習慣有關。此處更多著墨在對昆侖之丘的描繪上,從側(cè)面豐富了西王母所處地域的神秘性。無論是“鴻毛不浮”的弱水,還是“投物輒然”的炎火山,都起到了將仙界與人界隔離的作用。綜上所述,西王母的神話原型就是居住在昆侖神山上形容可怖的兇神。《爾雅·釋地》中有郭璞注:“觚竹在北,北戶在南,西王母在西,日下在東,皆四方昏荒之國,次四極者。”由此可見,西王母一詞也指極西的一個地方。以此為過渡,西王母由性別不明的兇神變?yōu)椤拔魍跄浮钡貐^(qū)的女首領。宗教成形前,巫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力,最先出現(xiàn)的母系氏族中所推選的群巫之首必然也是女性,女巫領導族人舉行祭祀天地、鬼神、祖先的活動。最早祭祀都是以人為祭品的,身為西方西王母地區(qū)的女巫,其必然奪去過無數(shù)被選作祭品的生命。這一點符合《山海經(jīng)》西王母主刑殺的職能,這位巫女于是成為了本族擁有生殺大權并與天對話的最高執(zhí)行人,亦是兇神西王母的傳話者。久而久之,這位女首領就被奉為在人界的“西王母”。自此,西王母成為始祖母神。
《穆天子傳》中的西王母完全褪去了野獸的形象,化作一位識禮且多情的女神。她于瑤池接見前來拜訪的周穆王,并許下周穆王“復來”的愿望。最終穆王不“復來”很有可能因其陽壽已盡,與王母無緣再會。關于西王母是否有令人長壽的能力,《穆天子傳》中雖沒有多余記載,結合此前所言人界西王母為部族巫首的身份,卻可以得出結論。西王母所在“昆侖丘”據(jù)考大致位于青藏高原上,有學者分析她就是生活在此一帶的羌族首領。聞一多先生特別強調(diào)了神仙思想的產(chǎn)生與羌戎民族進行火葬以求靈魂不死有密切的關系,他們相信經(jīng)過“巫的儀式”靈魂可以不跟隨肉體一同死去,主持這場儀式的就是他們的首領——西王母,所以西王母就這樣被賦予了使人長生的神力。其實,《山海經(jīng)》與《穆天子傳》中的西王母,究其根源身份是不同的。《穆天子傳》中的西王母貼近人的形象,是對西方少數(shù)民族女首領的神化,已經(jīng)屬于人類英雄的概念。二者之間的演變?yōu)楹髞砦魍跄競鹘y(tǒng)形象奠定了基礎。
西王母崇拜的完全成熟形成于兩漢時期,關于她的神化傳說更加仙人化。西漢的《淮南子·覽冥》有言“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羿妻嫦娥竊之奔月,托身于月,是為蟾蜍,而為月精”,可見西王母在漢代已然與不死神藥有了密切聯(lián)系。
三、長生神話與母神崇拜
由崇拜入手,遠古時期人們對神的崇拜源于對大千世界的恐懼,最初的目的只是想祈求惡神免除對人畜的傷害。《山海經(jīng)》中這種原始的兇神數(shù)不勝數(shù),這些神有猛獸和人的共同特征,他們的出現(xiàn)會給人類帶來災難,可見最初的神是形貌兇惡的半人半獸體態(tài)。他們之所以被奉為神明不過是因為當時的人們具有一種禳災的心態(tài),而非祈福。此外還有許多與這類神相似的怪物,如出現(xiàn)就會發(fā)大水的勝遇、蠻蠻、彘毛、軨軨、合窳、化蛇、夫諸,造成大火的畢方鳥、即狏,帶來瘟疫的絜鉤、蜚等。兇神是由先民對惡劣環(huán)境的恐懼不自覺產(chǎn)生的聯(lián)想,對母神的崇拜亦然。母神作為神被崇拜的區(qū)別性在于其生殖特征,這種崇拜一樣是由禳災向祈福發(fā)展的,當時的人最初崇拜母神是因為對無法掌握生命時限的茫然與恐懼。由恐懼向祈求發(fā)展是人類心理在認識的深化下不斷成熟的過程,如此可以簡單地解釋為什么西王母由最初的“司天厲及五殘”的刑殺之神演變?yōu)閾碛胁凰浪幍募瘛H~舒憲詳細分析了“虎食人”在原始時期的器具、雕刻、圖畫上的意義:“整個大地被表現(xiàn)為一只張開陰間之口的仰臥狀母虎。虎身內(nèi)部為陰間,虎身上方為陽界,陽界中央有宇宙山和宇宙樹,向上通向天堂神界。這個宇宙模式圖很好地顯示了初民以虎為死亡與再生母神的神話想象景觀。”
這段文字直接肯定了在先民世界觀中母神、虎與生死的密切關系。此外,槐江山神英招、昆侖之丘的神陸吾、泑山神蓐收等,都有虎和人的部分特征,證明在遠古時期虎是某種共同的崇拜元素。《大荒西經(jīng)》多了“穴處”二字,這不僅僅是對當時西部地區(qū)人們生活習慣的映射,而是暗含著西王母的母神性質(zhì)。遠古時期不乏在洞穴中祭祀神明的舉動,洞穴為他們提供了一種處于母胎的安全感。又言“穴”便是當時的人對母體孕育的生殖的隱晦幻想。弗洛伊德早就論證,山洞,溪谷,窟穴,乃至屋室都是玄牝或生殖腔孔的象征。從人獸同體的兇神向完全的母神過渡,正是“崇拜”的內(nèi)涵由恐懼逐漸走向“祈求”的必然結果。
《山海經(jīng)》中對于山川河流以及其中神屬都只是簡要記錄,只依照圖畫陳述,故而還原圖畫的結構十分重要。如何通過靜態(tài)的圖畫來展現(xiàn)生命的誕生與消亡?此中關于日月升落的情節(jié)既可以構成完整的圖畫,又與生死間的流轉(zhuǎn)暗中契合。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孽搖頹羝。上有扶木,柱三百里,其葉如芥。有谷曰溫源谷,湯谷上有扶木,一曰方至,一曰方出,皆載于烏。”這段文字講的是太陽在三足烏的載負下輪流交替的情景,說明扶木所在的大荒東是太陽的起始之處,同樣是生命的萌發(fā)之處。群山坐落于東南西北四個方位且相互接連,日月出入的山頂形成一“周”,先民可以眼觀的日月軌跡就是“周”。周是一個輪回,日月經(jīng)過輪回始終在天空運轉(zhuǎn)。這是先民對于生死互化的靈感來源,日代表新生,月代表死亡。同樣代表死亡的還有西方位,而西王母所居之處又被“弱水之淵環(huán)之”,外又有“投火輒然”的炎火山,說明這位執(zhí)掌刑殺的兇神本身就出于一環(huán)又一環(huán)險象的包圍之中。“環(huán)”“周”這樣的結構在《山海經(jīng)》中頻頻出現(xiàn),又以險山惡水為多,恰與前所提及出于恐懼的崇拜不謀而合。再說“月”與陰陽生死之間的聯(lián)系,《山海經(jīng)》中明確具有月神格的是常羲。常羲是十二月的母親,由她來“司其短長”,與生育十日的羲和同為帝俊之妻。月神之所以是女性是遠古先民出于“對行經(jīng)女子的恐懼”,他們僅發(fā)現(xiàn)女性月經(jīng)周期與月相變化似乎有著某種聯(lián)系,他們恐懼經(jīng)血,進而恐懼月亮、恐懼女性,于是有了“拜月”的習俗。代表了鮮血與死亡的月神屬性就這樣與母神牽出一條聯(lián)系。“月亮在神話傳說中的表意趨大,它不僅是繁殖、重生的象征,還因原始人類對女子信水的恐懼,成為死亡的象征”,西王母的刑殺死神神格應該與此有關。
彼時的神話傳說中“長生”可以具體地分為長生、重生、化生三種情況。長生是最為簡單的一種形式,即不老不滅,生命被無限延續(xù)。重生則是生命體征完全消失之后再次取得生命的過程。化生的條件更為復雜,是不變的“靈”由一個肉體進入另一個肉體從而實現(xiàn)其新生。第一種不老的長生,是先民對生死認識的第一個階段,他們意識到自我老去的過程,死亡則是這個過程的終點。不老愿望寄托于神則是來源于先民對自然的觀察,日月的輪轉(zhuǎn)、江海的循環(huán),一切周而復始的自然更替被視為其生命的永不消減,認為日、月這類自然物質(zhì)就像人一樣是由母胎孕育而生的。就此而出現(xiàn)的日神、月神最初都是以母神為原始形象,育有十二月的常羲、浴日扶桑的羲和皆為女性神。她們誕下并撫養(yǎng)了長生的日月,卻也釀成了“十日并出,焦禾稼,殺草木”的人間慘劇。這說明母神在最開始只是具有生殖職能的中性神,既不屬于吉神也不屬于兇神,僅僅作為創(chuàng)造日月的始祖存在。此時的母神崇拜應出于對自然災異的恐懼,隨著先民認識能力的發(fā)展才演化為向母神祈求長生,從根源看來這是生殖崇拜的萌芽。
第二種重生觀念則更加富有人情意味也更加大膽,是由“不老”向“不死”愿望的轉(zhuǎn)化。王充《論衡》有言“少則發(fā)黑,老則發(fā)白,白久則黃。發(fā)之變,形非變也。人少則膚白,老則膚黑,黑久則黯,若有垢矣。發(fā)黃而膚為垢,故《禮》曰:‘發(fā)變異,故人老壽遲死,骨肉不可變更,壽極則死矣。”可以看出當時對“老”的認識比較成熟,同時“不死”觀也早已發(fā)端。《山海經(jīng)》中出現(xiàn)過不死神藥:“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帝派群巫以不死藥解救窫窳,是對無辜受難者的仁慈。這些持有不死神藥的巫師應與女祭、女戚一樣為女性巫。母神崇拜除對生殖功能崇拜外,已然加入了對其司生死的神格崇拜。重生意味更加復雜,將已故肉體復活需要借助“不死藥”來達到目的,這也是西王母神格演變中一個極為重要的轉(zhuǎn)折點。與其意義相同的還有不死民:“不死民在其東,其為人黑色,壽,不死”,郭璞注“有員丘山,上有不死樹,食之乃壽。”“不死樹”大概就起到了不死藥的作用,證明了普通的國民也可以求得長生。就地理位置來看,與西王母所居昆侖之山距離不會太遠,此山也當屬神山。不死民有“黑色”的特點,黑色既與死亡有密切聯(lián)系,又在“陰陽”觀念中作為“陰”的一方成為母神的色屬,如此一來西王母在掌刑殺之余兼具“不死藥”的管理就顯得順理成章。
第三種化生,較之前兩種而言神話色彩更加濃郁,樸素世界觀的局限逐漸淡化,哲學思想悄然萌芽。此時生死不再只是肉體的誕生與消亡,人類意識到“靈”對生命的傳承,肉身只是非必要的物質(zhì)載體,“靈”才是驅(qū)使載體行動的主導者。借由“靈”進行生死轉(zhuǎn)化的典型事例有精衛(wèi)填海、鯀腹生禹的傳說,還有夸父逐日道渴而死后其杖化為桃林、蚩尤棄其桎梏變?yōu)闂髂疽活悺4祟惢男问奖容^晦澀,桃林、楓木的生命特性似乎沒有直接化生為人明晰,然而草木可以代代相生,傳遞著夸父、蚩尤的“靈”的思想。化生不需要借助外界因素,生死與否完全在于“靈”,比長生、重生來得更加神秘。此時,母神崇拜的原始性淡化,人類將更多的注意力轉(zhuǎn)向?qū)ψ晕业恼J識,最終保留下來的只有代表性的各種儀式,在本階段母神與女巫的作用別無二致,只作為天和人之間交互的媒介而已。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