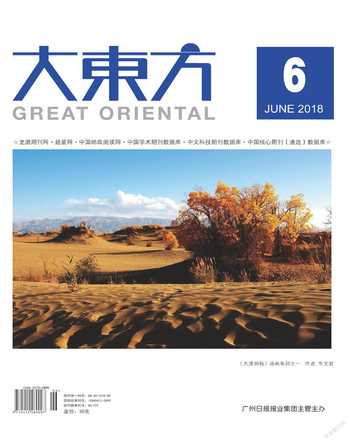論民事訴訟執(zhí)行難
摘 要:近些年來,民事訴訟執(zhí)行難問題成為了困擾司法機關(guān)的一大難題,執(zhí)行成效的問題對民事訴訟的影響也越來越深。司法實踐中大量的執(zhí)行難的問題引起了我國有關(guān)部門的注意,理清民事判決與民事執(zhí)行之間的關(guān)系,妥善解決民事訴訟執(zhí)行難的問題,是如今司法公正的必然要求,對于當代我國法治國家構(gòu)建同樣具有重大的意義。
關(guān)鍵詞:民事訴訟;民事判決;執(zhí)行難
一、現(xiàn)階段民事執(zhí)行難的現(xiàn)狀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民事判決執(zhí)行難的問題困擾已久,而隨著時間的推進,執(zhí)行難問題也越來越嚴重。民事案件居高不下,案子越積越多,舊的案件還未執(zhí)行,新的案子撲面而來,造成執(zhí)行案件一邊執(zhí)行一邊累積的惡性循環(huán)。而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交通的便利,執(zhí)行的難度也越來越大,在實踐中,有許多案件敗訴方的當事人負有給付、賠償?shù)牧x務(wù),但其為了逃避義務(wù),往往視法院的判決和法律不顧,在判決下達后,以外出務(wù)工等名義逃之夭夭,讓執(zhí)行機關(guān)找不到人。此時,法院不得不耗費大量的精力去找尋被執(zhí)行人,而由于時間和執(zhí)行人員數(shù)量的限制,法院也往往是無功而返,毫無頭緒。由于找不到執(zhí)行人,其他的案件又接踵而來,執(zhí)行人員也不得不將案件暫時擱置,使得生效的法律文書變成了“拿不到錢的白條”。同時被執(zhí)行人有可執(zhí)行的財產(chǎn)是民事執(zhí)行的前提,而由于執(zhí)行人法律意識淡薄,通常采用轉(zhuǎn)移財產(chǎn)的方式來逃避義務(wù)。被執(zhí)行人開設(shè)多個戶頭,并提供給法院虛假的賬戶,使得法院查不到其真實的賬戶信息;或者與他人惡意竄通,將其名下的財產(chǎn)轉(zhuǎn)移,造成沒有可供執(zhí)行財產(chǎn)的假象來逃避債務(wù),欺騙法院[1]被執(zhí)行人的消極對抗,使得執(zhí)行機關(guān)想要強制執(zhí)行,卻無從下手。因而“執(zhí)行難”的問題始終困擾著法院。最后,被執(zhí)行人暴力抗法的現(xiàn)象也越發(fā)的嚴重。
二、民事判決執(zhí)行難的原因
造成民事判決執(zhí)行難的原因并不是單一的,而是復(fù)雜多樣的。首先,從立法上看來,民事強制執(zhí)行法的缺失是最為直接的原因。我國執(zhí)行在立法上的缺失直接給拒不執(zhí)行的被執(zhí)行人們可乘之機,迄今為止,我國仍沒有一部完備的《民事強制執(zhí)行法》,沒有完備的立法規(guī)定,從而導(dǎo)致在執(zhí)行上缺乏可操作性,這是“執(zhí)行難”問題的一大癥結(jié)。[2]強制執(zhí)行立法上的缺位,使得我國民事執(zhí)行的主要依據(jù)為現(xiàn)行的《民事訴訟法》,而由于現(xiàn)有《民事訴訟法》對執(zhí)行問題規(guī)定的有限性,使得執(zhí)行難的問題一直未得到有效的破解。盡管在2012年、2015年連續(xù)對《民事訴訟法》進行了兩次的修改,增大了執(zhí)行的力度,但“執(zhí)行難”的局面仍沒有從根本上得到解決。
其次,從行政與司法的關(guān)系上來說,在實踐中黨政機關(guān)干預(yù)執(zhí)行活動的情況仍頻有發(fā)生。黨政機關(guān)以權(quán)壓法、用行政權(quán)力干擾司法活動已成為“執(zhí)行難”的另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因。[3]例如,2011年陜西省政府干預(yù)陜西省最高人民法院判決執(zhí)行的“7·17事件”是行政權(quán)力干預(yù)司法權(quán)力的典型代表案例。此案件源于是礦權(quán)糾紛,其導(dǎo)火索是一起久拖不決的“民告官”案,致使陜西榆林市橫山縣波羅鎮(zhèn)山東煤礦和波羅鎮(zhèn)樊河村發(fā)生群體性械斗。然而這起礦權(quán)糾紛案,早已經(jīng)榆林市中院判決,陜西省高院裁定,但久久得不到有效的執(zhí)行,致使價值數(shù)億元的集體財產(chǎn)歸于個人名下,引發(fā)民怨民憤。而就在陜西省最高人民法院最終審理該礦產(chǎn)案件時,陜西省政府辦公廳竟向法院發(fā)布函件,稱若高院維持原判決的審理結(jié)果將不利于整個陜西省的穩(wěn)定,向法院施加壓力。整個案件從判決到執(zhí)行,整整長達3年的時間,集中的體現(xiàn)了司法權(quán)和執(zhí)行權(quán)嚴重受到行政權(quán)力的制約。最后,從公民的守法意識上看開,公眾法律意識與誠信觀念的淡薄是阻礙民事判決執(zhí)行的一大絆腳石。
三、破解執(zhí)行難問題的方法
執(zhí)行難問題是一個全世界都在面臨的困境,各國為了有效的克服執(zhí)行難的問題,一直都在努力的尋求破解之道。縱觀世界各國的探索,其中英國和法國的執(zhí)行制度的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定與修改較為合理,值得我國借鑒。1806年,法國在《民事訴訟法典》中首次明確規(guī)定了執(zhí)行程序,為執(zhí)行提供了法律依據(jù)。而后在1991年的法國新《民事訴訟法典》中,執(zhí)行程序和審判程序已完全被分開,這樣,執(zhí)行制度在事實上就成為了單獨的法典形式而存在。[5]法國尤其注重執(zhí)行制度的變革與完善,采取審判與執(zhí)行相分離的執(zhí)行模式,并早就規(guī)定了規(guī)定民事訴訟檢察監(jiān)督制度,為民事訴訟的執(zhí)行提供了保障。
除對其他國家先進立法模式的借鑒外,為攻克我國執(zhí)行難的困境,應(yīng)從整個民事執(zhí)行的法律體系的構(gòu)建上做出相應(yīng)的調(diào)整。完善民事強制執(zhí)行立法,民事強制執(zhí)行立法的滯后和缺失已嚴重阻礙執(zhí)行工作的有效開展,雖然我國在執(zhí)行立法上的探索從未停止,不斷出臺相關(guān)的司法解釋和懲治“老賴”的規(guī)定,但尚沒有特定的執(zhí)行法律法規(guī),我國應(yīng)當制定完備的《民事強制執(zhí)行法》,為執(zhí)行工作的開展提供強有力的制度保障。完善民事判決執(zhí)行體系;完備的執(zhí)行體系能夠?qū)崿F(xiàn)對執(zhí)行問題保障機制。案件一旦進入執(zhí)行程序后,執(zhí)行機關(guān)應(yīng)根據(jù)需要采取相應(yīng)的措施,快速及時準確的掌控被執(zhí)行人的財產(chǎn),等候具體的執(zhí)行措施。建立完備的執(zhí)行體系,防范其他機關(guān)和相關(guān)因素對執(zhí)行工作的干擾,杜絕執(zhí)行人員消極怠慢執(zhí)法的現(xiàn)象,使得執(zhí)行階段進入一個嶄新的工作階段,擺脫上一階段的控制。
最后,完善整個社會的信用體系,創(chuàng)新執(zhí)行機制對破解執(zhí)行難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為推進整個社會信用體系的建設(shè),公權(quán)力應(yīng)當發(fā)揮其主導(dǎo)作用。我國執(zhí)行難問題的解決應(yīng)當不斷完善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梳理工作,在征信系統(tǒng)中對一些拒不執(zhí)行判決的“老賴”們予以透明化,對被執(zhí)行人的可執(zhí)行財產(chǎn)加以明確化,使得社會信用體系和征信系統(tǒng)得到合理的應(yīng)用。同時,創(chuàng)新新的執(zhí)行機制也有利于執(zhí)行難問題的解決。例如:舉行公開執(zhí)行聽證制度,對執(zhí)行有異議的當事人可提出聽證的要求;創(chuàng)立強制審計制度;強化申請執(zhí)行人的舉證責(zé)任等方式都能有效促進執(zhí)行難問題的解決。
參考文獻
[1]景漢朝,盧子娟.執(zhí)行難原因及其對策[J].法學(xué)研究.2000,(5)
[2]陳明.關(guān)于執(zhí)行難問題成因及對策的思考[J].山東審判.2016,(5)
[3]何世川,韋吉莉.試論法院執(zhí)行難問題的成因及對策.[J].法制與社會.2010,(12)8.
[4]朱揚.關(guān)于人民法院執(zhí)行難問題的思考[J].法制博覽.2017,(3)
[5]江必新.論民事執(zhí)行重大疑難問題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17.
作者簡介:
杜宇(1995-),女 漢族 黑龍江大興安嶺人,就讀于黑龍江大學(xué)研究生學(xué)院,研究方向:刑法
(作者單位:黑龍江大學(xué)研究生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