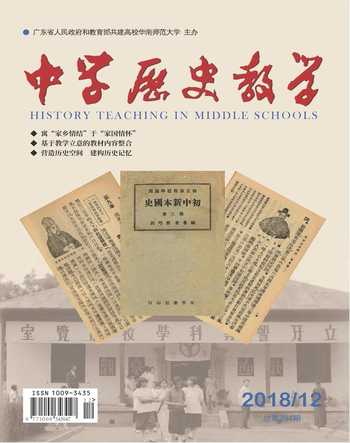要在“禮”上下足功夫
范從華
在人教版必修三“‘百家爭鳴和儒家思想的形成”(以下簡稱“百家爭鳴”)一課,教材有兩處提到“禮”:一處是,在介紹孔子的主張時寫道:“他希望恢復西周的禮樂制度,主張‘克己復禮,使每個人的行為符合禮的要求。”另一處是,“荀子……強調用禮樂來規范人的行為,使人向善。”在教學過程中,就筆者的觀察,教者對“禮”都不太重視。隨著閱讀和思考的深入,筆者認為有必要改變這一狀況。
一、從課程目標看,隱含著對“禮”的學習要求
禮作為日常生活中的文明行為規范,世界上任何一個地區或國家都有。所不同的是中國的禮在源于母系氏族時代的自然禮儀系統之后,中經五帝時代的社會禮儀系統,到三代兩次調整形成政治等級禮儀系統,[1]最后經孔子等儒家學者的整合、努力,使得“禮”在中國,成為“一個獨特的概念”,“其他民族之‘禮一般不超出禮俗、禮儀、禮貌的范圍。而中國之‘禮,則與政治、法律、宗教、思想、哲學、習俗、文學、藝術,乃至于經濟、軍事,無不結為一個整體,為中國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之總名。”[2]禮“標志著中國的特殊性”,因而,“要了解中國文化,必須站到更高處來看到中國之心。中國的核心思想就是‘禮。”[3]
盡管從字面上看,在《普通高中歷史課程標準(實驗)》的“學習要點”部分并未出現關于“禮”的學習規定,但是,在“課程目標”部分,課標提出“通過學習,進一步了解中國國情,熱愛和繼承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激發對祖國歷史與文化的自豪感”。顯然,標志著中國的特殊性的“禮”,是達成這一目標的“橋梁”和“載體”。
二、從課程內容看,“禮”是“百家爭鳴”的“主線”
細細分析“百家爭鳴”這一歷史現象,“禮”不僅是孔子、孟子、荀子等儒家學者探討的話題,而且也受到道家、墨家、法家等學派的關注,他們甚至曾對之展開過爭論。“禮”是貫穿其中的主線。
課文開篇寫道:“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社會發生重大變革。原來地位較低的士,在社會生活中活躍起來,受到各諸侯國統治者的重用。他們代表本階層或政治派別的利益和要求,提出自己的主張。政治和經濟大變動,導致教育和學術領域也發生變化,……,在社會上形成一些以傳播文化、發展學術為宗旨的學者和思想流派。”這段話揭示了“百家”出現及其“爭鳴”的政治、經濟和教育文化背景,體現了思想與時代劇變的關系。
“禮崩樂壞”是春秋戰國時期時代劇變在政治上的表現,這個崩掉的“禮”是“周禮”。周禮是西周開國之后,出于長治久安的考慮,在損益夏、殷之禮的基礎上歷成、康、昭、穆數朝近百年時間而形成的一整套典章、制度、規矩、儀節。它以王室為權力中心,“以血緣父家長制為基礎(親親)的等級制度是其骨脊,分封、世襲、井田、宗法等政治經濟體制則是它的延伸擴展。”[4]西周王朝因其持續強盛了差不多300年。但是至春秋之世,隨著王室的頹敗,周禮已不被人們遵循,比如,在貴族政治生活中,天子威勢掃地,諸侯爭為伯長,由“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一至“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再至“自大夫出”,乃至“陪臣執國命”;在城市生活中,于城市喧囂繁榮外表下出現普遍性的“游俠盜逞,作巧奸冶”;而在鄉野,已不復平和淳樸而又融洽的人際關系。[5]當時之天下,誠如孟子所言:“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6]
“一個動蕩的時代,常常使人們對既定的價值發生疑惑。”[7]疑惑引發思考,對春秋戰國時期的儒、道、法、墨諸家而言,“禮”是必須直面的話題,“對待禮的不同態度直接導致不同學派的產生,決定不同學派的學術旨趣。”[8]按照教材正文部分的敘述,正如本文開頭所言只在介紹孔子、荀子時提到“禮”,而在介紹儒家的孟子及道家、法家時都未提及其在“禮”方面的主張,其實借助文獻檢視教材所介紹的他們的主張,這些主張與其對“禮”的看法都有一定的關系。
1.儒家尊禮
作為儒家的開山鼻祖,孔子十分看重“禮”,《論語》及先秦文獻《左傳》、《國語》中記載了很多孔子議禮的言論。今人普遍認為,孔子之禮主要繼承自周代的禮儀制度,教材亦持這一觀點。但也有論者認為孔子并非一味地泥古“從周”,而是在周禮的基礎上,頗添加了“個人的一些向往和期待”。[9]這主要表現在:(1)提出“克己復禮為仁”,[10]通過援仁入禮,用“仁”來充實“禮”,使“禮”獲得了內在的道德依據和精神支撐。“禮”從此不再僅是政治之“禮”,而且是道德之“禮”,“‘禮被賦予了道德的內涵,由外在的、被動的、政治的約束,轉化為人們內在的、主動的、自覺的道德訴求。”[11](2)主張以德治民,“為國以禮”,[12]將過去只適用于貴族成員的“禮”變成適用于全體社會成員。“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13]這是對周禮“禮不下庶人”的顛覆。(3)興辦私學與“有教無類”的教育主張,否定了周代的“學在官府”,突破了周禮以“親親”為原則的貴族教育制度的藩籬。
孟子是繼孔子之后被尊為“亞圣”的儒家學者,其思想體系的核心是仁政學說。相對于“仁政”學說,“禮”在孟子的思想中似乎處于次要地位(有學者統計,《孟子》一書中,“仁”字出現157次,而“禮”只出現68次)。如果拘泥于教材表述,孟子似乎對“禮”視而不見。其實不然,孟子的“禮的精神,主要體現在‘仁的范疇內”,[14]其仁政主張“是先秦儒家以禮治國主張的一種具體作法”。[15]在孟子的仁政學說中,西周和春秋以來的禮的“人本”內涵已經完全向“民本”發生轉移。在跟各國執政者的對話中,孟子常提醒執政者要充分重視民眾。[16]在孟子眼中,民眾的地位高于社稷,高于君主,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17]
荀子是禮學的集大成者,他特別重視“禮”,在《荀子》一書中,他對禮的起源、本質、作用等作了詳細的論述,形成了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18]其理論特色在于:(1)認為禮源于人性之惡。他說:“古者圣王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導之也。”[19]在荀子看來禮的邏輯起點是欲是惡,為了制欲治亂,先王便“制禮義以分之”。[20](2)主張禮法兼用。荀子大講刑政,并稱禮、法,是荀學區別于孔孟的基本特色。[21]在禮法關系上,荀子更看重禮,他認為“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22]也就是說禮是治國的根本,是起指導作用的一般原則,而法是為了實現禮的原則而運用的手段。[23]
概括言之,孔子、孟子、荀子都主張用“禮”來匡正或維護社會秩序。但由于各人所處時代和思維路徑的不同,孟子在禮論中以“仁政”為前提,而荀子以儒家為宗,同時吸收了法家的營養,主張禮法皆用。[24]
2.道家“非禮”
老子、莊子對“禮”持批評態度,這種批評,一方面源于他們的宇宙觀;另一方面基于對現實政治的觀察,認為“禮”是邪亂的禍首。具體言之,老莊認為道是萬物的本原和最高主宰,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運動發展的總規律,視道為治理天下的唯一準則。老子說:“以道蒞天下”,[25]要求圣王遵守道的原則,順應自然,無為而治。莊子提出以道觀天下,要求君天下者循道無為,做到“無欲”、“無為”、“淵靜”。他說:“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26]基于此,他們站在道和“道治”的立場批評禮和禮治。老子從道和無為的視角考察道治與德(仁義)治、禮治的差別,得出結論:“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貞臣。”[27]“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28]在老子看來,“禮”是道、德、仁、義、忠、信的淡化,是邪亂的禍首;社會之所以混亂不堪,根源在于人類社會的禮法制度和知識。莊子沿襲老子的思路,全面否定禮的政治價值:“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29]這是說,道是不可以招致的,德是不可以得到的,仁是可以做到的,義是可以虧損的,禮是相互虛偽欺騙的。[30]正是基于這樣的認識,符合“大道”的社會,在老子看來應該是“小國寡民”,“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31]而在莊子眼中則是人類原初混沌狀態下的“至德之世”。[32]自然,這樣的社會是不需要“禮治”的。
3.法家否定禮治
韓非,曾師從荀卿。他主張“法治”,否定禮治,一是源于進化的歷史觀。在結合親身經歷的動蕩現實的基礎上,韓非指出“古人亟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謀,當今爭于氣力”,[33]因此,“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如守株待兔一樣可笑。[34]二是源于人性本惡的看法。基于“當今爭于氣力”的現實,他認為即使是君臣父子,其間的關系也是充滿了利己主義的打算,“父母之于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計之長利也。”[35]“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36]既然人們都在追名逐利,那么,沒有強制力的道德說教,沒有強力為后盾的“禮”自然無法達成社會的有效治理。不過要注意的是韓非的理論體系中并不是完全沒有“禮”的地位,在《韓非子》一書中的不少地方,他都流露出對于“禮”的尊重,比如,“行不忠,則大忠之賊也。”“無禮諸侯,則亡身之至也。”“國小無禮,不用諫臣,則絕世之勢也。”[37]他與儒家禮學的不同之處在于禮要符合“人主”(君主)的需要,否則就是“非禮”。[38]
綜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百家爭鳴”這一歷史現象(課)的演變邏輯:周禮崩壞——各家論禮(儒家尊禮、道家“非禮”、法家否定禮治)。
上個世紀90年代,曾有亞裔留華學生向學者葛兆光提了這樣一個問題:“老師,都說中國是儒學的故鄉,為什么故鄉沒有了儒學的禮義?”葛教授“聽了不覺悚然,一時竟無言以對”。[39]時至今日,盡管距此提問已經20多年,但這仍是需要把握和認真對待的問題。無疑,“禮”作為一種歷史現象有其時代局限,比如繁瑣的儀式規矩、等級森嚴的尊卑差別,但是,如果作為基礎教育組成部分的歷史課程只停留于此,看不到“禮”所包含的秩序、自尊、理性,看不到“禮義”所體現的“對人對己的尊敬與自重”、“對天道人理的自覺與敬畏”[40],那么“禮”在學生的頭腦中會是一種怎樣的形象呢?能激發起(學生)“對祖國歷史與文化的自豪感”嗎?有鑒于此,在教授“百家爭鳴”一課時要在“禮”上做足文章,梳理清楚先秦時期“禮”的由來、演變及諸子百家關于“禮”的思考,以便在學完“中國傳統主流思想的演變”和“近代中國的思想解放潮流”專題后,為歷史地、全面地、辯證地認識“禮”提供充分的課程知識支撐。
【注釋】
[1][2]鄒昌林:《中國禮文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331-332、14頁。
[3](美)鄧爾麟:《錢穆與七房橋世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7-8頁。
[4][21]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4年,第12-14、99頁。
[5]龔書鐸:《中國社會通史·先秦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93-498頁。
[6][17]鄭訓佐,靳永譯注:《孟子譯注》,濟南:齊魯書社 , 2009 年,第106、244頁。
[7]葛兆光:《中國思想史(第一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78頁。
[8]陸建華:《孔子之禮學》,《朱子學刊》,2005年,第384-393頁。
[9]葛志毅:《重論孔子的歷史文化定位問題》,《管子學刊》2010年第3期。
[10][12][13]黎千駒:《論語導讀(修訂版)》,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250、246、24頁。
[11]白奚:《援仁入禮? 仁禮互動:對“克己復禮為仁”的再考察》,《中國哲學史》2008年第1期。
[14][16][38]勾承益:《先秦禮學》,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第367、368、398頁。
[15]歐陽小桃:《論禮在先秦儒家思想中的地位和作用》,《江西社會科學》1989年第4期。
[18]張自慧:《禮文化的價值與反思》,上海:學林出版社,2008年,第66頁。
[19][20][22]張覺:《荀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99、393、8頁。
[23]胥仕元:《秦漢之際禮治與禮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52頁。
[24]胥仕元:《孔子、孟子、荀子之“禮”論》,《學習與探索》2008年第6期。
[25][27][28][31]陳劍譯注:《老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04、63、130、255頁。
[26][29][32]楊柳橋:《莊子譯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69、345、136頁。
[30]陸建華:《先秦諸子禮學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32頁。
[33][34][35][36][37]高華平,王齊洲,張三夕譯注:《韓非子》,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702、698、656-657、533、77頁。
[39][40]葛兆光:《關于“禮”的隨想》,《東方雜志》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