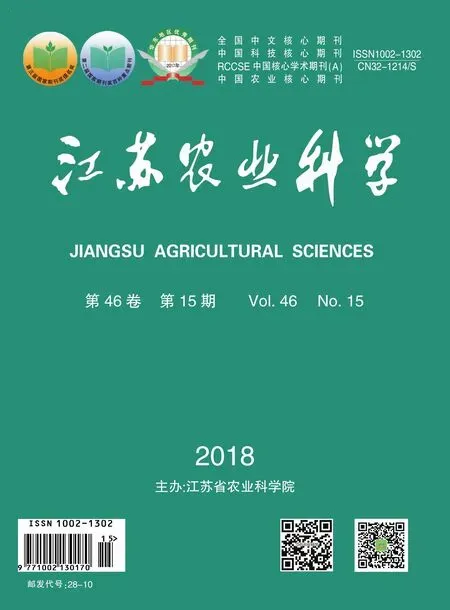施氮對高寒草原植物生長和土壤無機氮含量的影響
于 兵, 吳克寧
[1.中國地質大學(北京)土地科學技術學院,北京 100083; 2.國土資源部土地整治重點實驗室,北京 100083]
氮是植物生長的必需元素,植物的一生需要吸收大量的土壤氮素。施肥是改良草地的有效措施之一,可有效提高草地生產力。章學梅等通過對冷季型混播草坪的施肥研究發現,年施氮量為25 g/m2較合適[1]。韓建國等通過研究施肥對早熟禾(Poapretensis)草地土壤中硝態氮含量的影響,發現0~20 cm土層中硝態氮的含量受施肥影響最大,并且與肥料類型、施肥次數以及肥料量有關[2]。
草原對大自然保護有很大作用,它不僅是重要的地理屏障,而且也是阻止沙漠蔓延的天然防線,起著生態屏障作用。另外,它也是人類發展畜牧業的天然基地。草原退化、堿化和沙化、氣候惡化以及嚴重的鼠害等一系列生態問題,在全國絕大多數草原均不同程度地存在著,這是人類對草原不合理利用所造成的生態惡果。草原退化的標志之一是產草量的下降。據調查,全國各類草原的牧草產量普遍比20世紀50~60年代下降30%~50%。如新疆烏魯木齊縣,1965年草場平均產草量為1 275 kg/hm2,到1982年已降至795 kg/hm2,平均每年減少22.5 kg/hm2。草原退化的標志之二是牧草質量上的變化,可食性牧草減少,毒草和雜草增加,使牧場的使用價值下降。例如,在青海果洛地區,草原退化前雜、毒草僅占全部草量的19%~31%,退化后增加到30%~50%,優質牧草則由33%~51%下降到4%~19%。草原退化,植被疏落,導致氣候惡化,許多地方的大風天氣和沙暴次數逐漸增加。氣候的惡化又促進了草原的退化和沙化過程。我國是世界上沙漠化受害最重的國家之一。我國北方地區沙漠化面積已近18萬km2,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20年間,因沙漠化已喪失了3.9萬km2的土地資源。草原鼠害也日益嚴重,據1982年全國草原滅鼠會議反映,全國草原牧區受鼠害面積達6 600萬hm2,有的草場鼠洞密度多達 24 600個/hm2以上,使草場完全被破壞而失去使用價值。據估計,全國每年因鼠害損失的牧草約有500萬t,直接經濟損失有十幾億元。鼠害的發生既是草原生態系統平衡失調的惡果,也是造成草原生態環境進一步惡化的原因之一。
建立圍欄,實行分區輪放,合理利用草場等,都是已被證明的保護和恢復草原生態系統結構和功能的有效措施。根據中國農業科學院草原研究所的預測,若不能盡早改進目前牧業的生產經營方針,在今后的15年內,內蒙古全區草原產草量年平均下降率可達2.3%。另外,從長遠考慮,通過技術改造和適當增加投資,實行集中化經營的草業,其經濟效益更大。在畜牧業要發展、草原生態環境要保護的情況下,必須要以人工草地和種植飼料來獲得高的經濟效益和環境效益。目前我國人工草場的面積僅占草原總面積的0.4%,只是美俄等國的4%。而據專家們的估計,種植牧草0.5%~1%,可增加全部生產能力的0.5~1.0倍。可見發展人工種植牧草業是一項短期內即可獲得巨大經濟效益的措施,同時又利于草原生態系統的恢復。因此,必須加強對草原的合理利用和保護。
本研究通過對高寒草原生態系統進行不同施氮水平處理,研究不同功能群地上生物量和土壤無機氮含量對施氮的響應,以期對草地改良提供理論指導,進而為草場合理的規劃利用提供建議。
1 材料與方法
1.1 試驗時間與試驗地概況
試驗于2013年在青海剛察縣進行,剛察縣位于青海省東北部,海北藏族自治州西南部,青海湖北岸,介于99°20′44″~100°37′24″E、36°58′06″~38°04′04″N之間。剛察縣屬典型的高原大陸性氣候,日照時間長,晝夜溫差大;年降水量 370.5 mm,年蒸發量1 500.6~1 847.8 mm。冬季寒冷,夏秋溫涼,1月平均氣溫-17.5 ℃,7月平均氣溫11 ℃,年平均氣溫-0.6 ℃。該地區植被以紫花針茅為主[3-4]。
1.2 試驗處理
試驗設置8個氮梯度處理,施氮水平分別為0、1、2、4、8、16、24、32 g/m2,分別用N0(對照)、N1、N2、N4、N8、N16、N24、N32表示。采用田間隨機區組設計,每個處理5個重復,圖1為該試驗小區分布。氮肥形態為NH4NO3,分別于6月、7月、8月和9月每月月初人工噴施。

1.3 樣品采集
1.3.1 植物和土壤樣品采集 在8月20號左右,在每個小區收獲3個25 cm×25 cm樣方的植物,地上生物量的獲取采用直接收割法,采集植物地上部,烘干后稱質量。在8月份的取樣中,采用根鉆(d=8 cm)采集0~100 cm深度的土樣樣品,每10 cm一層。將鮮土樣品過3 cm孔篩后,冷凍保存。
1.3.2 植物和土壤樣品指標測定 土壤無機氮含量采用 0.01 mol/L CaCl2浸提,流動分析儀測定;土壤含水量采用烘干稱質量法測定。
1.3.3 物種組成調查 在每個試驗單元的觀測區內,設置1個1 m×1 m的非破壞性固定觀測樣方,其中設置100個 10 cm×10 cm的小方格,進行物種組成及蓋度觀測。
1.4 數據處理
數據采用SPSS 11.0軟件進行統計與分析,圖表采用Excel 2007進行繪制。
2 結果與分析
2.1 施氮對不同功能群地上生物量的影響
從表1可以看出,不同植物功能群地上生物量對施氮的響應不同。隨著施氮量的提高,禾本科植物生物量顯著增加(P<0.05)。其中,以N32(施氮水平32 g/m2)處理生物量最大,達110.3 g/m2,比對照增加了51.1 g/m2,在其他施氮處理下,禾本科生物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莎草科和雜草地上生物量對不同氮水平的響應沒有明顯規律。與N0(對照)相比,N4和N8處理可明顯增加莎草科生物量;N2、N24、N32處理對莎草科生物量無顯著影響;N1、N16處理則明顯降低了莎草科生物量。隨著施氮量的增加,雜草生物量總體上呈現增加趨勢,N16處理增加效果最為顯著(P<0.05),達 9.5 g/m2,與對照相比增加了4.9 g/m2。不同施氮處理均明顯促進植物地上部生長,其中,以N32處理對植物總生物量的增加效果最為顯著(P<0.05),達121.3 g/m2,比對照增加了53.9 g/m2。綜合看,N1處理莎草科和雜草生物量較低,禾本科生物量較大,且禾本科生物量占總生物量的93.5%,這說明總生物量的增加是因為禾本科生物量的增加;N2處理莎草科生物量增加,雜草生物量有所降低,禾本科生物量降低,總生物量降低,說明總生物量的降低是因為禾本科生物量的降低。

表1 8月不同氮素梯度下的不同植物功能群生物量
注:表中數據為平均值±標準誤,每列中數字后不同小寫字母表示處理間差異顯著(P<0.05)。
2.2 施氮對土壤無機氮含量的影響
2.2.1 施氮對土壤硝態氮含量的影響 從圖2可以看出,與N0(對照)相比,各施氮處理在不同程度上增加了土壤硝態氮的含量。不同施氮處理土壤中硝態氮含量由大到小表現為N32>N24>N16>N8>N1>N2>N4>N0,其中,N1、N2、N4、N8處理土壤硝態氮含量的增加不顯著(P<0.05);N16、N24、N32處理顯著提高了土壤硝態氮的含量(P<0.05)。總體而言,土壤中硝態氮含量隨著施氮量的增加呈增加趨勢。
2.2.2 施氮對土壤銨態氮含量的影響 不同氮素梯度下土壤銨態氮含量變化的柱狀圖(圖3)顯示,各施氮處理土壤中銨態氮含量由大到小表現為N24>N16>N1>N32>N2>N4>N8>N0,說明各施氮處理均不同程度增加了土壤銨態氮含量,但是土壤銨態氮含量無明顯隨施氮量變化的規律。與N0(對照)相比,N4、N8處理對土壤中銨態氮含量影響不顯著(P<0.05);N1、N2、N16、N24、N32處理對土壤中銨態氮含量增加效果較為顯著(P<0.05), 其中N24處理對土壤中銨態氮的含量增加效果最為顯著(P<0.05)。綜上所述,施氮可以增加土壤銨態氮含量,但隨施氮量的增加,土壤銨態氮含量無明顯的變化規律。


2.3 不同土壤深度無機氮含量分布
如圖4所示,同一施氮水平下,硝態氮在表層土壤(0~20 cm)中含量最高,隨土層深度增加而減少。硝態氮在表層土壤(0~10 cm)中含量隨著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在N0、N1、N2、N4、N8施氮水平下,土壤硝態氮含量隨土壤深度的加深而不斷降低,與N0(對照)相比,N1、N2、N4、N8對不同土層硝態氮含量影響不明顯。N16、N24、N32處理對土壤硝態氮含量影響明顯,且在土壤深度0~30 cm的含量較高,在土壤深度30~50 cm土壤硝態氮含量隨土壤深度的加深而不斷降低。這與8月份降水較多,土壤硝態氮明顯向下層土壤轉移有關。如圖5所示,土壤銨態氮含量在土壤表層較低,隨土壤深度的加深土壤銨態氮含量不斷增加,但不同氮處理并沒有明顯影響各土層中銨態氮含量。

2.4 不同施氮處理土壤含水量隨土壤深度的變化
由圖6可以看出,土壤含水量隨著土壤深度的增加而下降。不同施氮處理條件下,土壤含水量隨土壤深度變化規律一致,在土壤深度0~20 cm范圍內土壤含水量較高,土壤含水量隨土壤深度的加深而增加;在土壤深度20~50 cm,土壤含水量隨土壤深度的加深而減少,且在土壤深度50 cm時,各施肥處理的土壤含水量均最低。


2.5 土壤銨態氮、硝態氮含量與地上總生物量的關系
如圖7所示,地上總生物量與土壤中硝態氮含量呈正相關,其中r2=0.660 9,P=0.014 1<0.05,達到顯著水平。地上總生物量與土壤中銨態氮含量沒有明顯相關性(圖8)。


3 討論
3.1 施氮對地上生物量的影響
本研究中,從草地禾本科、莎草科及雜草等生物量來看,N0(對照)處理顯著低于其他7個施氮處理(P<0.05),說明適量施氮能明顯促進草地草的生長,這與韓建國等通過盆栽試驗得出的結論[5]一致,可以說明施氮能夠明顯增加草坪草的生長量。但是并不是施氮量越大,草坪長得越好,當施氮量高于8 g/m2時,植物地上生長并不隨著施氮量的增加而增加。氮肥作為草地植物需求的大量元素,合理的氮素釋放效率可以供給草地正常生長所需的養分,氮素釋放不足或超過范圍都會導致莖葉的凈光合速率、呼吸速率及其他生理反應相應地降低,從而影響地上生物量[6-7]。高寒草原不同植物類群的地上生物量對增施氮肥的反應不同,其中禾本科的反應最大,雜草次之,莎草科變化最小。有研究表明,高寒凍原的相對干燥的草甸禾本科植物的豐富度在施氮后明顯增加,莎草科沒有明顯變化[8]。禾本科在土壤氮肥增加的狀態下生長茂盛,但在對照區生長穩定,即可認為禾本科在養分充足下對養分的利用效率高,但在養分受限制甚至缺乏的條件下,對養分的競爭和適應方面屬于“弱者”。當養分停止增加或其他因素導致土壤養分不足時,禾本科生長則受到抑制。本研究中,雜草對增施氮肥的反應不敏感,當施氮量為1 g/m2時,雜草地上生物量明顯低于對照,說明施氮在促進禾本科生長的同時,在一定程度上相對抑制雜草的生長,這與沈振西等的研究結果[9]一致。以苔草為主的莎草科植物對施氮的不敏感性,使其得以在養分條件較好的環境中始終保持一定的穩定性,一旦人為施肥停止或由于放牧等原因使養分資源受到限制時,莎草科的這種低養分的需求特性優勢就會表現出來,這也就是為什么在中度放牧條件下莎草科會成為群落優勢種的原因之一。
本研究是在野外條件下進行的控制試驗,對自然大氣降水無法控制,特別是近年來降水量及其季節性分配波動較大,降水量的變化肯定會對施氮效果產生影響,這是沈振西等證實過的結論[9]。但是本研究是針對2013年8月份數據,8月降水較多,土壤含水量較高,含水量隨著土壤深度的增加而下降。草原植物的優勢種禾本科植物在6—7月處于旺盛生長階段,特別是施氮后(7月份)對水分的需求量較大,而此時降水量的多少以及分布是否均勻就很關鍵,直接影響施氮的效果,如土壤水分不足則易產生水分脅迫,加劇干旱的程度,從而影響植物對氮的吸收。但是本研究中8月降水較多,土壤含水量較高,因此對施氮的影響效果不明顯。適當地增加施肥量有助于提高表層土壤的含水量,同時可以明顯提高植株對深層土壤水分的吸收,水分也是該地區植物生長發育的主要限制因子。
3.2 施氮對土壤無機氮含量的影響
土壤中無機氮含量包括硝態氮和銨態氮含量。本研究中,不同的施氮處理與對照相比,增加了土壤無機氮含量,無機氮含量的增加是因為土壤中硝態氮含量的顯著增加(P<0.05)。低氮處理對土壤中硝態氮和銨態氮的含量增加效果不顯著(P<0.05),高氮處理顯著增加土壤中硝態氮和銨態氮的含量,說明合適的施氮量會增加植物的吸收,但是過高施氮,則會增加土壤中硝態氮的殘留。結果表明,在32 g/m2施氮水平下,土壤中硝態氮的含量達到最大值。隨著施氮量增加,氮的淋溶損失也隨之加大[10]。本試驗結果與以上結論一致,說明氮肥施用量和土壤中硝態氮含量密切相關,施氮量越高,草地土壤中硝態氮含量越高。
已有研究指出,同一施氮量水平下硝態氮在表層土壤(0~20 cm)中含量最高,隨土層深度的增加而減少[11]。本研究與其一致,這主要是因為氮肥隨著水分的下滲進入不同的土層,在根系層達到最大含量。另外,也可能是因為根系層的微生物活動及相關酶活性比較強,利于氮素的積累。同一施氮量不同深度比較,0~20 cm土層中硝態氮含量大于20~30 cm、30~40 cm和40~50 cm土層的硝態氮含量。
土壤銨態氮含量在土壤表層0~10 cm較低,隨土壤深度的加深,土壤銨態氮含量不斷增加,但銨態氮含量隨施氮量的變化無明顯變化規律。這表明銨態氮在下層土壤中分布較高,但與施氮無關,可能是由于銨態氮容易被土壤吸附和固定,不易流失。這說明在土壤生態條件下,土壤銨的釋放有自己的規律。土壤銨態氮的含量受黏土礦物類型,NH4+、K+、有機質含量,土壤質地,全氮量及其他陽離子等的影響,黏土礦物銨態氮含量和固定外源銨的潛力因土壤類型、管理措施和干濕交替而異[12]。NH4+固定受水分影響較大,廖繼佩等對湖南省黃泥田土壤的銨態氮含量研究結果表明,銨態氮含量由大到小依次為干濕交替8次>長期干燥>長期淹水,因為其主要黏土礦物是蒙脫石,濕潤不利于銨的固定[13]。說明在植被生長過程中調節土壤水分可以有效調節銨態氮含量。我國土壤銨態氮含量在 35~573 mg/kg變動,平均為 198 mg/kg,約占土壤全氮的 17.6%[14]。可見,銨態氮是土壤氮素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作物生長期間,土壤中的銨態氮可以釋放出一部分[15];因此,銨的礦物固定和釋放是土壤氮素內循環的重要環節之一,它導致土壤具有較強的“穩肥性”。
地上總生物量與土壤中硝態氮含量呈正相關,而地上總生物量與土壤中銨態氮含量的相關性不明顯。這是因為草原植物所需氮素主要來源于硝態氮,為滿足植物生長需要,表層土壤中銨態氮大量轉化為硝態氮。
4 結論
施氮能促進植物生長,增加植物地上生物量,但是高寒草原不同植物功能群對增施氮的反應不同,禾本科植物對氮肥增加的反應最大,莎草科和雜草類植物對施氮的響應并沒有表現出明顯規律。高寒草原施氮量為8 g/m2最適宜,既能保證植物地上生物量達到最大,又能夠降低土壤硝態氮淋溶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