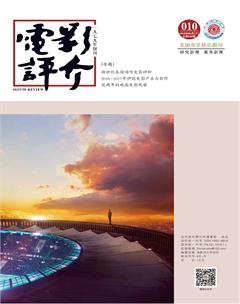2016—2017年伊朗電影產業與創作
黃含
2016—2017年,是伊朗電影發展較為平順的一個階段,出彩的電影作品數量與過往相比稍顯不足,但作為后起之秀的創作人才數量越來越多,并紛紛獲得國際肯定,這成為目前伊朗電影發展的常態。
一、 2016—2017年伊朗電影產業現狀和數據分析
2016年至2017年,伊朗政府持續鼓勵和引導國產電影產業的發展政策已初見成效,伊朗藝術電影在國內外繼續如魚得水,本土商業電影也呈現為恢復性發展態勢,電影票房市場有初步回暖的跡象。
(一)2016-2017上映國產電影數量及總體票房市場[1]
2016年伊朗國內總共上映電影60部,與近三年影片上映數量基本持平。其中,2016年伊朗國內電影上半年上映電影數量為20部,下半年上映了40部影片,包括成為票房冠軍的《推銷員》。
2016年伊朗國產電影在本土院線票房得到了恢復性增長,全年伊朗國內電影前十大總票房為246萬美元,與去年159萬美元相比大幅增長,而且超過2015年電影總票房,相比2014年的票房飄紅,院線票房仍有很大的差距,受到伊朗政府的文化產業政策的影響十分明顯。
從單一影片的票房來看,全部上映的60部影片里,有32部票房超過了10億里亞爾,其中,超過百億的有6部,在50億與百億之間2部,票房在10億與50億之間的影片有24部,整體票房構成較為合理。
從百億票房電影數量來看,2016年伊朗上映的伊朗本土電影有6部電影進入100億俱樂部。2014年有9部、2013年時有6部、2012年與2011年均有5部達到百億,伊朗國內電影票房正在回暖。
(二)2016年度票房冠軍:《推銷員》
在2016年伊朗國內電影票房市場平穩發展的情形下,伊朗導演阿斯哈·法哈迪導演的新片《推銷員》成為年度票房之冠。雖然《推銷員》在國際上聲譽斐然,然而在伊朗國內的年度總票房約合38萬美元,僅為2014年票房冠軍國產粘土動畫片《老鼠城市2》200萬美元的票房紀錄的1/5,為近年最低水平。
(三)2016年票房類型
2016年伊朗本土商業電影,一大批劇情作品進入院線,在伊朗商業類型片市場的疲軟現狀下,使得伊朗電影在2016票房取得了教好成績。從票房排行前十的伊朗電影類型來看,受伊朗大眾喜愛的仍然是劇情片和喜劇片。[2]2016年全年電影票房前五名依次是《推銷員》(Salesman)、《我不是薩爾瓦多》(Im not Salvador)、《五十公斤酸櫻桃》(50 kilos sour cherry)、《你好孟買》(Hello Mumbai)、《不朽與一天》(Eternity & a day),包含3部劇情片和2部喜劇片。
2016年伊朗國內電影票房市場不論是從上映影片的數量、影片的整體票房,還是影片的質量情況來看,伊朗電影創作和電影市場已經呈現回暖跡象,尤其是劇情片和喜劇電影的發展勢頭較好。
二、 2016—2017年伊朗電影創作概況和藝術成果分析
2016年至2017年的伊朗電影創作不似前一年那么碩果累累,在文化政策相對收縮,國際局勢相對復雜的現實因素面前,伊朗電影依然頑強地在本土和世界影壇開拓著自己的疆域。電影題材類型不斷豐富,日趨多元化,同時伊朗中生代電影導演和伊朗青年導演在本年度形成奮起之勢。《納德與西敏:一次別離》的導演阿斯哈·法哈蒂再出佳作,胡曼·薩耶迪等為代表的年輕一代導演也積極地在伊朗國內外電影節的平臺上找尋自己的位置。這些年輕導演已經擺脫了青澀,影片主題和風格更為成熟和穩定。比起老一輩伊朗電影人,新生代導演更關注伊朗社會邊緣人群和尖銳的社會問題,注重對敘事手法和個性表達的藝術化探索,不再僅僅滿足于將伊朗新電影的特質作為樹立自己作品的標桿,但他們依然對嚴肅主題有關切態度,依然繼承了伊朗電影的人文主義傳統。
(一)再臨奧斯卡
2016—2017年度,伊朗電影界最受到關注的作品莫過于阿斯哈·法哈蒂的《推銷員》。在贏得了第69屆戛納電影節最佳劇本獎和最佳男演員獎后,該片又一舉拿下了2017年美國電影學院獎的最佳外語片獎。作為影片導演的阿斯哈·法哈蒂也第二次成為奧斯卡的寵兒。早在2012年,他就憑借電影《納德與西敏:一次別離》征服奧斯卡,也創造了伊朗電影第一次留名奧斯卡的歷史。該片延續了法哈蒂以往作品的戲劇張力,劇情引人入勝,同時也在2016年伊朗本土電影票房市場表現疲軟的境況下,一躍成為當年的票房總冠軍,實現了在伊朗國內外電影市場與觀眾口碑的雙豐收。
(二)新銳導演再發力
青年導演雷扎·多米西安(Reza·Dormishian)的電影《劫富幫》(Latouri),關注伊朗當下嚴峻的社會問題以及年輕一代對此的態度,影片以新聞采訪的形式,與所謂的犯罪分子面對面接觸,揭開了激進的犯罪團伙“劫富幫”的面紗。電影講述了在伊朗社會貧富差距依然過大,男女極度不平等的現狀下,一群游蕩在德黑蘭街頭的社會青年組成了犯罪組織,他們專門將通過收取不義之財或侵占國家資產發家致富的家庭的子女鎖定為目標,通過搶劫和綁架他們來實現劫富濟貧的愿望。獨具匠心的偽紀錄片的外殼下,影片通過對犯罪團伙成員們、社會學家、人權活動家、政治強硬派等社會各階層人士的訪談拍攝,道出了人在伊朗社會所承受和面臨的巨大挑戰——貧富差距過大、男尊女卑、宗教制約,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問題。[3]盡管劫富幫試圖通過激進的暴力方式謀求社會問題的解決之道,然而由于社會大環境所造成的矛盾沖突依然蔓延到了團伙內部,在影片后半段因愛生恨的一段故事中,幫派成員之間也開始以伊斯蘭“以眼還眼”的復仇法則相互傷害。這部充斥著憤怒情緒的影片是對當下伊朗國內年輕一代心態的真實寫照,也反映出伊朗年輕人對改良社會文化環境的渴望。影片票房成績進入2016年的伊朗本土電影票房市場前十,其受歡迎程度可見一斑。
伊朗新銳導演胡曼·賽耶迪(Hooman Seyedi)的新作《喧嘩與騷動》(Sound and fury)獲得了2016年伊朗曙光旬電影最佳攝影獎項。早在2015年,塞耶迪執導的影片《13》就獲得了第18屆上海國際電影節亞洲新人獎的最佳影片獎和最佳攝影獎,該片也曾在2014年的韓國釜山電影節獲得“新浪潮獎”。這一次賽耶迪的新片主角不再是成長中的少年,轉而關注作為公眾人物的青年男明星。《喧嘩與騷動》男主角闊斯羅是一個受到熱捧的歌星,他脾氣火爆,富有魅力,與妻子和五歲大的兒子生活在一起。在遇到了瘋狂迷戀自己的女粉絲漢娜后,闊斯羅陷入了婚外戀情,然而隨著闊斯羅妻子的死亡,他的生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切都顯得撲朔迷離起來。這部電影與《13》一樣充滿了焦躁的情緒,低沉壓抑的配樂和攝影氛圍與經典好萊塢的懸念設置相得益彰,凸顯出主人公動蕩不安的經歷與起伏的內心活動。
(三)中國電影節上的常客
馬爾加·阿莎菲扎德(Marjan Ashrafizadeh)的電影《姐姐》在2017年的北京國際電影節上大放異彩,獲得了最佳女主角的獎項和最佳影片的提名。這部講述親情的影片,聚焦伊朗病殘母女的家庭生活。影片以質樸的鏡頭語言,為觀眾呈現出了伊朗人深厚的家庭觀念和血濃于水的親情觀,對傳統伊朗新電影的主題與風格有一定繼承。導演穆斯塔法·塔吉扎德赫(Mostafa Taghizadeh)的電影《籌款風波》在2017年的上海國際電影節上斬獲了最佳評委會大獎與最佳女主角兩項重量級獎項。
(四)伊朗驚悚/恐怖片受到關注
旅英伊朗導演巴巴克·安瓦里(Babak Anvari)的電影《陰影之下》在2016年上映后廣受好評,這也是繼2014年的電影《獨自夜歸的女孩》之后,又一部伊朗穆斯林文化為背景的恐怖驚悚題材影片。《獨自夜歸的女孩》中殘破不堪的伊朗邊陲小鎮和吸血鬼身份登場的穆斯林黑衣少女荒誕而迷人,但其不明的語義和實驗氣質沖淡了觀眾對影片的強烈感受。《陰影之下》則成功將捕捉到伊朗人對兩伊戰爭的復雜心理,通過女主角同惡魔的周旋與斗爭,來窺視戰爭對人性帶來的摧殘和傷害,以及人們是如何自我如何修復與療愈的過程。影片將戰爭對人造成的心靈傷害轉化為披著黑袍的惡魔形象,合理放大了女主角的脆弱心理——正是其在戰爭中的強烈恐懼感引發了惡魔的降臨。然而不愿失去女兒、丈夫、友鄰以及不愿失去自己所擁有的生活的強烈愿望,最終促使她變得強大,在跟惡魔的纏斗中,依然要向著前方前進。
三、 2016年伊朗電影案例分析
《推銷員》的故事發生在伊朗首都德黑蘭。艾麥德和拉娜所居住的公寓樓瀕臨倒塌,很快二人搬進位于另一棟公寓天臺的新居。排演完話劇后的一個夜晚,先行回家的拉娜被人襲擊。遇襲后的拉娜變得神經質,令丈夫感到不安,艾麥德逐漸對拉娜失去了耐心,他開始尋找傷害拉娜的那個人。在對蛛絲馬跡的追蹤中,艾麥德最后鎖定了嫌疑人,但給予施暴者的審判與懲戒似乎并未給這對夫妻帶來救贖和希望。
(一)承接主題:伊朗都市中產階級的迷思
縱觀在國際影壇上大放異彩的伊朗電影,會發現伊朗電影題材變得豐富,類型也越來越多樣化。然而細數那些為人熟知的伊朗電影,大多都直接或間接揭示著伊朗底層民眾貧困、落后的生活狀態,在國際銀幕上鮮少見到伊朗不斷發展中的現實國情或者伊朗的現代都市文化,阿斯哈·法哈蒂的電影填補了這塊空缺。他的電影主題圍繞著都市中產階級生活、家庭內部關系展開,導演在過去的作品如《煙火星期三》《關于伊麗》和《納德與西敏:一次別離》,均是以小見大的嘗試。導演以中產階級的婚姻生活為切入點,討論置身現代生活中的伊朗人是如何處理婚姻和家庭矛盾的同時,通過對人們日常生活的細膩記錄與刻畫,來展示出伊朗人民對伊朗國家和社會現狀的某種態度。同時,也試圖在保守的政治氛圍下隱晦地向觀眾拋出伊朗人對日常生活中出現的女性問題、宗教束縛以及現代性沖突的種種疑問。
(二)延續風格:紀實美學與懸念設置
《推銷員》延續了法哈蒂作品的一貫風格,即伊朗電影中一以貫之的紀實美學特征和導演對故事懸念迭起的情節設置。影片用干凈簡練的鏡頭語言自然地呈現了夫妻二人的居住空間和德黑蘭的街頭巷尾,在長鏡頭和手持攝影下,演員褪去表演痕跡的生活化展示,為影片增添了紀實感。對打掃屋子、鋪疊被子、做晚餐等日常生活的細膩展示,讓觀眾能快速接受和融入普通伊朗人的生活狀態。法哈蒂用客觀的視角來呈現影片內容,當拉娜在家坐立不安四處走動時,手持攝像機一直保持了冷靜的記錄,但觀眾仍可以通過攝影畫面的輕微顫抖和晃動感受到受傷后的女主角所承受的焦躁與不安情緒,這種無處不在地對觀眾視角的觀照使影片敘事顯得更加真切有力。盡管影像鏡頭前的生活看似波瀾不驚,但導演巧妙地利用故事情節,將懸念植入到瑣碎的生活細節中,通過看似不起眼的細節來將懸念層層推進,大多依賴對話,比如夫妻二人之間的對白,與鄰居和朋友支支吾吾的交談,以及丈夫走街串巷尋找施暴者的詢問等等。人物間的矛盾和沖突隨著談話不斷被醞釀的情緒不斷升級,最終在懸念揭曉的那一刻,影片劇情也達到高潮。拉娜受到傷害之后,看似沒有什么大變化的家庭生活變得暗潮洶涌,法哈蒂將這種懸念的設置隱藏于中,人與人互相之間的來往,不經意間經過的街巷、景物和及其平淡的日常對話都被導演安排作為揭開謎底的鑰匙,觀眾感受到的正是導演在影片現實主義的外殼下精心布置劇情所引發的,非同尋常的戲劇張力。與《納德與西敏:一次別離》的片尾一樣,夫妻二人坐在離婚辦理現場頹然無聲,《推銷員》的片尾依然使用了開放式結尾,在對施暴的老人進行了寬恕和報復之后,夫妻二人分別坐在劇場更衣室里各懷心事,黯然神傷,影片戛然而止。究竟他們的未來何去何從,是否能夠相互寬恕渡過難關,觀眾不得而知,這也成為導演留下的最后一個懸念,為影片增添了耐人尋味的涵義。
(三)尋求理解:“伊朗式關系”與“破碎美國夢”的互文
值得注意的是,導演在《推銷員》中設置了夫妻參演阿瑟·米勒的話劇《推銷員之死》的情節,嘗試著將話劇內容與影片內涵虛實結合,形成互文。作為揭示“美國夢不再”的一部杰出劇作,阿瑟·米勒的《推銷員之死》被伊朗中產階級搬上舞臺,劇場的排演表面上看似乎與現實生活空間所發生的劇情缺乏關聯,然而從本質上有著極其相似之處。《推銷員之死》立足美國中產階級的生活,通過一家人內部的關聯與斗爭,表現出美國民族價值觀念的問題。美國夢作為理解美國文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在戰后經濟膨脹所帶來的物欲主義下,已經喪失了原本具有的個體精神價值與道德尺度,這也為像男主角這樣的中產階級帶來了思想和物質上的空虛與疲勞。現實空間中扮演話劇男主角的伊朗男子艾麥德和他的妻子拉娜也面臨著物質與思想的雙重壓力,其樂融融的生活表象下,稍有外力的沖擊,看似穩固的夫妻關系、社會關系就顯露出疲態,他們同樣面臨著來自民族文化個性和倫理道德的制約。他們在舞臺上排演來自美國的話劇,可以依照劇本就生活的挫折與不幸采取美國式的指責和發泄,當離開舞臺回歸現實生活,卻礙于自身文化的保守性和男權主義的禁忌,只能對發生在自己或家人身上的不幸選擇緘默。這種道德禁忌和文化壓抑的氛圍,也束縛了夫妻之間的情感交流,拉娜渴求丈夫的關愛,卻沉浸在無法言說的痛苦中,并且難以相信丈夫會全身心再接納受過傷害的自己,艾麥德試圖理解和愛護妻子,卻無法忽視自己受到打擊和羞辱的心情,壓抑的情緒不斷累積,導致夫妻雙雙走入了偏執的境地。話劇內外反映出的依然是現代生活帶給都市中產階級人群的焦慮與壓抑,以及對掌控生活的無力感。劇場空間和現實空間在劇情的巧妙串聯下,構成完整的故事鏈,組成了艾麥德與拉娜的白天與黑夜,也成為跨國度、跨民族、跨文化的全球化語境下,都市人群所面臨的共同處境。
(四)鏡中伊朗:不可言說的罪與罰
推動《推銷員》矛盾沖突不斷發展的影片內核,是拉娜出事所引發的羞辱感。羞辱感成為了驅動當事人行為的重要因素。拉娜在洗澡時被男性襲擊,無論是對于作為丈夫的艾麥德還是拉娜自己都是非常敏感的一個話題,當偶然發現施暴者有意留在現場的現金后,一種可怕的事實似乎得到證實——拉娜被侵犯了。兩口子不約而同選擇了克制和緘默的態度,身體的傷害并不是重點,而名譽的受損才是關鍵。拉娜作為當事人,對自己是否受到侮辱的事情應該是清楚的,但她模糊地交代過去,并且變得敏感和焦慮。原本在夫妻關系中屬于拉娜的相對平等的地位,在她受辱后,似乎也發生了改變,拉娜對自己在家中地位有了界定:她成為了一個不純潔的女人,這無疑是丈夫介意的。在伊朗這樣一個男權至上的國家,自己的妻子受到其他男性的侵犯,是對艾麥德自尊心的巨大打擊。在妻子拉娜羞辱與丈夫艾麥德的羞辱感與日俱增的情況下,艾麥德不惜一切找出施暴者,意欲將這種羞辱感還贈給他,通過懲罰對方來獲得自己精神的平復。施暴拉娜的老人也不得不面對他的恥辱——當艾麥德執意要在老人結發妻子、女兒及女兒未婚夫面前揭穿他的真面目時,老人崩潰了,不惜一切甚至賠上性命,只為維護住他的名譽和尊嚴。從中觀眾看到了伊朗社會的深層心理:男權主義至上和群體個性壓抑。拉娜究竟有沒有受到侵犯,受侵犯到哪一步已經變得不重要,艾麥德為了搞清楚真相挽回男性尊嚴甚至不理會拉娜的感受,擅做主張讓她與老人對峙,片尾艾麥德不甘心地將老人再度置于死地的做法,暗示出在男權至上與階級分化明顯的社會現狀下,伊朗中產階級人群正面臨著來自婚姻家庭和法律道德的嚴峻考驗。
參考文獻:
[1]2011—2016伊朗本土電影票房市場數據[EB/OL].(2017-09-10)[2018-05-02]The database 1390-1395:Farabi Cinema
Foundation,FCF(http://fcf.ir).
[2]波斯電影票房研究[EB/OL].(2017-09-05)[2018-05-02]Film search from Persian movie(https://www.cinematicket.org).
[3]2016值得關注的5部伊朗電影——不離社會問題,摸著形式的石頭過河[EB/OL].(2017-1-11)[2017-8-23]http://cinephilia.
net/47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