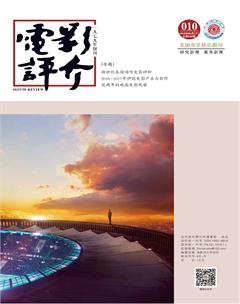《彗星來的那一夜》:科幻與人文的交叉地帶
王昌杰 宋自容
科幻片是電影類型片的一種,它的興起可追溯至20世紀20年代,經過近百年的發展,科幻片已架構起一套完整的創作體系與分類標準。從披著影視外衣的概念教學,到科學理論的具象化呈現,軟科幻的出現,真正實現了藝術想象、科學觀念、電影語言三者的結合。《彗星來的那一夜》便是一部典型的軟科幻影片,它將艱深的量子力學代入實際生活中,通過模擬聚會的方式,闡述了平行時空、相干性等物理概念。同時,本片也糅合了懸疑、驚悚等元素,進一步拓展人物維度,大膽解剖人性的弱點,在科學幻想與現世沖突之間找到了平衡。
一、 科學幻想:物理概念的影像化詮釋
“科幻”即科學幻想的簡稱,顧名思義,科學應是科幻片的第一要義。一旦失去強力可靠的理論支撐,僅靠想當然的猜測去完成劇情,影片便會誤入奇幻的領地,從而無法構筑令人信服的未來世界。然而,隨著該題材的不斷衍生發展,未來已不是科幻唯一的時間舞臺,許多電影開始嘗試將物理知識,合理地運用于當下,創造出一個充滿了未知性的現行世界。例如,經典的《時光倒流七十年》《蝴蝶效應》,以及《恐怖游輪》等近期優秀作品,其敘事手法均是科學理論搭臺,人物情感唱戲,大幅度增強了影片的可看度。盡管也摻雜了愛情、懸疑、心理等類型要素,但這些都是存在于電影藝術層面的內容,并未動搖基礎理論的根基。本片的創作理念也大致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彗星來的那一夜》并無任何修飾場景,其統一連貫的內部邏輯,完全是由細節與對白拼湊而成,這在同類題材中是極為少見的。
(一)平行宇宙理論
平行宇宙是指多元宇宙的合集中所包含的各個宇宙。其概念的出現可追溯至20世紀50年代,美國物理學家休·埃弗雷特率先使用“多世界”一語來解釋量子力學,盡管這一理論的真實性至今還存在爭議,但經過數十年的發展,平行空間的研究成果較為全面,知識體系也相對完善,足以用來支撐一部科幻電影。拋去它繁復的物理學定義,平行空間與人的相對關系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即“在當前世界沒有實現的東西,在另一個世界實現了”,而本片正是借助彗星的天文現象,來證明空間并行存在的合理性。
由于片中存在著無限個房子,人離開當前的房子后,就永遠不可能回到原有時空,經過多次的打亂重組,角色的身份顯得十分混亂,走馬觀花式地觀看電影,顯然無法梳理清楚情節的脈絡。因此,導演設置了大量的細節,讓它們成為遍布整個影片的線索,根據這些隱性的提示,本片的主線劇情和內涵思想便不難理解。大部分的細節線索以實物的方式表現出來,服飾、家具甚至一個小小的道具,都有可能對情節發展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休頭部的創可貼、李的眼鏡框、艾米的戒指,從這些物品本身來看,似乎都十分不起眼,然而,當我們將細微的變化與劇情結合在一起,它們便成了角色身份的最佳證明。盒子中的隨機物體與熒光棒的顏色,又可以作為群體與群體間相互區別的標識。此外,開場聚會的對白中也隱藏著許多伏筆,例如艾米所講的案例,芬蘭警方接到一位婦女的自首,她聲稱昨天殺死了自己的丈夫,事實上,他的丈夫就在眼前,可她卻并不認同。這個故事可以看作平行宇宙理論的簡化版,且暗喻著艾米本人的生存狀態,她在結局時選擇殺死另一空間的自己,恰好重演了故事中替代與穿幫的悲劇。《彗星來的那一夜》對平行宇宙的表現手法以細節見長,就好比軀體微小的螞蟻,能夠撼動自己體重數十倍重的物體一樣,軟科幻影片中任何一個細入毫芒的鏡頭,都有可能被賦予了舉重若輕的力量。
(二)量子疊加理論
1935年,奧地利物理學家薛定諤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思想實驗,通過宏觀世界中貓的生死疊加,推導微觀量子的存在方式和運動行為,而《彗星來的那一夜》完全可以視為影視層面上“薛定諤的貓”的重演,值得注意的是,它所模擬的不是單純的猜想,而是盒子打開后的結果。
在家庭聚會的背景下,該理論中的盒子被轉化為了房子,而深夜的停電,四周一片漆黑,房中人完全無法了解外界的情況,而外界也很難得知“貓”的生死,兩相呼應恰好顯示了結果的不確定性。房子中的兩個人貿然外出,回到房間的卻是另一時空的他們,這讓其他人意識到了空間的錯亂,就如八個人所投擲的骰子,可能出現從一到六等多個數字,且機會均等,任何微小的舉動都有可能導致世界的分叉,當骰子停止轉動,世界便坍縮為唯一的結果。隨著越來越多意外事件的出現,整個時空像滾雪球一樣極速膨脹,結局如樹杈一般逐漸增多,最終通往不同的結局,這便是“薛定諤的貓”實驗所表達的量子疊加理論。為了讓觀眾擁有更為直觀的感受,攝像機全程跟拍艾米,以她作為時空交錯中的唯一標桿,以她所處的房子來對應理論中的盒子。穩定參照物的出現,為觀眾的開放推理提供了可能,同時也避免了不必要的過度解讀。
影片的原名為“coherence”,譯作相干性,這個名稱顯然比頗具文藝氣息的中譯名更合理。在本片的理論體系中,平行時空是始終存在的,彗星的出現也只是開啟交叉點的一個契機,真正主宰情節走向和人物心理變化的,是經過不斷坍縮后的唯一結果。
二、 現世沖突:人物心理的全方位剖析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科幻片開始了其內部轉型過程,外星、宇宙、未來等傳統題材仍然占據主流地位,但許多電影人已經意識到,硬科幻電影存在著許多先天不足。除題材同質化、人物扁平化外,硬科幻電影普遍看重科學的理論邏輯,而忽略了影片情節的內在邏輯,好比一幢美輪美奐的摩天大廈,極具視覺沖擊力,當觀眾充滿興致地走入其中,卻發現內部空空如也。作為同類題材中的后起之秀,軟科幻電影表現出對社會、人性、心理、制度的關注,以科學的幻想情境為基礎,展開層次豐富、沖突強烈的敘事,彌補了科幻片的情節空白。
(一)外界沖突
電影角色的矛盾沖突主要由三方面組成,與內因主導的人際沖突、內心沖突相比,外界沖突具有較強的客觀性與不穩定性。在《彗星來的那一夜》中,外界沖突來自于不確定的另一群體,即“盒子外”的自我復制品,當八人意識到房間外存在著另一群人時,他們無不表現出極大的恐慌與焦慮。手持攝影在此時便發揮出了理想的效果,劇烈搖晃的鏡頭,似乎在暗喻著人物內心的躁動不安,簡單器材營造出的隨意感,恰好符合八人在這一時空碰面的偶然事件。使用這種類似家庭DV的拍攝方式,本是為了節約成本,出人意料的是,它恰好還原了光影的相互追逐、色彩的明暗交織,讓整個畫面蒙上了一層粗糙的真實感,與許多盲目追求華麗場面,甚至脫離于劇情外的影片相比,無疑是一次“弄拙成巧”。
在影片的開場,麥克便已對外界環境提出了大膽的猜想,認為對方可能是自己陰暗面的化身。隨著越來越多的外出偵查,平行時空的相干性不斷增強,人人自危的局面開始出現,殺戮還是共處,成為八個人必須思考的問題。在平行宇宙的理論中,同一時空只允許一個自己存在,和平相處顯然是天方夜譚,當麥克等人起了殺念時,房子外的“麥克”卻也做出了相同的舉動。顯然,所謂的黑暗版本不過是一個偽命題,真正的黑暗潛藏于人性深處,面對外界的不明威脅,魚死網破似乎是唯一的解決方式。其中艾米一行四人外出的情節,非常具有代表性,行走在漫無邊際的平行世界,乍然出現的熒光棒,觸目驚心的紅光與黑夜,形成了強烈對比,紅色代表著鮮血、不詳與殺戮,暗示了幾位主人公的心理活動。本片在外界沖突的表現上,并不拘泥于尋找差異,而是嘗試著挖掘人類內心最深處的黑暗,在未知的外在威脅之前,人們紛紛隱去了善,暴露出惡,步調一致地選擇了殺戮,這種帶有強烈情感色彩的表達手法,無疑是另類而富有震撼力的。
(二)人際沖突
人際沖突的實質是一種對立狀態,它不僅存在于兩兩之間,還可能存在于一個較大的群體內部。軟科幻電影以超驗主義的視角,解讀人與人、人與群體的關系,從角色間形成的各種效應中,抽離出相關的社會性邏輯。從這個角度而言,《彗星來的那一夜》可以說是不遺余力地渲染了八人間的緊張氣氛,展現出人們在災難面前的猜疑、魯莽,甚至自暴自棄。影片的開場,參加家庭聚會的幾個人表現得親密無間,整體氛圍輕松。導演為此刻意安排了大量的即興表演,在長達十分鐘的長篇談話中,演員可以隨機選擇話題,隨意發表看法,以此達到貼近生活的效果。彗星來臨后,為了表現整個人群的心理偏差,導演開始頻繁地插入配樂,這些樂曲均低沉平緩,缺乏節奏感,給人以壓抑無奈之感。突發音效的使用,又制造出驚悚懸疑之感,在彌補節奏空白的同時,與開場的溫馨氣氛形成對比。長對白與配樂的合理使用,與前文中提到的手持攝影遙相呼應,共同構成了影片獨特的人文藝術風格。
隨著時空交叉點的開啟,人物間的關系逐步走向緊張,深陷在懷疑織就的巨網中難以自拔。他們懷疑休和阿米爾是外界的入侵者,懷疑貝絲在食物中投放了致幻藥品,懷疑自己的男友是否忠誠,甚至懷疑平行時空存在的可能。八個人的群體中,個人的思維方式與行事風格本就存在著巨大的差異,當彗星來臨,所有時空被打亂重組,他們在驚恐之余,本能地爭奪有限資源,無目的地宣泄憤怒與敵意,反映出了最原始而真實的人性。本片在人際沖突領域突破了傳統,沒有設置一個英雄式的主角,而是平均用力,試圖深度挖掘八個人反目成仇的原因。而種種線索都指向了人類的趨利避害心理,將其視作影響人際關系的主要因素,是《彗星來的那一夜》提供給觀眾的一大啟示。
(三)內心沖突
內心沖突是一個較為抽象的概念,它可以看作是外界沖突與人際沖突的最終形態,周遭事物不斷向內施壓,就會給人造成心理上的壓迫或不適。本片人文部分的終極目標,便是要展現角色內心強烈的矛盾沖突,借助首尾對應的敘事,達到讓觀眾感同身受的觀影效果。
通過女主人公艾米在聚會上的自述,我們可以大致了解她的生活狀態和基礎情緒。明明是自己嘔心瀝血創作的劇本,卻成了他人成功的墊腳石,身為一個高傲的芭蕾舞者,艾米很難放下自尊,去做主演背后的替身。在事業的瓶頸階段,她又遭遇了愛情的考驗,男友凱文即將被派往越南工作數月,艾米一方面不愿意放下事業與他同去,另一方面,又分外在意男友的舊愛趁虛而入。事業與情感上的兩難處境,讓她的情緒始終處于低谷狀態,憂慮與不滿在膨脹,亟需一個隱蔽的蟲洞來告慰自己。上文的背景交代悉數隱藏于對話中,既明白曉暢,又可做到不露痕跡,觀眾很容易忽略這些看似隨意的抱怨,殊不知這一幕已為最后的結局埋下了伏筆。
艾米尋找著所謂的理想世界,期盼自己能夠進入一個事業上風生水起,與愛人相依相伴的房間,為了一粒夢想的后悔藥,擊倒了“完美”中的自己,并試著取代她,融入全新的時空。這一系列舉動是艾米在內心驅使下的必然選擇,也是她深思熟慮后作出的決定,然而,小小一個電話,就足以擊碎內心的全部妄想。片中的內心沖突,可以概括為去與留的沖突,是靜待彗星劃過,接受現有的自己,還是邁出房門,試圖從最初改變未來,艾米在完美房間外窺視的場景,有力地展現了角色內心的猶豫不定。明暗協調的背景中,屋內的艾米與朋友有說有笑,屋外的她則十分惶恐,眼神中流露出渴望、恐懼、不安。她深邃的眼睛將觀眾吸入了角色的內心世界,不禁回望自身的痛苦與機遇,重新審視過往的選擇,從而真正體悟到角色的闖入動機。時間的矛盾創造了片中人物的復雜個性,也凝練出深沉而悲涼的情感氛圍,同時,心理活動的細致刻畫,讓這部軟科幻電影的人文內涵,達到了相當的高度。
結語
浩茫的平行時空中,每個交叉小徑背后都隱藏著不同的道路,總有一個自己能夠找到永恒的幸福。《彗星來的那一夜》工于細節,勝在設計,將超驗主義與科學的經驗性相結合,在擷取人文元素的基礎上,深度剖析了人物的內心沖突,這一舉動,成功避免了題材同質化,塑造出立體而個性鮮明的角色。與傳統的硬科幻電影相比,它拋棄宏大場景與華麗特技,在故事與理論之間找到了平衡。人文性的強化,無疑為小成本科幻片突出重圍提供了新思路。